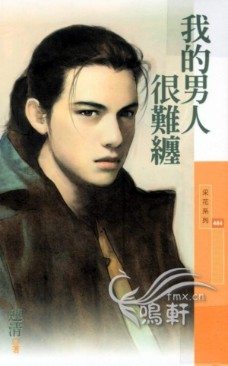我的诈骗生涯-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天后,信用卡寄来了,同时也意味着我得离开了。我和妈妈、迪恩在过道里告别,妈妈看上去又憔悴,又苍老。迪恩目光闪烁,躲开我的眼神。平常他对我极其崇拜,总是缠着我问这问那,但今天却光是踢墙,一个劲儿把手往裤袋深处插。我拥抱了一下妈妈,然后向门口走去。经过门廊就是前屋。父亲侧着身子坐在里面,抽着卷烟,两眼直视前方。
对希思罗我当然是敬而远之,而直飞伦敦盖德维克。在那里我跑了几家外币兑换所,在航站楼闲逛了一会儿,然后才决定搭乘维珍航空公司飞往巴哈马群岛的巨型波音747…400客机。几千英镑为我买来了头等舱的一个好觉。
这可是明智之举。要是你曾遇到过闹心的事儿——打个比方说,你一直盗用他人的信用卡,眼下正被一位英国探长盯上——拿骚城绝对是个好去处。起初我对当地人友好亲切的方言疑心重重,生怕以前我在无数学校和监狱遭遇的情景再次上演:人们引诱我落入圈套,然后,一刹那间所有的人变得凶神恶煞。可这样的戏剧性逆转并没有发生。
我定了天堂岛上一套宽敞的豪华套间。这个人间仙境到处是度假胜地和赌场,夜夜笙歌,四周是白得耀眼的沙子。我初次见到白沙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大自然的产物,激动得撒开脚丫子就冲进海中。到达后一整天,我躺在懒汉椅上悠哉游哉,一会儿望望海水,一会儿读读介绍附近景点的小册子,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逝。
夜幕降临,我依旧沉醉在海景中。四面环海的巴哈马群岛真是风光无限。回到酒店,我在酒吧里结识了一对年轻美国夫妇。见我套近乎,他俩相视会心一笑,但我没管那么多,只顾旁若无人说个没完没了。我们仨看起来倒是一拍即合。
迈克从事的是石油行业,刚刚在拿骚开完一个会,妻子简刚从得克萨斯搭飞机过来跟他会合。他们有苏格兰血统,毫不怀疑就接受了我所谓酒店咨询顾问的说辞,对旅行和鸡尾酒的喜爱跟我不相上下。
棕榈树婆娑舞影,玛格丽塔醇香爽口,暖风吹来阵阵隐约歌声,我们聊个没完没了,颇有千杯少之感慨。稍晚,他俩窃窃私语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向我说,他们明天会乘迈克父亲的游艇出海短途观光,希望我赏光同行。
我脑中最先蹦出来的念头是:骗人。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第二天凌晨他们把我叫起来,三个人走到码头。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尴尬,一来宿酒还没有消退,二来我一贯的防人之心在不时作祟。登上游艇的一刹那,我所有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游艇光彩夺目,大约12米长,处处都预示着此次出游将会多么轻松愉快。迈克和简一跃而上,仿佛赶公交车一般稀松平常;我则像个圣诞节早晨的小孩子一样喜气洋洋跟在他俩后面。我们穿过艇舱,往船头走了几步,迈克突然指指右侧:
“那间是你的,伙计,”他说。
我推开转门走进去,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镶满乌木和镜子的船舱,还铺了地毯。我丢下包折回到甲板上,迈克正忙着摁这个那个按钮,而简则张罗着准备日光浴。
“这简直……棒极了,”我大抒感慨。迈克满脸笑容。
“是啊,肯定会不枉此行的,”他回应道,顺手递给我一听啤酒。“想去托图吗?”
他指的是大洋之舌,拿骚西侧的一条天堑。海底在那儿凹了下去,形成一条深达数千米的巨大沟壑。不用说,我当然一门心思想去看看,迈克他们也兴趣盎然。
整个旅途中我兴奋得无可救药般,大部分时间都做博学多识状,言不及义地向迈克搬弄海军青年军训团的术语。接近大洋之舌,我爬上船头,刹时间呆住了:眼前只见无比深邃的一片黑色海面,直指天际。
我们坐到甲板上,随着波浪起伏,20来米下面,就是两个大陆板块裂开的地缝所在。在洛基老家,不只一个晚上,我神游过此处和类似的其他地方。大洋之舌、汤加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唯一不同的是环境——当时我是包在棉被里,揿着手电徜徉在书页之间。
“嘿,挺不错吧?”迈克突然从身后冒出来,手搭凉棚遮住阳光。
接下来几天我们就在埃克苏马、卡特岛、长岛和朗姆屿之间的珊瑚礁和浅水区间游荡。有时漫无目的顺流而下,遇到中意的小海湾就泊住游艇,不是下船戏水就是在珊瑚丛和色彩斑斓的鱼群中潜泳。夜幕降临,迈克抛锚停船,简做饭炖菜,而我则负责调鸡尾酒。然后我们在甲板上盘膝而坐,头顶漫天星光讲故事。
当时的感觉好像世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巴特菲尔德、信用卡和那个叫伊斯盖特的家伙仿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早晨醒来,极目远望,看到的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碰到的头一个岛屿——圣萨尔瓦多,你说我哪里还有闲心管那些破事儿?
回到拿骚,迈克和简得搭当晚班机离开,三人依依不舍,黯然道别。我敷衍说日后一定会再联系,独自走回酒店,一丝沮丧不禁涌上心来。我对拿骚留恋不已,又逗留了一周,迷上了海盗黑胡子,须知此人也曾把巴哈马群岛用作避难所。凡跟黑胡子沾点边的旅游线路我都逛过了,对这位恶名远播的江洋大盗,我还就其生平给导游们扎扎实实上了几课。
总而言之,此次加勒比海之行让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信念。它提醒我,生活能给人什么样的奖赏,特别是跟前段时间的颠沛流离相对照。然而,旅程虽近尾声,好戏却还没收场。
我赶到机场,办完登机手续,拐进一间酒吧。这是个简陋所在,门外就是飞机跑道,酒客寥寥。我坐在高脚凳上,隔着一个座位,是一位正在读报的肥硕男人。虽说他举止古板,但身穿夏威夷花衬衫,手握一大杯鸡尾酒,再严肃也有限。在这种场合,我全方位出击的假日势头从不消减。
“不赖的地方,”我开口道,但这个开场白显然不太对路,他扫了一眼酒吧,露出颇不以为然的神情。我赶紧补救:“那些岛屿啊,简直棒透了。我刚坐了艘船去过……”
这句话立马见效。他也曾驾船去过托图,我俩交流了航线、风向和旅途见闻。我朝侍者一打手势,他乐滋滋给我们斟满了酒。待侍者退下,我转过身来,面向这位新朋友。
“这里人真友好,”我说。并不是问他,他却给了个回答。
“都是看在钞票份上。”他嗓音淡定从容,但我却听出一丝非同寻常之处。他的皮肤虽然晒得黑黑的,却十分光滑,显示着良好的出身,腕上戴着一只贵重的手表。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啜一口酒,继而进一步发挥:
“当地人从游客身上赚钱,但事情远比这复杂。有的钱你可以实实在在看到,”他挥手指指机场里熙熙攘攘的游客,“可看不到的钱要比这多得多。”又啜一口酒。我身子只顾往他那边凑,差点从凳子上栽下来,这时他才转过头来把话说完。
“那些岛屿,”他说道,“堆满离岸资金。”
我隐约明白他另有所指,但似懂非懂,一时没回过神来。
“那是?”我问。
他咧嘴笑笑,伸手再拿起酒杯。“人们手中的钞票呀,”他说,“本不该在他们手中的钞票。”
盖德维克机场寒气逼人,再加上形势不妙,我决定还是隐姓埋名退守伦敦。我住进西区一家连锁酒店,然后忙乎着再张罗几张新卡。打出去的第一批电话中,有一个让我搞到了一位海军上尉的信用卡。(奇*书*网^_^整*理*提*供)卡没送到手中时,我对他的背景其实一无所知——我本来找的是史密斯先生,电话中也没提起海军上尉这回事儿。
这家信用卡公司非得通过各种繁复的授权,才肯发放账户副卡(比如给侄子用)。可是过不了几天我就会被这家酒店扫出店门,所以我干脆以账户持有人的名义申领了一张补发卡。瞎猫说不定还能撞上死耗子呢,我怀着加勒比海之行的乐观心理这样想。第二天卡送到我手中,嘿嘿,本该是先生的地方却赫然印着:海军上尉。
我打电话到信用卡公司核实账户详情,电话那头的年轻人毕恭毕敬念出我的头衔。这狗屎运也走得太好了吧,我昏头昏脑又问信用额度是多少。
“五万英镑,”那人确认。我转过身找外套。
如今想来已是恍若隔世了:几年前,我曾坐在艾尔郡家里的科本伯恩单元房沙发上,读一份简介,讲的是一家名为“吉凡克斯”的公司。文章说,这家公司是个裁缝铺,设在萨维尔街一号,是这条名街的“皇冠之珠”。200多年来,这家店曾为世界各国皇室人物、国家元首裁剪过衣服,而且素来与军队有着不解之缘。纳尔逊勋爵、威灵顿公爵和济民号军舰的布莱上尉都是在这家店度身定制的衣服。现在轮到我了。
这家百年老字号裁缝铺墙上挂满了皇室徽章和油画,置身其中,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位凯旋的战场英雄。一位老裁缝一边用软尺量我后背,一边和我闲扯军事。进驻伊拉克的战役几个月前刚打响,我们谈到了奔赴前线的可能性。
“够讨厌的,”老头儿嘀咕道,“布什这家伙,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
“我跟一些战友聊过,”我一副心已飞到战场的样子,“据他们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喏,”他给我打气,“至少您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像部队一员。”
=奇=说真的,看到这位好心老头儿尽其所能,为一位即将奔赴战场的新兵蛋子拂去心头的恐惧,我真有丝过意不去。但我又对那身次日早晨便可完工的军装爱得要命。出得萨维尔街,我信步踏上邦德大街,来到久已心向往之的瑞士表行。
+书+我曾无数次站在这家店外面,盯着一排排金表银表,大气不出。可是这次我径直走了进去,唤来一名售货员,让他为我逐个细说劳力士系列。我告诉他自己是皇家海军上尉,上岸休假,想买点好东西犒劳自己。
…网…过去两年来大约不下二十次吧,我曾在那家店听售货员讲解劳力士家族每款手表的特别之处,边听边频频点头。这回我又试戴了好多块手表,最后才相中一款,然后告诉售货员明天来取。唯一区别是,这一回,我真打算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吉凡克斯还没开张我就等在门口。军装棒极了,我跟人说要出席一顿正式午餐,当场就给换上了。我把换下的衣服塞到头天才买的公文包里,来到大街上。我这身装束既光鲜出众,又滑稽可笑。与早晨的购物人群擦肩而过时,不少行人发出吃吃的笑声。
我强作镇静,钻进瑞士表行。售货员还是昨天那位,一开始他没认出我,后来我故作夸张地把帽子取下,他才猛地认出来,子弹般冲出柜台迎接我。那款劳力士只是低端产品,一两千英镑,不过那一刻的感觉真是超级棒。
他刷卡时,我一丁点儿怀疑也没有。哪怕卡刷不过去,这套军装也是挡箭牌。在打印票据的当儿,他把装着表的盒子滑过玻璃柜台推到我面前,我把它跟其他平民物品一起放进袋里。
从邦德大街,我打了辆出租车到优斯顿火车站,然后登上前往曼彻斯特的火车。在座位上,我撬开盒盖。这可是我蒸蒸日上事业中的一大战利品。我捋起夹克衫的绣花袖口,有意无意地转动手腕,让手表滑来滑去,向世界炫耀它的高贵出身。我练习着一会儿抓抓颈背,一会儿正正帽沿,借机展示这一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