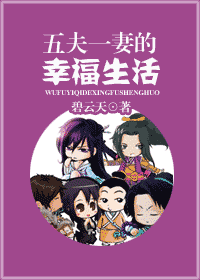幸福的苹果控-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章正南待了一会儿,打了个哆嗦。他四下看了眼,确定安全后站了起来,说:“咱们找个地方谈谈?”
秦知也站起来,摇头拒绝,“我今天结婚。”
“咱多年的弟兄,你不会这么绝情吧?”章正南低声下气地哀求,样子、语气、形态,要多猥琐便有多猥琐。
是什么压弯了章正南的脊梁,令他如此猥琐?
秦知没吭声。他们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互相打量着,一直打量到远处不知道谁燃了一枚白天没响的鞭炮。章正南吓了一跳,立刻蹲下四下张望。
“到底怎么了?”秦知问他。
黑暗中,章正南吃力地弯着身子,竟然在发抖。他抖了一会儿,说:“秦知,哥们儿倒霉了,真的。我知道今儿不适合,但是你能不能帮……一把。”
依旧是那股子遮盖不住的猥琐气。
心底微微叹息一下,秦知无奈了。他到底是招惹谁了?先是郎凝,接着是章正南,好好地结个婚怎么就那么难?他看看还在满院子找他的那堆老同学,还有依旧在屋顶上不嫌丢脸地唱歌的吴嘉阳,罢了,罢了,就这一回,最后一回,就当是在学校里没人理自己这个半自闭症患者的时候,章正南却一直陪着自己、总是惦记自己的报答吧。
“去楼上吧,你吃饭没?”秦知指指小区楼问他。
“还没呢。”章正南站起来,看下左右,小心地回答。
秦知带着章正南慢慢向回走,章正南小心翼翼地跟着。走到楼口的时候,吴嘉阳站在院子的小屋顶指着他大叫。秦知回头冲他瞪了一下眼睛,比了一个“嘘”的手势。这货立刻乖觉地闭了嘴,好奇地看着章正南鬼鬼祟祟地从院子的角落进了楼。
有些人即使是化了灰,吴嘉阳也能闻出他的味儿。有些事情他早就知道,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说。原本他想等着老大平平安安结完婚,他再去卖这个好的。
这人,怎么找到这里的?
吴嘉阳看着满院子寻找新郎的老同学,心里倒是一下子明白了。那个消息,这些人还不知道,他们依旧会把秦知的消息当成卖好的手段来讨好某些人。想明白这点,原本一脸醉态的吴嘉阳,竟然露出一副难得的聪明相。他冲着正在满院子起哄的马柏东招招手。马柏东走过来冲他笑,“我也没梯子,今晚你就别指望下来了。”
马柏东挑挑眉毛,转身去找梯子。
秦知跟章正南来到新房。今儿他的目标实在太大,才进楼梯,一群邻居的孩子便立刻围上来大喊:“找到了!找到了!……”
那些孩子四处大叫着,找不到秦知的老同学们再次一拥而上。尾随着进来的章正南被拥挤到了一个角落,没人在意他,怎么可能认出来呢?
雁城阔少,章正南,跟这个低着头、浑身散发着臭气的人,是不相干的,用正常思维无法连接起来的。
客人们都喝得不少,他们满嘴胡说八道地抓住秦知一顿威胁。秦知苦笑着看着楼口,今儿真的不适合谈话。
章正南努力缩着身体,看着站在新房外一脸无奈的秦知。他期盼气质可以挽救一下他,无奈此刻的秦知,自身也难保。
一只手突然就这样没预兆地搭到了章正南的肩膀上。章正南愣是吓得一哆嗦,惊恐地回头看去,却是陈律师他们四人,都是一脸暧昧的笑容。吴嘉阳仰头冲着楼梯大声叫了几声,引得楼上那些醉鬼们更加兴奋,一拥而上,齐齐抓了秦知下楼,闹洞房去也。
“章老板今儿过狂欢节呢?啧啧,瞅瞅你这身打扮!”赫逸元调侃了一句,让开楼梯。
章正南一脸羞愧,转身想走,身后吴嘉阳叫住他,“外面可是都在找您呢!我公安局还有一些开过赌局的哥们说,那可是几千万呢。”
猥琐的人只好又转过身看着这四人组。这一刻,章正南想到了死。如此不堪的境地,被不如自己的熟人看到,简直是生不如死。
陈律师指指楼梯。他倒是没嘲笑章正南,但是眼睛里的幸灾乐祸是怎么也遮盖不住。
“上去吧,老大那边还得一会儿呢。”
章正南点点头,很快贴着墙角上了楼。
秦知被人折腾了整整两个小时才脱身,等他来到楼上,章正南已经吃饱了。吴嘉阳站在门口,指着茶几上的三个大碗说:“三大碗喜面,这货可真能吃。”
秦知笑笑,指指门口,屋子里的其他三人站起来走了出去。临到门口的时候,陈律师小声对秦知说:“别借给他钱。”
秦知愣了一下,点点头,拍拍他肩膀送他出去后,反手关了门。wωw奇Qìsuu書còm网
以前最好的两个兄弟呆呆地坐在屋子里,吃饱了的章正南有了安全感。逃亡了整整一星期,他第一次觉着自己还算个人。
“我倒霉了。”章正南抬起头看着秦知,苦笑着说。
秦知看着那张已经洗干净、下巴上满是胡子茬的憔悴脸孔,点点头,“我说,那是女人才有的特权,每月一次,你哪里有那功能了?”
“我变成这样,我都替你高兴,真的。出卖朋友,撬兄弟老婆,我要是你我就放鞭放炮庆贺一下。”章正南自我批评地说着。
“放过了,今儿放了一天。你也甭难过,现如今撬别人媳妇那是大买卖,是能人才做的事情,一般人那都做不了的。”秦知回答。
“讽刺我?……你不问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吗?”章正南苦笑。
秦知深深叹息了一下。他觉着有点儿渴,站起来倒了一杯水。楼下,关妈妈不知道在骂谁,声音很大地传了上来。
“你看看,你们看看,原本说了准备两百斤喜面就够了,现在六百斤都出去了!说什么呢,谁叫你们这么抬了?谁说能放这里了?这亲戚里道的就差这几碗面条了?快拿走,快拿走,你们还不知道我这脾气?……忙了十多天了,喂,你谁啊?亲戚?谁家亲戚?就怎么不见来帮把手了?!呸,别提我家那个死老头,今晚我还没见到他……够不够啊?你家十多口人呢!再端几碗回去,明儿还有甜饭,记得来拿,碗可是要还的……哦,你谁啊?卖菜的?卖菜的也在这里混吃混喝?”
老太太的声音透着一股子喜气,虽然说的话还是那么难听,但是,以前的尖酸今晚却在话语里少了很多。难得的,今晚的关妈妈很大方,一个劲儿地推销喜面,怕是担心存的时间长了,过期发霉吧?
“郎凝来过了,她很伤心。”秦知把水杯放到桌上,对章正南说。
章正南没吭气。他一支一支吸着香烟,以此来显示自己已经豁出去、全然不在意的意思。秦知看着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方他才合适。章公子离了钱,本质上来说,就剩下俩字:麻烦。
不过,秦知倒是不嫌弃他。以前上大学时,他这个不合群的脾气总是跟人处不好。那个时候在学校呼风唤雨、喜欢拿钱换感情、喜欢给全人类埋单的章正南,身边总是不缺少朋友。拥有诸多朋友的章正南不知道怎么了,总是爱拉着秦知到处走,什么聚会都会拉着秦知。全靠他,大学四年,秦知总算拥有过一些关于学校的好的记忆。这一点,秦知觉着这一辈子,不应该忘记人家。
至于成年,成年后的故事总是透着那一股子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沧桑。秦知对这位学长有感情,是真的当他是朋友。假如没有章正南给他机会,那么也许真的不会有现在的秦知。看他变成这样,秦知是震惊的、无法理解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章正南此刻竟然臭到狗都不闻的境地?
饱腹之后的章正南找到了安全感,这室内的温度令他昏昏欲睡。灭烟头后,章正南抬起头,对秦知说:“我需要一些钱。”
哎,这么快就纳入正题了?秦知呆了一下。
章正南很想压低一下身姿,态度里加上一些愧疚巴结,就像刚才那样,称一声“哥”,也许这样秦知便会帮他吧?但吃饱后、吃饱前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变化,他努力了半天,却再也叫不出来了。他现在肚子不饿,便找到了骄傲跟尊严。
他沉默地等着这些天已经习惯的拒绝声。反正是要被拒绝的,不如早些说出来,他也彻底坦荡了。
秦知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学长、老哥、兄弟,最后他释然地笑笑说:“好啊,可我没有太多。”
章正南彻底惊讶,而后脸上露出一丝奇怪的笑。他努力用他的眼睛最直观地去透视、去探究秦知,而后他拍拍沙发,就像大学时候他坐在豪华学生公寓里那套英式真皮沙发上那般,叫秦知来自己身边坐。
秦知坐了过去,从怀里拿出支票本,填好数字递给他。
章正南接过去,看下数字,有些惊讶,“我以为你恨我,所以最后一个来找你。”
“一直恨。”秦知没抬头地说。
“……大学那会儿,人人都说你古怪。”
“你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告诉他们你的大度,这个我知道。”
“好像……是这样。这些日子,我求过好多人。亲生的一奶同胞叫我快去死,他们巴不得我倒霉。我的倒霉似乎现在尽如人意,全世界都在找续集看。”
“这样啊。”秦知应道。
章正南将支票推回去,苦笑了下,“嗯,我的身份证不能用了,如果可以,给我些现金吧。银行,那些该死的家伙都在找我。”
秦知取回支票点点头。他打开门,跟门外守候的几个人嘀咕了几句。陈律师看他的眼神实在不好,秦知也知道自己在自找麻烦,但这样的日子,实在不适合看到这个痛苦的人。
他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如果章正南不解释,他也不打算问——知道别人悲惨的事情,会心累。
秦知坐在那里发呆,章正南一言不发地抠着桌面的桌布。屋里空调缓慢地释放着温度,秦知酒意上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做着混乱的梦,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隐约觉着耳朵边有些人在交谈。秦知想睁开眼睛,却无能为力,大量的酒精再次侵蚀着他的脑神经,他无法思考,无法掌握身体的指挥权。
大约到了后半夜,秦知坐起来,晃晃脑袋。
吴嘉阳站起来给他倒水,马柏东递给他一封信。秦知再扭头左右看看,章正南已不见了。
秦知打开那封仓促写在一张礼单红纸上的信——现在的人,似乎不太习惯再用这种方式去交流了。用这样的角度去接触章正南,给秦知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拿着解剖刀子终于切开了皮肤表层一般。其实文字是很奇妙的一种东西,有时候,文字比语言坦诚,更加真实。
秦知老弟你好:
钱,你的下属给我了。你什么都没说,他们就懂得了你的意思。从这点来看,我依然是不如你的。这么久了,我身边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帮衬下自己,在适当的时候提醒自己的人。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比你会做人,比你玩得好,搞不懂为什么我总是要跟你攀比。到最后,你又不离不弃的追随者,而我却开始一无所有地在这个世界浪荡着,而且不知道要浪荡到什么时候了!
我不会做人,这是今天才发现的。
这些天,我一直在四处逃亡。家人在找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在找我。我没日没夜地到处走,后来才发现,我最害怕看到的不是债主,而是一无所有地贫穷。我就是个懦弱的、不敢承担责任的草包,一挂腐烂下水般的怯懦者。
随便你怎么骂我。
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因此常常做出旁观者的姿态,喜欢躲在暗处观察别人的脾性,并以此为乐。这次,一次看上去不大的豪赌,我输了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