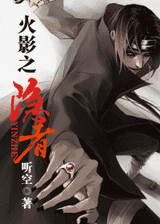难言之隐+7番外 作者:李暮夕(晋江vip2013-12-01正文完结)-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44章
战争比禾蓝想象中来得还要快。
特来区就是金三角南部的一块沃土;通往滇缅的一条黄金大道;暗地里无数双眼睛都曾盯过这块肥肉。但是;至今没有一个人敢真正下手。一是地势较高,崎岖难进,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二是没有足够的后备军火和后援物资。一旦进攻;倘若不能速战速决,此消彼长,很容易给周围其他虎视眈眈的势力在背后放冷箭的契机。
像这种乱世,从来都是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这一次;彭云清正式宣布围剿特来区;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加奇怪的是,他居然得到了周围很多山头土势力的支持。
禾蓝不清楚其中的原委,也不想去细究,她关心的只有杜洋的生死。
当年,他和他的父母一起接下围剿金三角毒枭的任务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会竭尽全力,鞠躬尽瘁。过不了多久,却在背后倒打一耙,和别人一起合谋,出卖了她的父母。她还记得母亲临死前,为了保护她才被对方的杀手砍中了要害,最后把她推入地道里,她才得以逃生。和父母同去的伙伴,也一一惨死在她面前,那一晚,她在漆黑的地道岩洞里蜿蜒爬行,磕碰地手心脚背都是血。
没有一个夜晚,比那晚更加漫长。
她只知道杜洋是仇人之一,却不知道其余那人是谁。
或者,不止一个。
连日来,禾蓝心神不宁。这天早上,在吃早饭的时候,她忍不住问道,“阿潜,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正在啃一块玫瑰米糕的白潜停下来,含笑看她,“你问这个干什么?难不成,你担心杜别那小子?”
才一句话,禾蓝就被他堵了这么一下子,心里的话说不出了。白潜喝了口乌冬汤,眉眼被出山的朝霞染得更为浓丽,只是看着她,禾蓝就觉得自己所有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只听他这么说,“你在打什么主意,我现在就不问了。但是,如果你想和那个姓杜的小子有什么牵扯,或者又想离开我……我不保证会做出什么。”
禾蓝沉默了。
“他这次死定了。”白潜捉了她的手,放在唇下落下个轻柔的吻,“这次的这批货里,居然有那么多是那些山区首领的女儿,可见杜洋运气不好,大家群起而攻之,他们两父子都死定了。”
那些货——分明是彭云清让人运来的,现在却推到了杜洋头上。事情更不可能那么巧,怎么可能捉的人都是那些山区首领的女儿?
“你陷害他。”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白潜施施然起了身,一点也没有诡计被戳穿的尴尬,“他们父子也作恶多年,这叫天理循环,自作自受,怨不得我。”
“杜别不是那种人。”
这句无意间出口的话,却激怒了他。白潜冷笑时也带着惊人的妩媚,扣住她的下巴,提起她的肩膀按在窗台上。禾蓝只有一半屁股沾着窗框,半个身子都在空中晃荡,她吓得抓住他的手臂,“阿潜……”
“你和那个姓杜的,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禾蓝微微喘着气,身下不断吹过的风把她后背的汗也吹冷了,黏在身上仿佛有冰凉的爬行动物滑过。他冷冰冰没有感情的眼神,也让她陌生而恐惧。他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很在意杜别。这个认知让她的心里很复杂,想开口,又咽回了话。
“说话啊,我要听你亲口说。”白潜双眼烧红,极力自制的冷漠,在她的沉默中渐渐崩溃。在他还没有认识她的十几年里,杜别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天和他们一起在花圃漫步的时候,就只听到杜别的谈笑风生细数和禾蓝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杜别还不知道他和她的关系,那么一切就不可能是预谋的。如果那都是真情流露,如果一切都是真的,他在她心里又算什么?
在禾蓝的那十几年里,记忆里只有杜别,而没有白潜。哪怕现在她是他的,也磨灭不了那个人曾经存在的事情。钉子在墙壁上留下了烙印,那么,哪怕是拔去它,痕迹也依然存在。
白潜死死地看着她,第一次这么脆弱不堪。
禾蓝还没开口,就被他紧紧抱进怀里。这个早晨,他就想这么抱着她。
“……杜别只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没有别的了。”禾蓝开口。
白潜听到,抬头看着她,“真的吗?”
他现在的表情,哪里有黑帮大佬的样子,就是一个刚过青春期怕被欺骗的小男孩。禾蓝终于笑了,“就是这样。”
白潜看着她,盯着她的脸,从她的眼角看到她的唇角,似乎要辨别出她话中的真假。半晌,他忽然轻笑了一声,“空口无凭,我要看看你是不是在说谎。”说完一把扛起她,几步到了床边,在禾蓝的尖叫中把她放下去,俯身就压了上来。
他像个野兽一样,近乎粗暴地撕开了她的上半身的衣服,仰头脱掉了自己的汗衫,和她肌肤碰肌肤贴合在一起。禾蓝胸前的两团乳/f分外柔软,像两个发胀的面团,还带着暖气,白潜喘着粗气抱住了其中一只,捏成凸起的形状,伸出舌尖一下一下地舔着,牙齿故意咬住那个小尖头,拉起来扯了扯。
……
白潜抱着她,紧紧压着她,他的吻既温柔又粗暴,像发泄又像品尝,舌尖舔着她的唇瓣,一点一点地舔着,似乎她是什么美味的佳肴。
室外的阳光盛了,忽然,走廊里一阵急切的脚步声传来,他们还没反应,移门就被人从外面推开。
“禾蓝,我来……”声音戛然而止,杜别在门口化成了雕像。
禾蓝尖叫一声,紧紧缩在白潜怀里。他的肉/棒还留在她体内,她上半身差不多都是光着的。虽然有他挡着,但是,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他们在做什么。
这是个偏僻的别院,为了避免被人打扰,白潜故意挑了这个地方,还让人守在外围。
杜别出现在这里,实在是个意外。
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
白潜扯了被单,晃眼间就把禾蓝层层裹了起来,光着身子坐在床头,把她抱在怀里,“真是不识趣,在别人做这种事情的事情闯进来,败兴!”
杜别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回话。
他的目光还在禾蓝身上,从来没有过的震惊。禾蓝在他心里,一直是个很保守的女孩,是需要被呵护爱护的妹妹。他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被别的男人压在身下,自动地岔开双腿求欢。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破碎,怎么也拼凑不回来了。
“看够了没有?”白潜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拨了拨禾蓝的嘴唇。
杜别动了动嘴唇,“小蓝……”
禾蓝只觉得无地自容,把头深深地埋到白潜怀里,“你走,求求你了!别看了!”
“听到没有,我姐让你滚!”
杜别扶着门框,踉跄着逃开,沿着走廊快速奔逃,仿佛身后有什么魔鬼。他的脸色比来时更加苍白,心里最后的希冀也被磨灭了。阳光一瞬即灭,黑暗又席卷而来,刚从战场上回来的满手血腥似乎在这个时候更加浓郁了,熏得他透不过气。
杜别的身影消失很久,禾蓝还不敢从他怀里抬头。
“好了,他走了,起来吧。”白潜爱怜地抚着她的头发。
禾蓝茫然地看着窗外的太阳发呆。
白潜轻轻啃咬了一下她的耳垂,贴着她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来这里吗?”
禾蓝回过神,怔怔地看着他。
白潜笑地有些狡黠,“杜洋撑不了多久了,你说他来是做什么?”
禾蓝被他的笑容骇到了。
“你怕我吗?”白潜用鼻尖蹭着她的脖颈,“可我好喜欢你,姐,你是我一个人的,永远都是。谁要是敢和我抢,我就让他家破人亡,不得好死。所以,姐,你就发发善心,放过他们吧。记得以后不要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我一不高兴,没准就以为他们是你的奸夫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
“在你面前,我就是不可理喻。”他开始耍无赖了,抬起她的下巴,“啧啧”叹道,“看来,你还很有力气啊。要不,再来一炮?”
禾蓝惊呼中被他压倒,又是一阵大干特干,到了半夜,他还是不肯停歇。她像只在江流中摇个不停的小船,被他操地晃来晃去,颠簸不停,摇摆不住,只能在他有力的臂弯里喘气。
白潜的精力很旺盛,这么多年的历练,在刀锋上行走,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做个一天一夜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了。苦的是禾蓝,早上起来的时候下面都红肿了,两片花瓣都被他弄得变了形。她张开双腿看了看,顾不得吃早饭,一瘸一拐地走到走廊尽头的佣人室,红着脸向嬷嬷借药膏。
嬷嬷是过来人,一看就明白过来了。她摇着头出去找,回来后递给她。
禾蓝刚要接过,老嬷嬷就收回了手,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不要什么事情都顺着男人,不舒服的时候就要拒绝,不能太惯着他。你年纪也不小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不像他,年轻力壮的。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懂得体恤女伴,你连路都不能走了。一会儿我帮你说说他,真是的。”
“不要!”禾蓝满脸燥红地拉住她,“不关他的事,是我同意的,嬷嬷别说他了。”
嬷嬷听后不敢相信地看着她,“你都快奔三十的人了,怎么也这么糊涂?女人要爱护自己,别只顾着一时爽快……”
嬷嬷后面的话,禾蓝根本不敢再听了,几乎是爬着逃出来的,到了门口,还差点滑一跤。旁边伸出只手,及时捞住了她,“小心点。”
禾蓝听出白潜的声音,抬头一看,果然是白潜微笑着的脸,晨曦中俊美地就像神只一样,苍白的肌肤,精致到了极点的五官,就像一江春水里撕裂开的朝霞一样浓艳而秀丽。只是,现在她看到这张脸就想打他。弄得她这么难受,还害得她这么丢脸!
不等她开口,白潜就懒腰抱起她,轻松地搂到怀里。
嬷嬷从屋里赶出来,拿着根拐杖打他,“你这个小兔崽子,一点都不知道怜惜人……”白潜怪叫一声就向远处逃去。他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现在却被一个老人家追着打。
好不容易摆脱了嬷嬷,逃回了房间,白潜一脚把门倒带着勾上,把她压到床里。禾蓝手里的药膏被他夺了过去,摆弄着,“这是什么?”
“药膏!”禾蓝夺过来,现在双腿间还肿痛不堪,对他多了很多的埋怨。
“你哪里受伤了?”他作势要解开她的衣襟。
“别!”禾蓝抓住他的手,支支吾吾的,“……是……那儿。”
“哪儿?”白潜一出口,就懂了,目光移到她的双腿间,撩起了她的裙摆。禾蓝伸手要挡,却被他轻松地移开。褪下了她的底裤,他倒吸了一口凉气。那片娇嫩的地方凌乱不堪,两片嫩嫩的花瓣肿的充涨起来,合在一起鼓鼓的像颗青涩的小桃子,颜色更是红颜地让他口干舌燥。
“有那么严重吗?”他伸手去碰,禾蓝“嘶”地一声,差点哭出来,“不要碰。”
他惶乱地慌了,“我不是故意的。”
“我昨天让你收了,你偏偏不要,还一直……我很难受,今天早上起来都这样。”禾蓝终于有了一个借口,都不想和他说话了,抱了被子把自己盖住。
他有时真的不知道节制,她到最后都几乎晕过去了,都忘了发生什么,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他那个东西还留着里面,硬邦邦的,她当时还没什么感受,早上五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