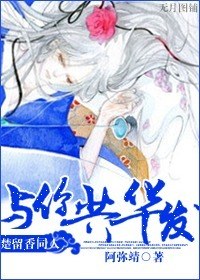宫砂泪美人与权谋的较量:宫砂泪 作者:池灵筠(出书版手打完结)-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手。
上官嫃微微胆怯地往后退了一步,躲藏在他身后,“他们是什么人?”
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刮起,旌旗飘荡,红底黑墨赫然画着一个唐正威严的“查”字。
“爹?”查元赫迟疑再三,牵着上官嫃慢慢朝前走。
对方亦加快了速度,知道先行的士兵们将他们二人团团包围。查元赫感到异样,高声问:“查将军可在车上?”
驼铃叮当,晃晃悠悠拉着篷车走进了包围圈,敞开的布帘令车内一览无遗,司马银凤缓缓走至车边,目光极为复杂地盯着他们,语调疲惫:“你爹往南边寻去了,我一会儿要给他传个信,叫他回扁州去。”顿了顿,司马银凤斜睨着周围的将士,“怎么?你们都不认得皇太后?”
一圈圈士兵陆续跪下,呼声震天,“叩见皇太后!”
只这短短的一瞬,上官嫃前一刻被冰冻三尺的心里,陡然又涌起无数惊涛骇浪,她忠实挣脱了查元赫的手,缓缓走向前,“平身。”
司马银凤并未下车,始终高高在上睨着他们,下令道:“既然找到了,那便先在前面扎营,明日回程。你们去给皇太后搭寝帐,本宫稍后再做安排。”
士兵们纷纷忙碌起来,大队伍缓缓移进绿洲。
上官嫃脑里空白一片,只觉得这夕阳极刺目,刺得人头昏眼花。司马银凤躬身,朝她伸手,语气温和道:“太后,请上车。”
上官嫃木然地朝她走过去,耳边传来查元赫低微的呼唤:“晚上在帐里等我。”那熟悉的嗓音令她心绪稍微平和了些,不论前边的路究竟要怎样走,他都会护着她的吧。
寝帐的帘子厚重,一放下来,大漠里呼啸的风声顷刻被遮掩着毫无踪迹。上官嫃呆呆地跪坐在床铺上,失神地望着自己的手臂,并未察觉有人进来,直到司马银凤逼近地问:“太后似乎有心事?”
上官嫃心中一惊,从容地将衣袖放下,“皇姐劳累了,怎么不在帐中休息?”
司马银凤满面倦态,不似从前那般锋芒毕露,叹道:“我想叫你看个东西,又担心你情绪过激,便先来问一声、”
“皇姐想叫我看什么?”上官嫃定定地望着她。
“我们在大漠里遇见了押解犯人去扁州的队伍。”
上官嫃喜出望外,表情刹那又僵住了,静静地不发一言地瞪着司马银凤,似乎预料到了什么,手指便剧烈颤抖起来。司马银凤握住她的手,痛心道:“他们被风沙埋致死,后又被暴晒多时,已被晒成了干尸,面门难忍……只想叫你去认一认你爹,好焚了骨灰回去下葬。”
打至183
上官嫃僵了许久,嘴角微微抽搐,艰难地挤出几个字,“等一会儿。”
“嗯,我在帐外等你。”司马银凤戚然地望了她一眼,快步走了出去。
上官嫃猛地捂紧了胸口,大口大口喘气,生生地将悲伤吸进肚里不着痕迹地消化掉。她极度恐惧,又必须撑下去,世上已再无亲人,最疼爱她的爹此刻就躺在不远处,等她去认,等她带他回家。她还记得,娘亲的墓穴有两口石棺,其中一口是爹留给自己的,她要带爹回到娘身边,让他们重聚。
上官嫃骤然爬起来疾步冲出寝帐,对背对着自己的司马银凤说:“我们走吧。”
此刻,查元赫正站在一丈开外,怔怔地望着她。司马银凤侧头唤他,“你也一起去好了。”说着,她便拢着防风斗篷朝小帐去了。上官嫃失魂落魄地随着司马银凤,并未在意查元赫朝自己伸来的手,只自顾自地朝前走,好似只剩下一具躯壳。查元赫抿紧了唇快步跟上她,护在她身后,生怕那摇摇欲坠的身子突然晕厥倒地。
这一段路极近,怎么好像走了一世那么长。帐里守卫的士兵掀开帘子,现出里面两排用白布遮盖的尸首。上官嫃顿了顿,垂头钻进去。
司马银凤抬了抬手示意,士兵便将白布扯开。数十名干尸呈现在眼前,那些皮肉干枯粘连在骨骼上,面容惊悚至极,头发稀疏枯黄,就像传说中的恶鬼一般。上官嫃侧目瞟了几眼,便不敢再看,肚里一阵汹涌好似翻江倒海,忍不住扭向一旁干呕起来。其实口里什么也没呕出来,只是眼泪先簌簌扑落了。查元赫揽住她的胳膊,心疼得无比复加,却不知要说什么才可以安慰她。
司马银凤轻声道:“若是不敢,改天吧。”
上官嫃死死咬住下唇,踉跄几步冲到那些干尸当中,一面泪流,一面细细打量。查元赫在一旁看的揪心,恨不得将她拖出去,好不让她刚结痂的伤疤又再次溃烂流血。
上官嫃剧烈颤抖的手翻动着一具具干尸身上褴褛的衣裳,终于在其中一具面前跪了下去,泣不成声。
司马银凤快步走了去,瞠目端详,问:“是他么?”
“是……亵衣的袖口有娘亲绣的花纹……”上官嫃攥着尸首的袖口,隐忍的哭泣渐渐变成嚎啕,声嘶力竭。查元赫从身后抱住她,用自己的胸膛包裹住她颤抖且冰冷的身体,埋首在她颈间哽咽道:“还有我,娘子,我一直都会在……”
上官嫃渐渐伏地痛哭,她许久没这样哭过,最近的一次,仿佛是在太液池边,她以为那是便穷极了一生的眼泪,原来不是,伤痛不曾麻木,而是逐渐加深。丈夫、爹娘、家族,一丝丝从她生命中被剥离,她终究落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就算躲在大漠里,仍然逃避不了如此残酷的命运。为何要甘心忍受?为何只有无尽的忍受……她从未争过什么,但也是时候争点什么了。此仇,不共戴天……
漆黑的帐里燃起了一点火光,司马银凤提着灯笼慢慢走近床边,见上官嫃仍然坐在角落里纹丝不动,好似丢了魂一般,只是等着空洞的双眼。查元赫趴在一旁睡得正熟,轻微的鼾声中海透着几分天真。
司马银凤望着上官嫃低声说:“你知道左右命运的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自己。公孙一族因受凉王怂恿意图弑君才惨遭灭族,皇上喘疾突发全因酒中被凉王的人吓了毒,你父亲更是如此冤死在大漠之中。如今朝堂诡异,忠良陆续被害,摄政王一心培植自己的势力,罔顾社稷。上官嫃,你饱读圣贤书,知书达理,难道要做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徒有虚名的皇太后吗?”
上官嫃缓缓抬眸,晦暗的眼中再也不复往日清明,她气若游丝却无比坚定道:“我不要。我是皇太后,我要回去告诉所有人,是谁弑君,是谁逆谋,是谁在扰乱朝纲,是谁让社稷陷入风雨飘摇。”
“好,我会助你。”司马银凤慢慢走近她,用灯笼照亮了查元赫的脸庞,“可是他呢?元赫生性耿直,为人仗义,他会为你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可是你真想看见他赴汤蹈火、两肋插刀的场面么?我承认我自私,不想他牵涉到那些无法明辨的是非当中,你可割舍得下?”
上官嫃一合眼,满眶的泪便倏然滚落,嘶哑的声线中透着一股恍若隔世的沧桑。缓缓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他阳光般的笑靥,是她陈年旧梦中唯一的光亮,与其让这光亮在阴霾里渐渐湮灭,倒不如放逐他去更加光明的地方,如那些翩翩白鸽,遨游蓝天。
司马银凤已然得到了想要的答复,提着灯笼转身离去,帐内又陷入一片昏暗。上官嫃伏在查元赫身上,湿漉漉的嘴唇贴在他唇瓣辗转,“元赫……再唤我一声娘子,可好?”
可惜,凄凉的静谧中,徒有她肝肠寸断的哭泣。
弦月如钩,夜幕漆黑,不似往日的深蓝。营地间篝火寥寥,这是大漠里最后一夜,明日就要进城了。疲惫的士兵们随便吃了一阵便回营帐休息,几只骆驼也相继趴下,驼铃叮当作响。
帐内充盈着肉香,在大漠里能吃上肉便是极奢侈的,查元赫却直愣愣望着菜肴发呆,丝毫没胃口。司马银凤这一番也着实受累了,微微咳嗽了一阵,抿了口水,道:“不管你作何想,都必须打消那年头,她是你舅母,这辈子都是。回去之后,我会请求皇上将你调走,去戌边。”
查元赫戚然道:“男子汉大丈夫,焉能始乱终弃?娘,请恕孩儿不孝。”
“何止是不孝!”司马银凤气急,狠狠扇了他一巴掌,“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如今身怀六甲,难道抛妻弃子就是大丈夫所为?”
查元赫傻傻捂住火辣辣的半边脸,磕磕巴巴道:“她……她……她怀孕了?!”
“你明媒正娶的妻子如今身怀六甲……”隔着帘子,帐外的上官嫃只听清楚了这一句话。她收住已经在掀帘子的手,缓缓摸在自己的小腹上,一步步往后退,最终扭头而去。
见查元赫痛苦纠结的样子,司马银凤渐渐压下怒火,厉色道:“你现在就去帐里跟她说清楚,你们只能一刀两断,别无他选!”
查元赫跌跌撞撞冲出了长公主的寝帐,抱头瘫坐在尚有余温的沙地里。别无他选?不,他从不违背自己的内心!
帘子揭开,夜风乘隙而入。火焰摇摇晃晃,许久才稳下来,一缕缕黑烟从火柴中腾起,熏得帐内有些呛人。上官嫃在火堆边发愣,莲查元赫进来都只抬目望了一眼,继而又垂眸下去。查元赫眼见着她日益消瘦,心痛难当,面对这样形容枯槁的上官嫃,他想说的话更加难以启齿。
“你怎么不歇着?”上官嫃问道,嗓音嘶哑。
查元赫直勾勾盯着她,小心翼翼问:“明日就进城了,我知道你想送你爹回金陵去,可是我们一旦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不如……我们到下一个落脚的地方就逃走吧?”
上官嫃淡淡蹙眉,胸口一阵钝痛,“逃去哪里?就算逃走了,他们也会派兵寻我们。”
查元赫急切地握住她的手,“不怕,我们去西域,他们一定找不到!等我弄匹马,我们就可以连夜逃走!”
上官嫃斜斜睨着他风尘仆仆的面庞,一点点将自己的手抽回来,道:“我不走。”
“什么?”查元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凑近了她一些。上官嫃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遍,“我不走。我要回去。”
查元赫急急喘气,眸子渐渐湿润,“为何?我们已有夫妻之实,我会待你很好,我们去寻一片海阔天空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上官嫃移开视线,毅然打断他,“无忧无虑?我们要靠什么为生?你能给我锦衣玉食的生活吗?还是下半辈子都要跟你颠沛流离?我过不了那样的日子!”她挤出这一番话,尾音悄然在颤抖。
查元赫怔了许久,喃喃道:“你在说什么啊?娘子……我们这些天过得不好么?你不快乐么?你不用吃苦,不论如何颠沛流离,我绝不让你吃苦,我可以伺候你,我可以把你当皇太后一样供着……”
上官嫃含泪吼道:“够了!我不想听你胡言乱语。总之我要回去,你也回去,我们互不相干!”
查元赫重新攥住她的手,用尽整条胳膊的力气紧紧攥着她的手,声音颤抖着说:“互不相干……难道我在你心中的分量,还比不上那皇太后的地位?”
上官嫃僵了许久,缓缓道:“没得比。”
查元赫不敢置信地瞪着她,手下的力道又重了几分却丝毫不觉,一字一句地问:“你可曾喜欢过我,淡薄也无妨,只要一点点……”
这句话,与她当日说的如出一撤,他们原来都这样傻,上官嫃苦笑着,斩钉截铁地答了两个字:“从未。”
查元赫骤然松了手,浓眉渐渐收住,仍带有几分不干苦哑追问:“既然从未,又为何委身于我?”
上官嫃喉口抽紧,强咽了半响,垂眸道:“不过是寂寞时候,聊以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