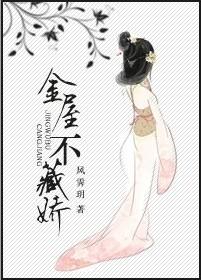尘香(重修版) 作者:悄然无声-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些什么。
过了半晌,听得一个懒洋洋的道:“红云,给我倒杯茶来,死丫头你又跑到哪去了?
宣华踌躇了一下,转身对佣人吩咐了几句,边推了门走了进来。
室内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离了原位,只有那张黄梨木的榻是整齐的,嫣红缎的褥子,上面放着一个紫檀的长方形匣子,大红绸的底座绣的春睡海棠,上面嵌着放烟膏的锡盒,烟刀、烟签、镊子、梅花纹饰小巧玲珑的烟灯还有缠枝青花磁的小茶壶。
宣华只等这个机会,抬起头飞快地将榻上的女子眉目五官过了一遍,方才彻彻底底地自惭形秽起来。都道自己貌美,面前的女子看起来不过是二十出头,极纤弱的模样,身上是件密密绣着缠枝海棠花的纱衫,同色丝葛裤子。只是坐在那里,便是一幅工笔美人图。她似是才坐起来,烟劲还没过,鬓发蓬松,惺松地撑开眼睛,一手还拿着那只错金珐琅的烟枪,日光在她的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
他俊美冷冽的眸只望着她,若有所思。
宣华只觉得满室上等鸦片的幽香,像一根千斤的铁柱,压得她气都喘不过来了。
这便是当年湖都大名鼎鼎的名花,顾安安。
她呆呆的站在那里,顾安安却似没看到一般,清清冷冷地再次开口:“红云。”
宣华这才笑了道:“夫人可是渴了,吸完烟喝茶最是伤身子的,我叫人我已经叫人备了荔枝红枣汤,您再等等。”
顾安安这才正眼看着她。宣华只觉得她昏懵倦怠的眼神半开着,细眯的瞳孔,射出一线透人肺腑的寒光,半晌才笑了:“难为你这么有心。”
放下了烟枪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宣华注意到,她的面颊虽已经瘦的削尖,但腮上的两个笑窝一闪一闪仍是十分动人。
“宣华。”
宣华看着她,也看着他。
他不动亦不语,冷漠的目光甚至不曾投向宣华,仿佛都没察觉到她的进来,也没察觉到她的讲话,只是望着她。
一股什么味儿就从心底里沁出来了,直往骨头里浸进去似的,浸得她全身都有些儿发酸发麻,却只能咬紧牙根,慢慢的咀嚼着那股苦凉的滋味。
“好名字。”
顾安安说罢便要跻鞋起身。
黄梨的脚踏上同样是溅满了碎磁片,宣华刚要提醒她当心,他早已快一步冲了上去。月白绫的鞋子,他拿在手中,细细磕尽了里面的碎磁,然后套在了她的脚上。
她似习以为常,只要起身,却不想烟劲正浓,她踉跄一下。
她的手,慵慵懒懒的搭在他的肩上,她的袖子挽了起来,一截皓白的手臂露在外面,映了日头,分外的纤细如玉。梳成髻的头发仿佛因为躺得久了,散了下来,一丝一缕落在他的颈项。
她却不以为异,头也不抬地道:“你今天来得不巧,瞧我这样子也没办法招待你,改日来了,咱们姐妹再好好聊聊家常。”
“你先回去吧。”他看这才转头看向她,低声道。
他看着宣华,顾安安却在看他,朦朦的眼睛里有些莫名的东西。他回头看时,她已经转眼看向宣华,笑了说:“红云,帮我送送。”
宣华的嘴唇张了张,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看见了他望向她的眼神,宁静似水。窒了窒,一咬牙,便推门出去。
当晚他喝得如一滩烂泥一般回来,宣华帮她他脱了衣服,扶他到床上躺下,静静的看了他半晌,然后她缓缓闭了眼睛,眼泪一滴一滴落了下来。
第二日,红云就送来了一份礼物,只说是顾安安送给她的见面礼。红云拉着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总之前又拉着她的手密密叮嘱了一番,那一份儿殷勤,自是不同了。
红云走后,宣华才打开那份礼服,一套的钻石首饰,颜色极正的火油钻,隐隐带着微蓝。不知为何,宣华却想到了她的发色,不是寻常的乌黑,带着浅浅的栗色。
宣华又去上门道了一回谢,过不了几日,管家便把宅子的帐目悉数交给了宣华过目,只说是夫人吩咐的。
她这才知道,原来所有的一切,那个仿佛工笔画卷的倦怠女子,全部都看在眼内的。
又过了月余,已是初冬,这日早上方起来,就见丫鬟慌慌张张的进来。
“怎么了?”
“舅老爷在前面跟管家发火,管家叫四姨太过去呢!”
舅老爷指的是顾安安好赌成性的唯一兄长,宣华不敢怠慢,连忙起身,还没走到前厅,就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骂得鸡飞狗跳。
“不过是个姨太太,真以为自己得了宠就飞上了天?老子的事她也配管,连给我妹妹提鞋都不配,我呸!”
宣华一口气堵在胸口,缓了一缓,才走进来。
他方才住了口,却不起身,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斜着眼看着她。
宣华也并不理他,只对管家问道:“怎么了?”
管家唯唯地说着:“舅老爷急用五千大洋,可是帐面上没有那么多现钱。”
“少拿这话敷衍我,我只问你给是不给?!”
“舅老爷也听到了,帐面上没有闲钱,就是有这宅子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都是要钱的……”
“我呸,你也配跟我打官腔,你凭什么?不过是个舍家弃亲的,连丫头嫁人都是三媒六聘,你个连丫头都不如的,也来管我的事?”
舅老爷一口气说下去,声音越来越大,话说到最后,几乎已经是破口大骂。
宣华脸上渐渐地失了颜色,怒极反笑道:“我只告诉你,如今这里我说的算,凭你想要不明不白的拿出钱去,门都没有!”
他却仿佛霸道惯了张嘴还带叫骂,却见宣华一双眼睛,异常地亮,似燃着了火一般,炯炯然叫人不敢直视,这才住了嘴,偃旗息鼓地去了。
柯锦书和舒凝早就闻了信来了,此时都掩了口,互相使眼色暗笑,剩余的人面面相觑。
宣华着看着两房的人牟足了劲准备瞧她的笑话,也知道自己莽撞了,但木已成舟,无法挽回。
到了晚上,他突然派了车接她去西园,看着侍卫严肃了的脸色,宣华已然知道不好,也顾不得理会他人幸灾乐祸的样子,急急上了车。
到了西园佣人却不领到客厅,直接将她到了楼上卧房。
宣华也是第一次见到她的卧房,和那日的烟房不同,里面是十分豪华的西式布置,宣华却无心看四处的陈设。
他坐在床畔,似是刚到,连军转都未来得及换下,神色凝重,眉端紧锁,一望而知便是隐忍着极大的怒火。
宣华心里怦怦直跳,叫了一声:“老爷。”
床头紫铜熏炉里添了一段沉水香,浅浅淡淡的味道弥漫开来,半浓半浅,朦朦胧胧地,像是鸦片幻化出的一幕烟纱,温香中含着轻寒。雕饰纷繁图样的铜床,垂着浅紫色的悬帐,顾安安躺在上面,并未起身,身上盖着金色柔软的真丝棉被。
一个老妇人坐在床的另一头,拿着手帕边哭边擦着眼角,看了宣华进来霎时间哭得更加的大声:
“我可怜的女儿,我可怜的女儿……”
宣华这才知道,她病了。
他端着一碗药,慢慢的吹着,半晌尝了尝,觉得温度合适了才递给顾安安。她接过碗,低着头慢慢地啜着。
那药的味道想是极苦,她的五官都皱了起来,病中憔悴,又是这副模样,并不十分好看。但他的眼却一直在望着她,也很苦。
涩涩的苦味搅得宣华胸口翻腾,每一呼吸都似那么艰难。
顾安安喝完了药才抬眼,用奇异的悲悯目光望着宣华。纯黑色的珍珠眸子浸在染上了水一样的迷离,却还含着幽深婉约的光泽。眼波微微一转,那水、那光,便流到宣华的心里去了。
另一边她兄长坐在凳子上,极狼狈的样子,褂子的前襟也撕破了,露出里边浅灰的汗衫来,此刻大声的叫道:
“就是她,就是她,妹妹你要给我作主啊!”
宣华被她兄长叫得的心顿时吊起来了。
他脸色渐渐铁青,向她走了几步,又停住了,用冰冷的语气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那边的老夫人哭得更加的凄惨,吁吁叨叨的念着:“我可怜的儿,什么人都能踩到你的头上,我们母子是没法过了,还是收拾收拾回老家了……”
“去跟他认错!”还没等宣华出言解释,他的眼睛已经不在看她。
宣华心里膨膨鼓鼓地跳,听得他沉了声命令,到底是一口气没憋住,挺直背回道:“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认错?!”
老夫人的哭声似乎变得更加的惨烈,夹杂着她兄长的叫喊声,他的脸上逐渐布满了阴云,猛然的上前一步,仿佛就要撕碎了她。
“够了!”
说话的是顾安安,她两剪清眸,望着宣华,理不清百结愁肠。挣扎着要起身,却仿佛气力不够,情不自禁地捂住了嘴,伏在床上低低地咳着。
她如云的栗发上沾满了汗,湿漉漉的,披散在皱褶凌乱的枕巾上,人亦如秋叶般纤弱憔悴。待撤开手一看,素白如玉的手上沾了一片艳红的血痕,殷然醒目。
他猛地一颤,扑到床前,失声叫了出来。
“安安!”
那厢的老妇人和她兄长还待一齐哄然再哭,却被她喘息着打断:
“娘,你们都出去,哥哥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
老夫人和她兄长俱是一惊,随即望着她的脸色,这才悻悻的走了出去。
而宣华不想她如此说,不由抬了眼望去,几乎哭了出来。
顾安安倚在他的怀中,对了宣华勉力微微一笑,道:“难为你了,烦请你看在我的面上,别跟我哥哥计较才好……”
还待再说些什么,却被他硬声打断:“好了,你出去吧!”
宣华心下一酸,面上仍强撑着浅笑盈盈,转身出门,刚合上门便听到里面人叹息般说:
“明明是你带了人蓄意让我哥哥去赌钱,如今反而累上无辜的人,作给谁看?”
无限的心酸,尽在这一语之中。
以后的日子里,所有人都说她命好,不止得了他的眷顾,连脾气极怪的夫人俱是十分的看重,一向混世魔王的舅老爷见了她,都要礼让三分,再也没有人敢待慢她,渐渐的所有人都知道了极为得宠的四姨太,连已经决裂的傅家人也上门来了。
但只有宣华自己知道,每每午夜梦回,便是他终没有看自己,只望着顾安安,恍如不知道她的存在一般眼。缓缓地伸出手,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自己的脸颊,每每从指间传来的感觉,是水样的冰凉。
不知不觉的到了春日,便是他的生日。宅子前光是汽车就都排出了老远,那种盛况,恐怕再无人及得上。
顾安安也从西园来到宅邸,难得他的兴致极好,灿烂灯火下,他英俊的面容看来慑人心魂,越发显出一股优雅沉蕴的风派,一直挽了一身百蝶穿花大红裙褂的她招呼着客人。
红云怎是忙里忙外的指挥着佣人,一会席红玉也到了,右手执着一柄檀香扇,一阵风似的到了顾安安身边,挽着她亲亲热热的说笑了几句。
转过头看见她们,微微点头,大刺刺地坐到沙发上去,红云上前敬烟,席红玉却从自己皮包掏出一盒烟来,取出一支,装入一杆长烟嘴里,红玉替她点上火,便高傲地喷着烟圈。
宣华和舒凝、柯锦书等人过了一会子便在侧厅打上了牌。
“不过是个师长的姨太太罢了,也眼高于顶,全然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