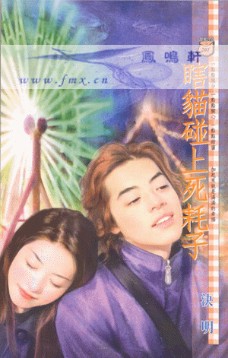����Ҫ����-��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ʱ�䲻����Ϊ�˵���ʹ��ֹͣ�����˵���ʹȴ����һ��������ʱ�����ʧ������¹�ȥ�ˣ��������ɹ�����ʬ����һ����
���������ε�Ȱ˵��������ӣ�������ֻ��ҡͷ��Ĭ����ǿ����һͷ��ʨ���������û�а취������������ҩ��
����һ�������еij��տ���ȥ����ͨ��ûʲô��ͬ������һ�㶼û�Գ�������ʱ������ͷ�����Լ��Ķ��ӻ���ɻ���������и����ӣ��и�Ī�����Ķ�����
�������뿪����Ҳ�ж���֤���������������µ�ӡ����
����˫�ֱ�ס�Լ������ĵ���ů�ͺ���Ī�����ģ���֪��ʲôʱ��ʼ����ϲ��������ƣ�����Ī��������������������
���꣡
�ű������̶���һ��ţ�̽������������緹û�Զ��٣��ȵ�ţ�̰ɣ��Ժ��Ӻá���
���սӹ�����ţ�̻����ȵģ��������������һ�ڣ���ζ����������е�塣�����ű��Ӹ�Ż��һ�£������ӷ��¡�
����ô�����ˣ���
���գ������˺ȡ���
����Ŀ����˸�������ȺȰɣ����˲��á���
����ҡͷ��ת��ͷ�����⡣
���̶��ų��տ���һ�������������ͷ�����ðɣ���Ӯ�ˡ�һ���Ҫ��Ҫ��ȥ��䣬��ܾ�û�����ˡ���
�������˺ܾã������ڵ�˼ά��Щ�����ģ��������뿪����
���ţ���
���տ������̣��������뿪S�ǡ���
���̣���ȥ�Ķ�����
���������룺��H�ǰɡ���˵��үү��������ˡ���
���̣����DZ��������ˣ���
����ҡͷ��
�������ѣ���
���ջ���ҡͷ��
�������ȥ��˭�չ��㣿��
���գ����Ҳ���Ҫ���չˡ���
������Ц��һ�£���������������Ӳ���Ҫ���չˣ���
���ճ�Ĭ��һ�����˵����������̫���ţ�����IJ���Ҫ���չˡ������˶���˵����Ҳ����ֻ����Ҫһ�����ϴ�����
ž��
���̻�û��Ӧ�������Ѿ�һ���ƻ��˳�ȥ�������˿��ų������ϵ������ָӡ�������ַ�ŭ���������Ǹ�Ī���������б�Ҫ���������Ϊ������˾����Ҫ��������үү������Ҳ���µIJ�ҵ����һ�����˶�������ȥ���㵹�ã�����Ƥ��ʹ�ⲻ������Ҫ���������ӣ����ǹ��������ϣ�����Ҫһ�����ϴ������գ��Ҷ���֪����ô˵�㡣��������ͷ�������dz�û�ˣ�ץ�����ϵ�ţ�̾�����������࣬������Һ���ȥ���Ǻ��Ӳ���Ҫ����
ţ�̵�����ӿ���ǻ�������������̵Ļ�������������ۣ������������رս����죬˫��ȥ�����̡�
���������ˣ������϶�������ա���һֻ��ץס���յļ����ֱ���Ƶ��ڴ��ϣ�˫ϥ˫������ѹס���յ�˫�֣�Ȼ��Ӹ����µ�һֻ�ְ���յ��죬һֻ�ְѱ��ӵ��ڳ�����ߣ���ţ�̵��˽�ȥ��
����ʹ��������ţ�̵��õ������ǣ����ϡ������ϣ�˳�����������˴�����������ȵ�Һ�������������뵽������ĺ��ӻ�������ȥ��ͻȻ���ֽ��������Ŀ���Ϯ��������Ȼ����û���������������Ѿ����ȣ������Ķ�������������
����㵵ؿ��Ž�����ߵ����̵������������۾�����ë�Ҳ��������������Ʋ����������ſ���ݺ�ҧ�����Ĵ��ϡ�
���̳��۵������������������������������ܵ�ϴ�ּ�ȥ�¡�һ����һ�������Լ��Ķ��ӣ���Ҫ����Ҫ����Ҫ�ߣ�Ī�����ı�������Ҫ�ߣ������㡣
����֪���Լ�Ϊʲô�����������¼�������û��ԭ�������Ǹ����˲�Ҫ�����˺������������Ƿɶ��˻�һ���ϲ����������
���ӻ��ǽ�������������������˿һ���ϸ�ۣ�Խ��Խ���ԣ�Խ��Խʹ�����������õ��������һ�������۵�վ�����ȣ�˳��ϴ��̨���ڵ��ϣ����Ŷ����۵ú������˳�����
����һֱ���ڴ��ϴ����������Լ��ղ���ֵľٶ�������ϴ�ּ����쳣���������͵��ѹ������嵽ϴ�ּ�һ���ŵ�������ɫ���������ڵ��ϣ������Ŷ��ӣ����ݽ���ҧ���´������͵͵����ʡ�
��һ�����ȥ������վ���ҽԺ�ܣ����հ������ץ�������·���ҧ����������Ҫ���ӣ���Ҫ�õ��������㣬�̸�磬�����㡭���������������������������þ�ʹ���ڳ������Ͻ������ų��գ���ʱ��ź�֪����Լ�һ���ϲ������
�ǰ�����ϲ����ô�����ۣ���ϲ����ô���ں��������Ż�������л�ץ���Լ�����������Ů�ˣ��ݺݵس����Լ�һ�����⡣
�뿪
ԽϪ��ҽԺ�������������۾������ˡ����ѹ����Ϳ�����ֻ�۾������һ����Ů�ˣ�ɤ��ɳ�����ʣ�����ʲô����
ԽϪ�������ˣ��������𣺡����գ�������ô�������ô�������ң������ھ�ȥQQ���š������ϰǹ��ǶԹ���Ů��������û�����ˣ��ر��Ǵϳ��Ǹ����ˣ�ǰ�컹ҫ��������˵Ҫ�����ˣ��һ�������ĸ�Ϲ�۵����ˡ�����ԽϪһ��˵һ�߸о�������������������������̧��ͷ�ɻ���ʣ�����ô�ˣ���
���տ���ԽϪ���죬��ɵɵ���ʣ����ʹϳ϶����������˭����
��������˭����Ȼ�ǡ�����ԽϪ������ͷ�������㲻֪������
��ʱ�����������鱨�����Ž��������˿�ԽϪ�ٿ��˿����գ��ʣ�����ô�ˣ���
ԽϪһ�������µı��飬���������ۿ����ת�����ҡ��Ҳ�֪���ϳ϶����������û������˵����
����üͷһ�壬�����߹�ȥ����ԽϪ�����ų���˵����������ģ����Dz����кý���ġ���
����ĬĬ�ذ�ͷת�˹�ȥ���۾�ʪʪ�ģ�Ŀ��Ҳ�������ģ��������������˹�����һ��������ʶ���Լ��Ŀ����������ֲ��뱻�˿��������ѱ����������ɵ�ͷ��������������һ��Բ��
ԽϪ�����̶�����һ�ۣ�ԽϪ��˵ʲô��������ҡͷ��ֹ�������˾����ڲ����������ϣ���Ĭ�ص��ų��ճ�����
��������������۾������������۾�Ҳ����һƬ��ڡ����ǵú�ҹ������ӵ����������ζ������Ƥ�����������塢���������ǵ��������������ĺ���������������˵����ۡ�����Ѫ��һ��һ�룬һ��һ�����������·���������ֻ���������ˡ�����������������һ��ʱ����ȼ�ճ��˻ң����ʣ�µ�������������һ�ؿ�ľ��
��ľ�Ϳ�ľ�ɣ���ľҲҪ����ȥ��ʹ�Ż��ǻ���Ż�Ҳ���ǻ�����Ķ���ʹ����ֻ�ǻ�ķ�����һ�����ѡ�������֮����һ���Ӽ�ʮ�꣬��ʮ���Ժ�����ʹҲ�����ɻ������ţ��Ҹ����˾�������̫�̣�ʹ����˾�������̫��������һҹ��ͷ��
���쿪���ӣ���������һƬƽ�����������̺�ԽϪ������һ��Ц�ݣ�����Ҫ�뿪S�У�ȥH��ɢɢ�ġ���
���̺�ԽϪ�������ҷ��ԡ�����һ������̲�����ʲô���������鱨��������˵�������գ����ӻ��ڡ���
�Ѿ��������ķ·�������һ�£����յ�ͷ�����Լ��Ķ��ӣ����ȵ��ૣ������ڣ���
���̣���������
�����ڵĻ�������������������˵�ú�ƽ���������Ѿ�ʲô��û���ˣ�Ҳ����������ү���ҵ����Һúû��ŵ�֤�ݡ���
ԽϪ��ͷ���˳���������̾��һ������Ĭ�������գ����Ѿ�ʹ����ľ��������ʱ�仹��ʲô���������ܴ��ŵ�����������һ��ľż�����������ع��Ż�е������
�뿪S�е���һ�����������ʣ����մ���ţ�п�ͺ�ɫ���£����ϴ���һ�����ī������Ϊ������������һЩ��ɫ�İߣ�������������Щ�㲡������Ż�ɫ����Ƥƽ��Ь���Եý�С��������һ���߽��˻�����
������IJ�Ҫ������ȥ�����������Ż�Ʊ���ǻ��ڡ�
���գ�����Ҫ����
��ȥ�DZߺ�С�ĵ㣬���˸��ҵ绰����
���գ����š���
����Ʊ�Ͳ��������ˣ�������ס����˵�����ɻ���ɻ���һ��������������ɡ���
���տ�������һ�ۣ����������̵��֣�����һ���Ӷ������������������̣����ʱ��лл�㣬���ڵ��Ҳ�����ϲ�����κ��ˡ���
����û����������˵��һ���ֱ��ϣ�����֮�����DZ�һ��Ҫ�չ˺��Լ�������߹�����æ��ʱ���ȥ���㡣�DZ߱���Ҫ�Dz��������˵�����ٻ�һ������
�Դӳ��ϵ�������Ҳ��Ӱ�죬�����������ǰ��������Ȼ��Ը�����鷳���ˣ��������ϲ��ܾܾ������á���
���̽��������Ʊ�ڣ��������������߹��սDz�������¥�������������������������ģ�����һ����ɫ�ı�ʿ���۶��ߡ�
����������ü������̫��Ϥ�ˣ������ٴ����ﶼ�μ������·�ϱ�ײ�ɡ�ֻ��Ī������������ʲô���ѵ���������ҡҡͷ�������Լ������ˣ�Ī�����ñ����ֶ�Ӯ�ó��ϰٷ�֮��ʮ�Ʋ�����������Ȧ��һֱΪ����ڸ�������������Ǽ��Ȳ�Ը�ἰ�̼ң��ر��dz��գ���˵�дδϳ���������Ī����������Ƣ����
����������˵�ģ�Ҳ����ȫ���档����̧ͷ���˿���¥�ĺ���ң���Dz��Ծ���¶��һ��Ц����ô���ã�ֻҪ��ƽ����H��������һ��ʱ�䣬��ʹ�����������ġ�
H�еķ�������������������һ��ƽ��С������հ�������֮��ķ����ؽ���ӭ�˽���������Կ�ס�
���մ�����������Ҷ����ķ��ӣ��ɾ����࣬�Ѿ��ܺá�����ôס�������������ҹ����ҹ���죬��е�ؿ���ɫ�仯������ʱ����ĺܳ�����Щ�������������һ���ӣ�����һ�������Ѳ�֪Ʈ���ĸ����䡣
Ҳ�������彥������˵�Ե�ʣ����ﷴӦ���Խ��Խǿ�ң���ʲô��ʲô������ˢ��ʱ��һ���³�����ˮ���Ƿۺ�ɫ�ġ��ò����װ���ǰ�����£����ӽ�����������һ���˳���ɢ�����ںӱ������ػأ������Ϲ���ͬ���и��������������£����˵����綼��ô���֣�����ûʲô��ͷ�ġ�
��֪����ô���ģ���ʲô�����������ʲôҲ�������úÿ���������Ӱ��������֪������Щʲô�����ǵ�ӰԺ����ˣ����Ű�ɫT���������������������������۽���������һЩ���Ƶı�Ӱ����㱾������Ǹ����ڡ�
�ţ������ãȻ������Ҳ����ľ��Ҳ����ô������Ц������Ҳûʲô���¡�
����Խ��Խ���ж���ò�����������Ҳ������ϵ����Ь�ӣ���ķ�������и�Ь�ܳ����Ľ�Ҳ���ˣ����Ŵ��ĺ첼�и�Ь�����ģ��dz����������������ò���ʶ�Լ��ˡ���ʹ����һ��ҹ��ͻȻ���ٵġ�����һ���ε�������ʱ��ԽϪ����������ָ��8��˵��˧��������Ŀ�������������Ī�������ϣ���ʱ���������ᣬ����ͦ�ν�������������Ұ��ȴ���������������߹��������������֣������ա���
�ܾ�û�м����������е�����������Щģ���������ǵ��������ӣ������������Ƿ����ģ���������ĺۼ���Ƥ����С��ɫ���Ǿ������л����˶�ɹ�����Ľ�����ɫ�������˽ý���ͬһֻ�Ա��������ϻ��������뺹ˮ�������˶��ڷ��⡣
��������֪���Լ������Σ��������ټ��������������ɵ�ʱ���������⾭��ʵ��̫���ã��õ����̲�ס���������������̲��ã���Ҳ֪���������϶��������ۣ�Ȼ��һ����ͬ����ɢ�����١�
��ʹ������ʱ�����Ԥ�ؿ�ʼ������ʼ����Ϊ����ʹ���ɺܿ���ò��ԣ��ڰ�������һ˫���ε����ڼ�ѹ�¸������ſ��ۣ��¹�Ӵ����ս������컨��һƬ���ף������̡���
����������һ�����ͷ�û�ж�������ʹһ��һ����ÿһ�ζ�����һ�ξ��ң��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