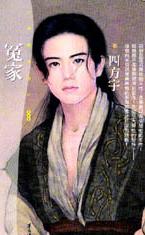陆观澜-冤家宜结不宜解-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正在想,等过一段时间,待到有空的时候,她要小写怡情,写一本以她和宋聿同学为蓝本的小说,书名她已经想好了――
冤家宜结不宜解。
就这么定了!
HAPPY ENDING'正文完'
番外一
我是沈寒培。
我的父亲,曾经是J省的副省长。从小,他对我和哥哥的要求,一直都很严格。
大我两岁的哥哥,是个优秀的天才,他写得一手好诗,他画得一手好画,他的学习成绩,一向都比我出色,父亲在我们俩,尤其在他身上,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在我们念初中和高中的时候,那时的父亲,是D市的市长,工作很忙碌,他担心身边人,包括温柔的母亲,对我们太过纵容,因此,在父亲的要求下,我和哥哥一直都在别的城市念书。
我们知道,虽然表面上对我们很严厉,但是父亲,是爱我们的。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十八岁的哥哥,高考过不久,就莫名地死于一场车祸。
我只知道,一向冷静,很有自制力的他,是在跟父亲大吵了一架之后,愤而跑出门外,才撞上了那辆飞驰而来的大卡车。
我跟妈妈都不知道他们关在书房里,在吵什么,但是,我们都看到了哥哥推门出来的那一瞬间,脸上那种冰冷彻骨的绝望。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短短时间内,老了十岁,特别是我的妈妈,她是高干家庭出身,向来知书达理,温和善良,但是,从那时起,她的精神,逐渐濒于崩溃。
她的眼神里,不时闪过深深的痛苦,还有,深深的绝望,她开始,经常默默地,一个人坐着。
她得了抑郁症。
我的痛苦,我的伤悲,不亚于我的父母。
哥哥和我,向来是最贴心的,父亲整天在外面忙碌,而母亲,再怎么关心我们,毕竟,还是有些话,是不能跟她倾诉的。
所以,高考放榜那天的晚上,哥哥就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他的房内,他先是郑重地让我闭上眼,然后,在抽屉里摸着什么,再笑着对我说:“睁开眼吧。”
第一时间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女孩子的脸。一张照片上的脸。
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十分年轻,也十分美丽,但是,她的那种美,那种气质,非常非常特别。
很快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会有那样一种感觉,因为,她的脸上,没有笑容。
她的眼神,略带忧郁,她只是静静地凝视前方。
哥哥说,她叫梅念尘,有点特别的名字,就像她这个人。
哥哥还说,他们俩,从高一开始,就在同一个班,她是以高分考入那所重点高中的,她性格有些内向,很少笑,所以,哥哥和她,将近一年的时间,从无交集。
但是,她和哥哥,居然有一个同样的爱好。
那就是,午休的时候,都喜欢偷偷遛到校园西北角的小山坡上,倚着那片小小的桂花林,或看书,或小憩。
直至一日,他们遇上彼此。
从一开始的有些局促,到渐渐开始有了交谈,再到后来,在不自觉中,两个人,开始期待着,每日午后心照不宣的小小邂逅。
但是,当时的两个人,什么都没有明说。
但是,在高考前夕,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一同报考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
他们都考上了。放榜日,哥哥出门了整整一天。
然后,那晚,在那张小小的照片面前,他对着我笑,因为,那天,梅念尘,终于接受了他的表白,还因为那一天,他第一次,吻了她。
那是他们之间的初吻。
十天后,一直很忙碌的父亲突然间在下午就回到了家,然后,他把哥哥叫到了书房,再然后,仅仅是两个小时之后,哥哥,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想,尽管从来也不说,但父亲的痛苦,应该远远超过母亲,因为他一向引以为豪的黑发,仅仅在一夜间,就白了泰半。
不久之后,我要求转学回到D市念高二,这次,父亲没有说什么,他第一次,运用他的权力,很快帮我办好了一切手续。
我要多陪陪我可怜的母亲,尽管她的沉默,一日甚于一日。
家里的气氛,一直笼罩着哀伤,即便父亲在这一年被任命为新一届的省委常委,和副省长,也并没有改变分毫。
父亲在人前,永远都神采奕奕,但只有我知道,人后的他,往往只在一瞬间,就褪去了脸上所有的笑颜。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我考上大学。
两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我考上了我唯一所填的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哥哥未竟的愿望,我要帮他实现。
并且,我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愿望。那是我在哥哥的墓前,对他许下的愿望。
父母亲的脸上,重又有了久违的笑容。尽管一开始他对我执意要报复旦不太赞同,眉宇间,似乎还有着隐隐的忧虑,但是,终究,他还是默许了。
在手持我的录取通知书的那一霎那,他和妈妈的眼里,泛起了点点泪光。
两年前,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们手上拿的,也是同样的录取通知书,只是,上面那个名字的主人,已经不在了,已经永远不可能,出现在那个美丽的校园中了。
但是,哥哥,我会把大学生活里的一点一滴,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告诉你。
我跨进了复旦的校门。
几乎从我跨进校门的一霎那,我就下意识地找寻一个身影,找寻一个名字。
梅念尘。
那个几乎会成为我嫂子的女孩子。
除了那张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我曾经在哥哥墓前,见过她带去的鲜花,那束哥哥的生辰忌日,必然会出现的鲜花。
很快我就打听到了她的消息。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梅念尘,很容易打听。
因为她傲人的成绩,因为她的美丽,还因为她冷若冰霜的气质。
据说,有无数的男孩子,被她所吸引,但无一例外的,都被她通统拒绝。
她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她的眼底,掠过无比的惊愕,还有深深的伤痛,她的唇微微颤动着,说了一句话,说得很低很低,但是,我听得极其清晰。
“你……你跟寒磊,长得真像。”
她的眼角,瞬间湿润。
从此,我们经常在一起,看书,聊天,间或,也一起出游。
她经常会跟我说起,她和哥哥当年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她说,在当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爱”字。
也永远,都来不及说了。
渐渐跟她熟悉后,我发现,梅念尘是一个外柔内刚的,极其倔强的女孩子,她只有一个母亲,她的家境,极其贫寒,以至于她需要课余兼几份工作来贴补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梅念尘身上,总有一种让我觉得熟悉的,亲切的温馨感。
于是,我不忍看她繁忙若此,瘦弱若此,我想帮她,但是,被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生平第一次,我对这样一个女孩子,充满了钦佩。
同样是生平第一次,我对这样一个女孩子,渐渐产生了淡淡的,有些异样的情愫。
哥哥,我已经不只是单纯地,想帮你照顾她了,而是……
但是,仅仅半个月后,父亲派了辆车到学校,嘱我即刻回家,来的那个司机传话说,我的父亲,有要紧事跟我说。
父亲还是坐在书房里的那个宽大的椅子上,他的脸上,是无比的疲惫。
他让我坐下,然后,他一言不发地,默默坐着。
又过了半天,他开口了,他的声音,空洞而干涩:“寒培,你见到梅念尘了?”
我微微一愕,因为父亲的眼神,充满了悲哀。
那一刻,我的脑海中,蓦地掠过两个字。
宿命。
是的,他的脸上,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哀。
我的心头,掠过一阵不祥的预感。
果然,父亲低低的,哀伤的声音响起:“寒培,你不能跟她在一起,你不能重蹈寒磊的覆辙,”他的声音,越来越暗哑,“因为……”
我屏息以待,等着他往下说。
父亲惨然一笑:“因为,她……她是你的姐姐,”他闭了闭眼,“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和梅怡的女儿。”
我愣住。
那年,父亲八岁,梅怡五岁。
那年,梅怡和爷爷一起搬到父亲所居住的那条窄窄的小巷。
她住巷头,他住巷尾。
她的父母,早已离异,她和爷爷相依为命,而她的爷爷,开了一间小小的点心铺子,赖以养家糊口,她家的院落里有一株年龄已高的桂花树,一到秋天,镇日散发出淡淡的桂花香。
父亲永远记得,每到秋天,在早上淡淡的晨雾中,总有一个全身带着幽幽桂花香的小女孩,快快乐乐地,来敲他家的门,然后,用软软的声音说:“尘哥哥,这是我爷爷做的桂花糕,第一炉的呢,快趁热吃吧。”
然后,那个小小的身影,连同左摇右晃的发辫,快快乐乐地,奔跑,远去。
那年,父亲十八岁,梅怡十五岁。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十年来,他们青梅竹马,朝夕相处。当时年少的父亲,在梅怡的心中,高大得像一座山,一座可以倚靠一辈子的大山。
十八岁那年,学业优异的父亲得到一个外出参加竞赛的机会,他去了,他得了第一名,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他用为数不多的奖金,除了给家里买了一些生活用品之外,又加上自己省下来的一点钱,奢侈地,买了一条粉红色的纱巾。
他是买给梅怡的,因为他知道她一直很羡慕班上的女生有这样一条纱巾,但是,她买不起。
只是,这条纱巾,永远地,留在了父亲手中。
因为当他兴冲冲地回去的时候,放下东西,第一时间奔到那扇熟悉的,不知敲过多少次的小小乌门前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从未有过的荒凉,和寂然。
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已经物是人非。
在他走后第二天,梅怡的爷爷,就因为突发脑溢血而溘然长辞,三天后,孤苦无依的梅怡,在父母亲双方的多次拉锯中,终于被早已改嫁到外市的母亲,勉强领走。
她走得很匆忙,匆忙得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讯息。
十八岁的父亲,站在那扇小小的木门前,完痴住。
再后来,父亲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他的老家,D市,做了当时D市市委书记的秘书。
父亲的文字功底一向很了得,再加上为人精细练达,懂得进退,很快就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和大力推荐,仕途上,开始现出曙光。
但是,直到父亲二十九岁之前,他都只字不提成家的事情,婉拒了四面八方给他做媒的人。
直到我的外公,当时回乡颐养天年没多久的前某大军区司令员,通过一些工作接触认识了我的父亲,他很赏识他,于是,找到父亲的领导出面,意欲把自己的独生爱女许配给他。
父亲应该是拗不过上司的劝说,并且,此时的父亲,已经不是十八岁的少年了,想必,对于自己的前途,自有一番考量,于是,在见了我母亲几面之后,出乎众人意料的是,他很快就和母亲结了婚。
或许,真正的原因,只有父亲才清楚。
父亲的仕途继续一帆风顺,很快就成了当时D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其中固然有他的努力,当然,外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