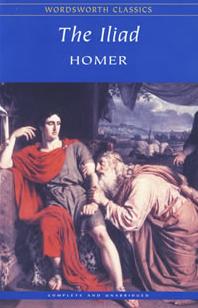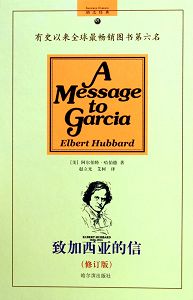伊利西亚-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我为什么不使用和以前一样的力量——同样的方法——去对抗邪恶的老大神们。我给你的答案是这样的;我们早已记不清当时是如何击败它们的了!”
克娄听到这话,惊讶得目瞪口呆:“可是,您参与了那次行动——是您自己策划的行动——时至今日,您并未改变,依旧是当时的那个元老之神,那个将它们击退的伟大科学家呀!您是说忘了是怎样取得那次胜利吗?”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哦,过去数百万年的事情我们还能记得颇真切,可是在那之前35亿年发生的事,我们怎么可能还记得呢?”
正当克娄在心里衡量这么长的时间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并努力去理解这一奇特思想的时候,他感到可撒尼德在自己头脑里寻找相似的知识,好找出个表达方式能让克娄明白他的意思,最后:“在经过了35亿年后,在我体内没有一个原子能保持不变——每一个都会不断再生!记忆?你能记得起你在地球上出生的第一个星期里的事吗?听着,在我看来就像是你们星球昨天的地球历史中,很多民族都说拉丁语——可如今还有谁会说?恐怕只剩下几位学者在揣测这古老的语言了吧,也许他们当中有人已接近成功了。古埃及人建造了大金字塔,可今天有谁能告诉我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建造的?你们的学者又是只能揣测。事实上,你们最近才重新找到了古埃及文字!元老神们化身人形,降临几间与人间女子结合,使人类变得更加强大。你们人类当中又有哪位记得这件事?没有人记得,只有模糊的传说回响在你们中间。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片土地上却有巨人存在过。是的,我已经忘记了!”
克娄极其敏锐的头脑还是无法接受:“难道没有记录吗?”
“记录?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我的思想像古老的书籍或是什么录音带的密纹唱片,泰特斯·克娄!最好的记忆水晶也会在10亿年里化为沙土。金属会变形,沙土会变成石头,转而又被蚀化为沙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就连整个世界也可能轮回一圈了!记录会消失,会被遗忘,抹煞,腐蚀,绝迹。现在,连我们也和人类一样生活在神话和传话中了……”
“除了恩何拉蒂之外……”
“对,可以说在每一万年中它们只是‘生存’了几个小时。它们的思想还处在未受侵蚀、未被破坏的原始状态。它们记得那个年代的每一件事,而且有关传说就铭刻在它们封闭的牢门上。”
突然,克娄感到自己在这位伟大的神灵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脆弱,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的民族有史以来所能学到的东西还远远不及您实际遗忘的多,”克娄喃喃地说道,“您告诉我该干些什么?”
这时可撒尼德告诉了他将如何“使用”德·玛里尼。克娄也许会反驳,会拒绝。他的朋友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但不管怎样亨利总还是有一线成功的希望的,他本人也曾冒着如此大的风险,通过套式轨道活着到达了目的地;正如可撒尼德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正规的通道能抵达伊利西亚。
克娄思忖了许久才最后点了点头说:“我会借助您的尚思找到德·玛里尼的,可撒尼德,是的,我要告诉他我必须告诉他的内容。”
只见这位高人长出了一口气,严肃地点了点说:“我真该好好谢谢你,泰特斯·克娄。事实上,整个伊利西亚都要感谢你。在你出发前,我们必须发出信号。你就先呆在我身边,听听我对信使们要说的话,然后,我会发出思维感应波,将你的虚拟影像和思想带到波利亚去。”
可撒尼德一动,那个幕帘便“沙沙”地打了开来,外面大厅里人群的喧哗之声一下子便涌了进来。然后,可撒尼德点了其中某些人,让他们走上前来……
……过了一会儿,四位信使便走出了水晶宫,马上起程前往伊利西亚的各个地区。他们当中有一位是泰特斯·克娄先前在人群中注意到的热神,另一位是长着一对薄翼、长得像昆虫的生物,它们的生命虽很短暂,但他却身负重任,携带刚才可撒尼德临时准备好的记忆水晶;这两个本身具有飞行能力的人都朝着高耸的蓝山脚下的时钟通道飞去。
另外两名信使,一位就是蒂安妮娅本人——她要骑着奥斯·莱斯飞到尼玛拉花园的神树那里。还有一位是埃氏的德奇·奇斯的学生,专门研究密码和巫师们的神秘对话,他的任务是乘坐反重力飞行器到达位于伊利西亚最上层空间里阿尔达塔·埃尔的球形巢层。
在时钟飞船通道里,热神在一个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巨大玻璃时钟飞船前停了下来。钟的圆盘上有四个古怪的指针,每一个指针的针尖都装饰着黄金,使它们看上去十分醒目,在这刻满了象形文字的圆盘上的运动更加令人琢磨不透——这类装置都是这样。热神最后想了想它们的指令;他要一字不差地向外传达可撒尼德的讯息,直到这件与元老神有关的事件完成为止,否则,他也许永远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伊利西亚。
一切办好之后,热神打开时钟飞船,进入其中,跃出了地下通道,冲上蓝山,在伊利西亚的高空中,一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目的地很远,远在宇宙的最深处……
那个柔弱的昆虫精灵选用的时钟是一个只有9英寸宽的灰色金属管道——它实际的传输能力比看上去强得多,除了任何飞船都有的4个弯弯曲曲的古怪指针外,这架飞船看上去可以说是毫无特色而言——在飞船里用笛子般的声音发出了一连串指令,然后将可撒尼德的记忆水晶往前一放,这架飞船竞神奇般地接受了指令。这个不起眼的铅灰色管道实际上是个非常特别的飞船:它能作用于一切会做梦的生物的潜意识世界,而不是像普通的飞船那样要在时空连续体中传送实体物品。说白了,这是一架专门跨越时空、传送梦想的飞船,是统领许多梦谷精神世界的机械领袖,而且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寻找并将它的货物传送至另一个机械,昆虫的指令刚被确认,就见这灰色的立方体变得越来越柔软,透明,最后竟化为一阵疾风,昆虫在确定了一切运作正常后便展开蝉翼出发了……
就在梦想时钟飞跃伊利西亚的意识世界,高高地飞行在城市和田野上空的时候,埃氏的得意弟子到达了阿尔达塔。
埃尔隐居所——那个银白色的球体。这个长着鸡冠状脑袋的德奇·奇斯将飞行器驶进这个漂浮在空中,有着光亮外表的球体,并将飞行器停在那儿,然后伸出退化了的翅膀,并用末端的枯指轻轻地敲了敲弧形的银色镶面板。
过了一会儿,只听那个球体用三种人工创造的语言,悲伤地同时问道:“谁在敲呀?”
好在这三门语言德奇·奇斯都懂。
“没有人。”德奇·奇斯知道阿尔达塔·埃尔非常喜欢这种猜谜游戏,所以立即也用相同的三种语言答道。
“没人敲门?那么是谁在用三种语言跟我说话?好,因为我并不在这里,请保持平稳状态。”
由于可撒厄德已事先通知了他阿尔达塔·埃尔不在家(至少是“部分”不在家),所以德奇·奇斯不迟疑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兵,这一点我想您也很清楚。但是术士,我带来的信却是出自一个大人物之手。”
这次德奇·奇斯只用了一种语言,就是伊利西亚流行的地球上的英语。
“那么我和这位大人物熟吗?”
“您是想让我说出来呢还是您自己先猜猜?”
“如果你愿意,就直说吧。”
德奇·奇斯知道这样做更能取悦阿尔达塔·埃尔,就说:“非常乐意。如果说您的头上戴着一顶象征无边法力的锥状白色巫术之帽,那么他所戴的就是无限仁慈与恩惠的王冠。”
球体里传来了阿尔达塔·埃尔的声音:“可我从来不戴帽子,而且他也一样。”球体继续若有所思地说道:“嗯!他是显赫的伟人,他向外派遣信使去执行他的命令;他是个好人,如果他真的戴着一顶王冠,那么它必定是充满善意的一个。啊!你看线索这么多——还有一个换音词!‘仁慈的桂冠’,没错!可撒尼德!”
“太棒了!”德奇·奇斯大声喊道。
“还没完,”球体说道,“你是个德奇·奇斯族人,而且想必是埃氏大师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这是个很简单的推理:除了德奇·奇斯人外,谁还能通晓这么多种语言,而且还能如此淋漓尽致地模仿巫师们的怪异发音?哦,你是德奇·奇斯,没错,但你不是那位大师,因为你出的谜语很一般,可他出的却总是极其高深。”
“是的,可我也一直在努力呀。”来访者耸了耸肩答道。
“事实上,你已远远超出常人了,”球体以阿尔达塔·埃尔的名义点了点头,“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弯曲的镶面板向外张开,并形成了一个装有阶梯的坡道,德奇·奇斯二话没说就爬了上去。
“请随意,”那个机械般的声音还在继续着,这时德奇·奇斯那半人半鸟的身影出现在通往入口的一条明亮的金属走廊上,“正如你事先就知道的,我不在家也就无法亲自欢迎你了。”
“不太可能在家,”来访者回答,说着到达阿尔达塔·埃尔的内室,“暂时还不可能在家。不过请告诉我:既然你不在家,现在到底在哪儿?”
“我现在正在埃克西奥尔·克穆尔的住宅里玩神秘预测取乐呢;他曾是原始地球后塞姆何佳时期的魔法师,现在是仙女座的里特之神……”
“请向你的朋友转达问候,”德奇·奇斯一边迷惑地凝视着四周,一边说,“请转告他如果有朝一日他需要一个半吊子语言学家——”
“什么?”阿尔达塔·埃尔轻笑起来,“不会吧,当你们的远祖还在始祖鸟的巢窝里等着孵化的时候,埃克西奥尔·克穆尔就已经在进行探索行星奥秘的工作了!好了,说吧,是什么让你现在变得如此局促不安?”
德奇·奇斯好像是吞东西似的回答:“只有这个,看上去毕竟您身体的绝大部分还是在这里!”
在这间核心房屋的中央处,上面吊着这个术士的躯体,他的衣服随意地飘动着,好像失去了重力一般,他的周围飘浮着许多能放射出祖母绿般的光芒的球体,将他笼罩在一片绿色的雾霭之中。阿尔达塔·埃尔足有8英尺高,可却瘦得像根棍子,在他那飘着的铜红色网状袍子里尤为明显。面容看上去还算年轻,但毛发已经花白,而且皮肤也像死人一样苍白;双眼紧闭,深陷在紫色的眼睑之下,就像死尸一样。
阿尔达塔·埃尔的手有六指,手掌的内外侧各长有一个拇指;长长的手指上长着如蜡般洁白的指甲的尖部却都被漆成了黑色。下巴和鼻子尖尖的,脚上穿的铜黄色网状拖鞋在趾部蜷曲着。
他的胸膛好像是纹丝不动,就算是有起伏,也缓慢得令人不易觉察,从他的嘴唇上也看不出有任何的气息进出,他看上去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但是,“我想请你区别对待,”不知从哪儿又传来了那机械般的声音,着实把德奇·奇斯吓了一大跳,‘你一定是想知道我的那一小部分在哪儿,对吧?斜躺在这里的这具壳只是阿尔达塔·埃尔的肉体。而他的思维——也是他更伟大真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