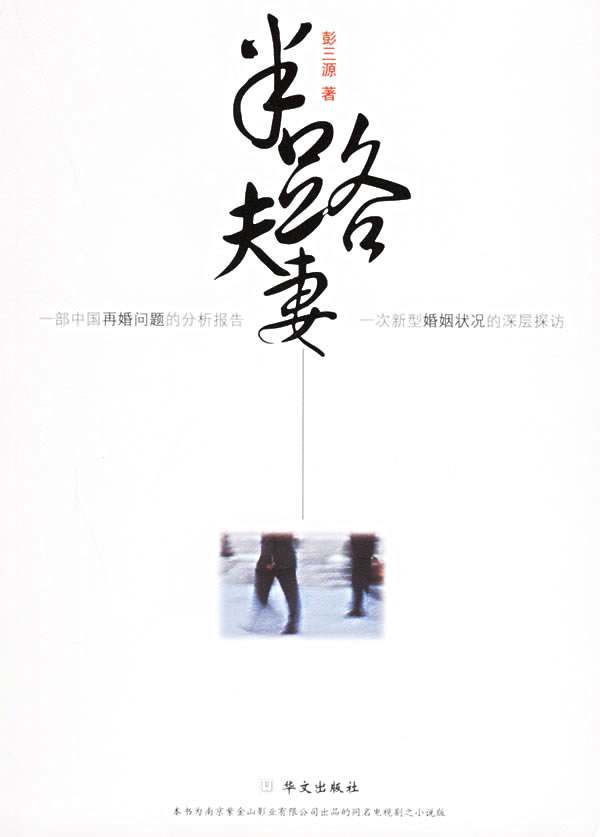这一半-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几个姑娘甩胳膊扔腿狂舞了一气,一个鲜红高挑的女人没头没脑地走了上来,她一登台台下响起了一片欢呼与唿哨。二管家把两只手举得很高,带头鼓起了巴掌。二管家低下头小声对我说:〃小金宝!〃我望着舞台上这个叫小金宝的女人,从头到脚就觉得她是假的,不像人。她的长发歪在一边,零零挂挂的,藤蔓一样旋转着下来,她对着台下弄出一个微笑。在另一阵欢呼中她把两片红唇就到了麦克风前。她的歌声和她的腰肢一样摇摆不定,歌词我听不清楚,只有一句有个大概,好像在说谁,〃假正经,你这个假正经〃,这句话小金宝唱了十几遍,整个大厅里就听见她一个人在哼,〃假正经,你这个假正经……〃
客人们三三两两走进了乐池。台上的姑娘们舞得也格外起劲。二管家的脸上一直保持了微笑,他不停地喝,很突然地向我侧过身。
〃小东西,王八咬过你没有?〃
二管家的话在大厅里极不清晰,我几乎没有听见。二管家不高兴地放下杯子,伸出右手把我的脑袋扭转过来,让我与他面对。二管家大声说:〃你有没有被王八咬过?〃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茫然地望了他一眼,又把头转过去了。
二管家再一次伸出手,把我的脑袋拨向他自己,他的嘴靠过来,嘴里的热气喷得我一脸。〃你真欠这顿咬!〃他点点头说,〃听我说小子,王八咬住你,你千万不能动,就让它咬着,你越动,它咬得越紧。把那阵疼熬过去,时间一长,它自己就松下去了。〃
我恍恍惚惚地点了一回头。二管家用指甲弹着玻璃杯,用一种怪异的神情盯着我。〃你要让她高兴,就好办了。老爷包了她,她就有法子让老爷高兴,老爷一高兴,她就成歌舞皇后了。在上海不论什么事,只要老爷高兴,就好办了。〃二管家点上一支烟,点烟时二管家自语说:〃在歌厅里给老爷挣钱,到了床上给老爷省钱,她就是会用二斤豆腐哄着老爷上床……〃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但我听出来了,老爷喜欢吃豆腐,我回过头去,大声说:〃等我开了豆腐店,我天天供老爷吃豆腐。〃
二管家愣了一下,叼了香烟懒洋洋地把眼珠子移向了我,他笑起来,没有声音,胸口一鼓一鼓的。他笑的时候叼香烟的嘴角一高一低,有点怪,显得下流淫荡。二管家摸摸我的头,说:〃傻瓜姓了唐也会变得机灵……豆腐你还是自己吃吧。老爷的事,有人伺候。〃二管家的目光把小金宝从头到脚又摸了一把,对今天的一切都很满意。
小金宝在台上一曲终了。她倒了身子,裙子的岔口正对了台下,她的目光骚烘烘地从这只眼角移到那边的眼角,均匀地撒给每一个活蹦乱跳的男人。
二管家把香烟架在烟缸上,站起身说:〃跟我来,到后台去。〃
这个叫小金宝的女人把我的一生都赔进去了。人这东西,有意思。本来驴头不对马嘴,八杆子打不着,说不准哪一天你就碰上了。我和小金宝就是碰上了。恩恩怨怨也就齐了。我的上海故事,说到底就是我和小金宝的故事。我怕这个女人。那时候我也恨这个女人,长大了我才弄明白,这女人其实可怜,还不如我。珠光宝气的女人要么不可怜,要可怜就是太可怜。怎么说〃红颜薄命〃呢。老爷花钱包了她,在上海滩她好歹也是〃逍遥城〃的小老板,其实她能做的事就两样,就是二管家说的,在逍遥城给老爷赚钱,在床上给老爷省钱。后来我和她一起押到了乡下,我们像姐弟那样好了两天,我对她一好就把她害了。我想救她,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出口就要了她的命。在唐家做事就这样,一句话错了有时就是一条命,现的。立马就让你看见尸。小金宝就这个命,多少人作践她,她自己也作践自己,没事,一有人对她好,灭顶之灾就来了。她就这个命。
小金宝没有死在上海。她死在那个小孤岛上。她把那把刀子插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了。我就在门外,我被她关在门外,只过了一会儿血从门槛下面的缝隙里溢了出来。我用手捂住门槛,捂住血,对她大叫说:〃姐,你别流血了,姐,你别流血了。〃她不听我的话。她的血也不听我的话。她的血和她的年纪一样年轻,和她的性子一样任性,由了性子往外涌,灿烂烂地又鲜又红。血开始滚烫,有些灼手,在夏末汹涌着热气,后来越洇越大,越铺越黏,慢慢全冷掉了。我张着一双血手叫来了老爷,老爷一眼就明白了。他显得很不高兴。老爷嘟囔说:〃我可以不让人活,就是没法不让人死。〃
你信不信梦?我信。几十年来小金宝反反复复对我说一句话,她总是说:〃我要回家。〃这是她死前最后一晚对我说过的话。梦里头小金宝披了长发,上衣还是翠花嫂的那件寡妇服,蓝底子滚了白边。我就没问一句:〃你家到底在哪儿?〃我那时不问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她答不出。我一直想在梦里头好好问问她。我一问,梦就醒了。梦是一条通了人性的狗,该叫的时候叫,不该叫的时候它就是不叫。我想来想去最后把她的骨头迁到了我的老家,埋在一棵桑树底下。桑树可是她最喜欢的树。我去迁坟的那一天是个秋天,没有太阳。小孤岛上芦苇全死了,芦苇花却开得轰轰烈烈。芦苇花就这样,死了比活着更精神,白花花的一大片。秋风一吹,看了就揪心。岛上的小树一直没有长大,秃了,上头停了几只乌鸦。我刨开地,小金宝的骨头一块一块全出来了。她手腕上的手镯还在呢。我坚信小金宝埋到土里的时候还没有死透,她的手像竹子,一节一节,散了,但弓得很厉害,两只手里都捏着大土块。我坚信她没有死透。当年上海滩上的一代佳人,而今就剩了一张架子,白的。大骨头都糠了。我把小金宝的骷髅捧在手上,闻到了几十年前的腥味。脑子里全是她活着的样子。她在我的脑子里风情万种,一眨眼,就成骷髅了。一张脸只剩下七个洞,牙咬得紧紧的,一颗对了一颗,个顶个。世上万般事,全是一眨眼。灯红酒绿,掉过头去就是黄土青骨。大上海也好,小乡村也好,你给我过好了,是真本事,真功夫。小金宝就是太浑,没明白这个理,自己把自己套住了,结成了死扣。
二管家带领我走向后台。过道又狭又暗,只有一盏低瓦路灯。刚才台上的一群姑娘叽叽喳喳下台了。她们在台上很漂亮,但从我身边走过时她们的脸浓涂艳抹,像一群女鬼。我有些怕,脚底下又没深浅了。
二管家用中指指关节敲响了后台化妆室的木门。他敲门时极多余地弯下了背脊,这一细小的身体变化被我看在了眼里。〃进来。〃里头说。二管家用力握紧了镀镍把手。小心地转动。小心地推开。小心地走进去。
〃叫小姐!〃二管家一进门脸就变了,长了三寸。〃叫小姐!〃他这样命令我。小金宝半躺在椅子上,两条腿搁在化妆台边,叉得很开,腿和腿之间是一盒烟与一只金色打火机,她胡乱地把头上的饰物抹下来,在手里颠了一把,扔到镜子上,又被镜子反弹回来,尔后她倒好酒。我说:〃小姐。〃小金宝没理我,却在镜子里盯着门口的一位女招待。小金宝说:〃过来。〃女招待走到小金宝面前,两只手平放在小肚子前面。小金宝点点头,说:〃转过身去。〃女招待十分紧张地转过了身。〃嗯。〃小金宝说,〃身腰是不错,出落出来了。〃小金宝摸摸女招待的屁股说,〃难怪客人要动手动脚的。〃〃……小姐。〃女招待惶恐地说。〃刚才没白摸你吧?〃小金宝说,她猛地把手伸到女招待的乳罩里头,抠出一块袁大头,小金宝盯着女招待,眼里发出来的光芒类似于夏夜里的发情母猫。〃别说你藏这儿,你藏多深我也能给你抠出来!〃〃小姐。〃女招待拖了哭腔说。小金宝用袁大头敲敲女招待的屁股说:〃你记好了,屁股是你的,可在我这儿给人摸,这个得归我,这是规矩!〃小金宝把洋钱重新塞到女招待的乳罩里去,脸上却笑起来,说:〃你是第一次……〃女招待连忙讨好地叫了声小姐。〃但我也不能坏了我的规矩,〃小金宝敛了笑说,〃这个月的工资给你扣了,长长你的记性……去吧。〃
女招待刚走小金宝就回过头,瞟了我一眼,自语说:〃这回换了个小公鸡。〃小金宝端起酒杯,在镜子里望着我,她的目光和玻璃一样阴冷冰凉,但她在笑。〃过来。〃这回是对我说的。
我往前走一步,踩在了一件头饰上,紧张地挪了挪脚步。小金宝伸出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的手冰凉,好像是从冬天带到夏天里来的。我的脖子缩了一下,僵在了那里。她的大拇指摸着我的喉头,上下滑了一遭,问:〃十三还是十四?〃
〃十四。〃二管家在后头说。
〃十四,〃小金宝怪异地看着我,〃……和女人睡过觉没有?〃
〃小姐……〃二管家十分紧张地说。
〃睡过。〃我愣头愣脑地说。〃谁?〃小金宝的头靠过来,小声说,〃和谁?〃
〃小时候,和我妈。〃
小金宝很开心地重复说:〃哦,小时候,和你妈。〃小金宝扬起眉头问:〃姓什么?〃
〃姓唐。〃二管家又抢着回答说。
〃姓什么?〃小金宝迅速地掉过头,〃……让他自己说!〃
〃姓唐,〃我咽下一口口水,回答说,〃我姓唐。〃
小金宝说:〃你姓唐。〃她把唐字拉得很长。小金宝说:〃从今天起,你就叫臭蛋。〃
〃我不叫臭蛋,我叫……〃
〃我让你叫什么你就叫什么!〃
小金宝望着我,她总是那样笑,似是而非,似有若无的样子。〃我喜欢这孩子。〃她说。小金宝背过身去,把手指伸到了酒杯里去,她在喝酒的瞬间看见二管家松了口气,小金宝拿起打火机,不经意地在火芯上滴上葡萄酒,然后盖好,放回原处,拿了根香烟夹在指缝里。小金宝面色和悦地坐下去,说:〃给我点根烟。〃
我站在那儿,愣了半天,说:〃洋火在哪儿?〃小金宝用夹烟的两只指头指向打火机,说:〃那儿。〃
我取过金黄色打火机,听见二管家在身后说:〃这是打火机。〃我把打火机正反看了几遍,却无从下手。二管家走上来,看了小金宝一眼,手脚却僵住了,慢慢收了回去。我打开盖子,盖子却掉到了地上。小金宝又笑起来,伸出手把打火机塞到我的左手上,再拽过我右手的大拇指,摁在火石磨轮上,猛一用力,打火机立即闪了一下。我的手像撕开了一样,疼得厉害。小金宝回过头对二管家说:〃这孩子灵,一学就会。〃我把大拇指放到了唇边吮了吮,望着小金宝。小金宝说:〃给我点烟。〃
我伸出大拇指一遍又一遍搓动磨轮,火石花伴随着搓动的声响阵阵闪烁,我一连打了十几下,看了看自己的大拇指,又看看小金宝。小金宝目光汹汹。
二管家从身上掏出洋火,慌张地划着了,他把那根小火苗送到了小金宝的面前。
小金宝没动,就那么盯着我紊乱的指头,脸上挂了一种极其古怪的喜悦。她用余光看着洋火上的火苗一点一点黯淡下去,一直烧到二管家的指尖。
我额上的小汗芽如雨后的笋尖蹦了出来,那只金黄色打火机掉在了地上。我捏紧了大拇指,抬起眼,眼眶里的泪花忽愣忽愣地闪烁。
二管家慌忙拣起打火机,对我大声训斥说:〃你他妈怎么弄的?你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小赤佬,你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