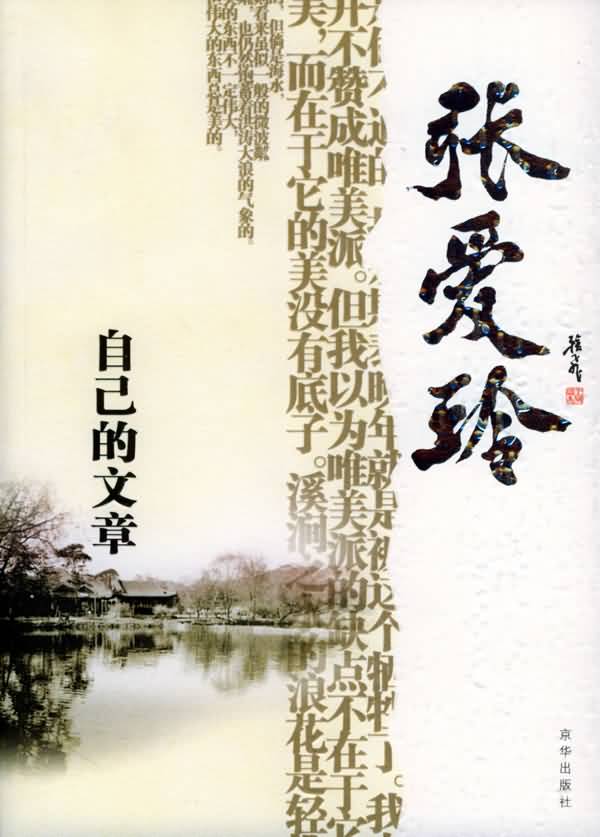石康文集-第2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行,我就是冲着漂亮去的,要连我媳妇都不如,我不操,叫她们丫没生意。”
“这要求不高,估计那儿的姑娘能满足你——”
“我告诉你,我喜欢那种瘦瘦的,白白的,小小的,软软的,皮肤嫩嫩的,眼睛大大的,屁股圆圆的,头发黑黑的——”
“小腿儿细细的,阴道紧紧的——去你妈的,不就是幼女型的吗?”
“对啊——我就喜欢小逼——”
“你丫真够禽兽的。”
“我操,你丫装什么正经呀——”
“我不是装正经,我是对你那爱好不感兴趣,这样吧,要是有你说的那种姑娘,你操她,我把她妈叫来——”
“我操!”赵东平眼睛里猛地闪出兴奋的火花,“我——操!——咱们走吧。”
“我不去,没兴趣。”
“又装!”
“我没带那么多钱,要不你先借我点儿?”
这句话总算刺中了赵东平的要害,他立刻化兴奋为沉默,化沉默为顾左右而言它,化顾左右而言它为看我的剧本,化看我的剧本为匆匆离去——真是太棒了!
我关上他慌慌张张走时没有关上的门,回到椅子边坐下,重新面对笔记本,我点上一支烟,看看表,已经快十点了,陈小露的电话还没有打来。
我来到电话前,抓起电话,只按了几个键就放下,然后回到笔记本边,准备把刚写的看一遍,洗手间的门开了,传出陈小露学赵东平的声音:“我操——你丫装什么正经呀——我操——咱们走吧——我操——又装!”然后是她略带沙哑的出自天仙之口的笑声。
我回头,眼前的情形叫我大吃一惊,陈小露一丝不挂,光着脚,右手捏着她的真丝胸罩儿和内裤,左手拎着她的漆皮小背包,带着墨镜,从洗手间晃晃悠悠走出来,先是锁了房门,然后走到我面前:“你信不信,我就是这么来的?”
我盯着她,热血上涌,几乎瘫在椅子上。
陈小露走到我面前,经过我,走到床边,把手里的东西扔到床上,墨镜也摘下,又走到窗边,把留有一条缝儿的窗帘拉严,然后转过身,再次学着赵东平的腔调说:“我告诉你,我喜欢那种瘦瘦的,白白的,小小的,软软的,皮肤嫩嫩的,眼睛大大的,屁股圆圆的,头发黑黑的——小腿儿细细的,阴道紧紧的——小逼!”
她一边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把手做成兰花指的式样,拿着戏曲份儿(她以前学过),依次指着自己身体上被说到的各个部位,迎着我火辣辣的目光,走到我近前,在我向她伸出手去,就要够到她的一刹那,抬手给了我一记耳光:“去你妈的,看什么看!”
我刚要说什么,她用手一指洗手间:“你去对着镜子看看,看看你那一脸馋相儿,像作家吗像作家吗?你的严肃呢,你的深沉呢,你的话语权呢,你的灵感呢,我告你,今儿你非得给我做出个才气横溢的样子才行,要不老娘就不让你近身——”话音未落,一头栽到床上,迅速钻进被单,只露一个脑袋在外面,“别怕,你消费得起——今晚我大减价,来吧——”
对于这样的姑娘,你能说她什么呢?说她可爱?说她特别?说她聪明伶俐?说她漂亮迷人?说她妖里妖气?说她令人兴奋?说她不同凡响?我不知道,我想不出,我无法用语言形容,这是另一种花朵,鲜艳夺目,亮丽无比,就像炸开的五光十色的焰火一样叫人叹为观止,她所展示的大胆粗俗和下流是那么得体,所有经她表现出来的一切都自然而然,生动有趣,完美无缺——除了叫她天仙以外,我想不到还有更恰当的称呼。
以后的事情我记不住了,但有一件我记得,在她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由于心慌意乱,差点接着问出“多少钱”这句话来。
94
“你必须给我表演坐怀不乱,必须表演,现在就演,马上就演,立刻就演——来来来——别构思啊别构思,再构就假了——”
已经是后半夜了,陈小露还在跟我逗,她似乎是一台永不休止的发动机,可以没完没了地飞速转动,这是另一个迷人的陈小露,说实话,我早就被她完全弄晕了。
但是,光把我弄晕对她来讲还远远不够,她还要与我谈论别的东西,因此,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每人都两眼布满血丝,却一点睡意也没有,还在没完没了地聊天,我躺在床上,抽着烟,她躺在我旁边,头枕在我胸前,手指不是摆弄放在我肚皮上的烟灰缸,就是在我胸前划来划去。
“你知道吗,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这是谁说的?”她问。
“TS艾略特。”我答道。
“风吹得很轻快,吹送我回家走,爱尔兰的小孩,你在哪里逗留?——这是谁?”
“TS艾略特。”
“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这是谁?”
“TS艾略特?”
“今晚我精神很坏,是的,很坏,陪着我。跟我说话。为什么总不说话。说啊。你在想什么,想什么?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是谁?”
“不知道。”
“还作家呢——这都不知道,告诉你吧——还是TS艾略特。”
“我也喜欢过艾略特。”
“又装。”
“我讨厌女诗人。”
“你骗我。”
“写东西的女的里面我喜欢吴尔夫,她后来疯了,跳河自杀——”
“还有女的自杀吗?”
“我记不得了。”
“女的就是不行,连自杀都比男的差——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会自杀也不一定会写文章。”
“同性恋呢?”
“我喜欢的作家大多是同性恋。”
“谁是同性恋呀?有谁呀?”
“毛姆就是。”
“还有呢?”
“纪德。”
“还有呢?”
“多了去了——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是同性恋?”
“当然了,不仅同性恋,还是受虐待狂呢,据说,他晚上老找纪德聊同性恋的事儿,也许在王尔德快死的时候还去看过王尔德。”
“讲讲,讲讲。”
“我都记不得了。”
“他们怎么同性恋呀?”
“我又不是,怎么知道?”
“你想想,想想嘛——普鲁斯特怎么同性恋?”
“据说,他弄几个男妓关在他的房间里,白天也不许走,谁要是走,就得向他请假,讲明理由,有的小男孩受不了跟他在一起,账也不结,就跑了,他就会感到非常悲伤,于是就把悲伤写在小说里,据说,为了写出真情实感,他才这样做的。”
“真的?”
“我是在他传记里看的。”
“你爱看王朔吗?”
“王朔的书我看过一半吧。”
“怎么样?”
“够贫的。”
“你说王朔是同性恋吗?”
“不知道,没听人说起过。”
“我上学的时候,特爱看王朔小说,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睡我上铺,看王朔简直看疯了,一会儿哭一会笑,跟个疯子似的,她长得挺漂亮的,那时候她要是遇上王朔,肯定会跟他睡觉,你信吗?”
“我不知道。”
“你以后不许写王朔那种书骗小姑娘,听见了吗?”
“我不会写他那种书。”
“我告诉你啊——你应该写村上春树那种,你看过村上春树吗?”
“看过《跳跳跳》。”
“《挪威森林》你没看?”
“我有,还没来得及看。”
“回去看,回去看,特来劲,真的特来劲。”
“我现在很少看小说,我写剧本,小说写的很少。”
“别写剧本了,写剧本不好,你应该写小说。”
“写小说无法生活。”
“你真没出息。”
“没办法。”
“没办法也要写小说。”
“钱怎么办?”
“借呀——笨蛋。”
“开始还可能有人借你,时间长了,就没戏了。”
“我借你,只要你写小说——他们说你会写小说。”
“我想想吧。”
“我从小就想跟作家混,看着他写小说。”
“你够怪的。”
“我告诉你,要是你写小说,我就帮你找编辑发表。”
“你想什么呢——编辑怎么会听你的?”
“笨蛋,我跟他睡觉呀!——他要是不发,我就跟他睡觉,看他发不发——”
“要是编辑是女的呢?”
“笨蛋!找男编辑啊!”
“我觉得你干得出来。”
“是——我干得出来,这对我太容易了。”
“你别这样——你要是跟编辑睡觉,我就不写小说了。”
“那好吧,你要是觉得用不着我,就自己跟他们睡吧。”
“我?——算了吧。”
“你放心吧,我就是跟编辑睡了,也不会告诉你。”
“你——你为什么要让我写小说呢?”
“如果连小说都不写,那活着还有什么劲呀!”
“要是你愿意跟我一起混,我就写小说。”
“真的?”
“真的。”
“你说话算数啊。”
“我不会骗你。”
“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你就跟你睡觉吧——我读过你的小说,你写的长篇我在大庆家看过,是我让大庆把你介绍给我的——不知为什么,看了你写的小说就想跟你睡觉。”
“你这人太怪了。”
“你是怎么开始写小说的?”
“说起来话长。”
“说说。说说。”
“我上高中时,和外校的一个女孩混,我给她写诗,后来,开始写小说,有一天,她对我说,现在你小,是我的小作家,你属于我,以后等你长大了,成了大作家,就不属于我了。她的话虽然听起来很酸,却让我很感动,就开始写了。”
“她呢?”
“谁?”
“跟你说这话的女孩?”
“早跟我掰了。”
“为什么?”
“看不上我呗。”
“是你甩的人家吧?”
“不是。”
“又骗我——你能不能对我说点真话。”
“我没骗你。”
“哎,我问你,她是不是你写的阿莱呀?”
“不是。”
“那她后来怎么样了?”
“一上大学就掰了。”
“那阿莱呢?”
“那是我上大学认识的。”
“她漂亮吗?”
“一般。”
“你喜欢她吗?”
“那当然。”
“她为什么不跟你好了呢?”
“是我甩了她。”
“又骗人。”
“我没骗你,我说过,我不会骗你——”
“那么,以后我也不会骗你。”
“……”
95
那个在饭店客房里的夜晚,我认为是个了不起的夜晚,我永远不会忘记。
96
一切都是偶然的,就像是愿望达成,就像忘记失望,就像被踩死在行人脚下的蚂蚁,就像与行星相撞的彗星,就像盛开的红玫瑰,就像被风吹散的晚霞,就像被云遮住的月亮,就像身边的地狱。
如果我不会回忆,不会阅读由文字书写的历史,不会观察现实,就会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偶然便失去力量,多少次,在梦中,我仿佛置身于一团飞速旋转的火球之内,突然之间,火熄灭了,我被烧成了一股随风飘扬的轻烟,我洋洋洒洒、我茫茫然然,我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