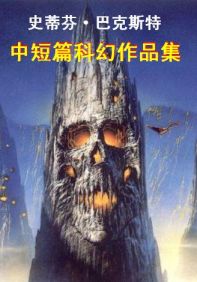贾平凹作品集-第2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偏又有一妇人提了猪头过来,见了狗又说是她家的,走失好几个月了,正到处寻找不见。演员们就和这一男一女争辩,这一男一女也争吵不休,窄窄的街巷拥了许多人,演员们就说:“你们不能这么钻了钱眼!你们说狗是你们的,有什么根据?”那男人就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饼逗引狗,狗跟了过去;女人也就用猪头逗引狗,狗又跑了过去。一个演员急了,飞脚赶回村找导演商量:电影正拍到紧要处,怎么能随便没了这条狗?于是,导演又叫上几个女演员牵了小母狗“爱爱”,一起赶到镇街说:“拍电影有的是钱,但国家的钱也不是随便往外撤的,这样吧,你们两家都叫狗,我们也来叫,狗若跟了谁走,就是谁的。”于是,那男的又以饼招逗,女人又以猪头引诱,女演员们就牵了小“爱爱”走,阿黄就汪汪叫着,紧追“爱爱”不舍。人们哄地大笑,那男人便灰溜溜退走,钻进店铺里再不出来。店铺的花格子窗下,一个人影闪动,有个演员瞧见了就悄声对同伴说:“牛磨子在店里,是那老东西出的馊主意吧!”阿黄便对那店门汪汪狂吠,店门也便哗啦关了。
赶集回来,导演和演员们将认阿黄的事说给老大昕,老大说:“牛磨子的老表就在镇街上,他也太不像话了!以后少理这种人得了。”但是,在拍摄第六十四场戏时,地点无论如何要在牛磨子的庄宅那儿。第一天,导演让牛磨子充当一个群众角色,演毕,他竞提出要钱,每一个群众演员二元钱,他却坚持自己要三元,因为他不仅是群众,而且说了三句话。老大看不惯了,就说:“你家也是去挖了矿,钱总算不紧手吧,为一元钱,说得出口吗?”牛磨子说:“这是公家钱,又不是导演掏私包,阿黄都是高价买的,我不如一条狗了?”老大说:“胡搅蛮缠!不怕丢了自己人,可这个村的脸面还丢不起哩!”牛磨子便说:“我丢什么人了?我当了八年队长,我没给自己赚钱,我没勾引良家妇女!”出言不逊,老大就火了,问道:“你说话说明白,谁赚了谁的钱?谁勾引谁家妇女?”牛磨子说:“孙家女子的肚子大了,莫非是长了癌性瘤子?!”一句话说得老大血冲脸脖,叫道:“我和云云光明正大,结婚证都领了,谁一个屁都放不得!”他逼近牛磨子质问,牛磨子以为要打架了,当下就猫腰扑下,抱住了老大,又双手来捏老大的命根儿,先下手为强,且哭叫道:“你打呀,你小伙现在是不得了嘛,你当了矿长嘛!”导演忙拉开他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元钱给他,估计不能继续拍摄,就让司机装了器材返回。却不巧,车在拐弯时,竞轧死了牛磨子的没尾巴狗,牛磨子正没个出气的机会,当下就睡在了车轮下,
口口声声说是摄制组故意轧死了他家的狗。叫骂要砸车,要烧车,又骂出他的儿子和那“媳妇姐”,让他们拉住司机不放。司机就火了,将拖了他腿的牛磨子用力一甩,牛磨子滚倒一个坎上,鼻血流了下来,偏不擦,抹一脸红,大叫:“打人了!打死人了!”哭闹不止。
吵闹声惊动了全村,许多人跑来看,有说东的,有说西的。村长就赶来问了情况,也训斥司机无论怎样不能打人。老大便说:“这事我在场,不能怪司机。”牛磨子就说:“张老大,你这个汉奸卖国贼!摄制组给了你好处,你就处处向着人家,你这电影厂的狗啊!”导演两方劝止,最后说:“就算我们打了你,我们领你去镇医疗所看病吧,轧死了狗,我们赔你的!”牛磨子说:“怎么个赔法?”导演问:“你这狗值多少钱?”牛磨子说:“一百!”有人就叫道:“牛磨子你疯了,你那是什么天狗?!”牛磨子说:“你说不值,我也不要钱了,我要我原来的狗!”老大就对村长说:“你瞧瞧,咱的人像不像话?”村长却说:“老大,不是我说你呢,你挖矿不是也为着钱吗?牛磨子开的口是大,但咱本地人要向着本地人的。”老大说:“我开矿也确实为了挣钱,可我不是混钱!我要像他那么挣钱法儿,我一头碰死在石头上了!”村长就过去调解,达成协议:电影还是要拍,这是公家的事;但电影厂一定要注意群众关系,打了人就看病,以后类似事件绝不要发生;狗价二一添作五,五十元。这项协议气得老大满嘴冒白沫。
事件之后,摄制组一片埋怨,说这地方少文明,不开化,刁民太多,往后再也不肯多和本地人往来。除了张、孙两家常来驻地院落,别的人来了,演员们就冷言冷语相讥。时间一长,村人就又慢慢论起老大的不是。到了腊月二十三日,村子里逢着会日,挖矿队也放了假,人们有去走亲串友的,有去七里镇采
买年货的,有去九仙树下烧香敬神的。演员们下午拍摄几个镜头后.闲着无事,就在驻地院子里跳舞取乐,一对一对在那里翩翩旋转。村里就传出一股风:摄制组的人在一男一女抱着磨肚子了!闻者赶来瞧热闹,一个演员就关了院门。村人不得进去.隔门缝往里瞧,噢噢地哄,丢石砸门,那门终是不开。
二
老二远远地坐在山坡上,那里完全可以看得清摄制组的大院:他第一次看见城里人跳舞,心迷,眼迷,抑制不住的嫉妒和一种万般滋味的冲动。后来看到村人砸了一阵那紧关的大门,陆续骂骂咧咧散去,也感到了本地人的可怜和羞辱,就跑下山来.在矿洞那儿的土地上仰面躺下喘息。但那大院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音乐声,使他又不能静静地躺着,就如同狼一样地跳起来.拉了枯草枯树枝,在洞口燃起火,自个乱跳乱吼,发泄自己的冲动。这喊叫声,蹦跳声,使那些逗起了冲动却无法排泄的村中光棍汉,都跑了来,和老二一起乱跳。后来,他们就跳起往日过会时祭神驱邪的巫舞。已经是寒冷的暮晚,他们全脱了身上的棉衣,甩掉了帽子和包头巾,将那些废纸撕了条子,一条一条贴在脸上,举着钎子、镢头绕篝火堆跑。皆横眉竖眼,皆龇牙咧嘴,似神鬼附身,如痴如疯。旁边的人就使劲敲打铁器.发出“嗨!嗨!”吼声。后来就你从火这边跳过去,我又从火那边跳过来,用火灰抹脸,汗水流着,冲开灰土,脸恶得如煞神一般。这是性的冲动,原始的力的再现,竟将摄制组那边的音乐渐渐压下去,后来就无声无息。
已经是吃晚饭的时辰,家里的男劳力都没有回家,做好了饭的女人们听见了吼叫声,也跑来看热闹。一站在发了狂的男人面前.都吓得失了魂似的,但不久就陷入痴醉之中,于一旁为他们拍掌叫号。云云也来了,她的肚子明显地凸大,虽然穿着宽大的衣服,但还是看得出来。她叫喊了一阵,就觉得气堵,有几次那男人们跳过来,险些撞倒了她,赶忙蹲下去。双手紧紧地护住了肚子。也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了老大。老大是什么时候来的,她竟未发觉,这阵见他也加入了男人群中,大声地吼,拼命地跳。云云从来未见老大这么狂过,好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似乎比老二,比自己的弟弟光小还要野!后来就见老大突然用镢把将篝火堆一挑,火花飞溅,红焰蹿处老高,跳动的人都吃一惊,停下脚步。老大就叫道:“跳呀,都跳呀!”自已便跳了起来,却一下子摔倒了。云云大叫:“老大!老大!”老大并不理,从地上又跳起来,那膝盖处就印出一块红来。云云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把老大拉住了,拉出了人群,训道:“你是怎么啦?你是疯了?!”
老大说:“你让我跳吧,我跳一跳,喊一喊,心里就受活了!”
云云立即明白了老大也来又叫又跳的原因。多少日子来,他为着挖矿,为着这个村子,辛辛苦苦地干,忍气吞声地干,却总是磕磕绊绊被人误解,被人辱骂,她安慰过他,他总是又笑着劝她。那原来都是一种假象吗?那都是自己控制了自己,暗暗吞食了最大的痛苦,这一夜才是真真实实暴露了他的真人真性吗?云云看着老大,强忍着要掉下来的眼泪,说:“老大,你要觉得那样心里好受,我不挡你,你跳去吧。”
老大却突然把头埋下去,双手紧紧地抱着,像是抱着一个球,要拧下来,要抛出去,大声地吸动鼻子哽咽起来了。
夜越来越黑,篝火慢慢地没了光焰,火炭发着红光,后来就覆盖上一层灰白。乱跳乱叫的村人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像是卸了套的牛,下了竿的猴,没了一丝力气。清醒过来,又都恢复了往常的寡言少语的秉性,默默地站起来,站起来.蔫沓沓地走散,消失于深沉的巨大无比的黑暗中。
死寂的篝火残灰上,却出现了两点绿光,一个奇异的黑影慢慢大起来,雌麝作了寡妇之后,无依无靠,很是孤单,它决心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了。当它走下山,经过村子里,家家的门都关了.人在屋里发出鼾声。在经过矿洞时,它突然恶从胆生.用四蹄猛地把篝火残灰扬起,灰里的点点残火烧着了它的脚.燎焦了脚上的毛,但它还是把灰全扬了,将点点残火在它的一泡臭尿中浇灭去。也就在这么一阵疯狂之后,它感觉到了肚子痛,痛得剧烈,终于,将腹中的生灵落在灰土中。
“儿子!”雌麝暗叫了一声,脑子嗡嗡,昏了过去。等它醒来.残月已坐了西边山峰顶上。看着身边滚得满体血和灰的儿子.它没有气力再带儿子往别的地方去了。它望着远处的天峰和天峰的那座古堡,挣扎着起来,用嘴叼了儿子,一步步回到石洞去。
三
翌日.人们去矿洞施工,发现在狼藉一片的残灰里有一摊污血.血已经凝固了,和灰搅在一起,而那些小石头上,血红刺眼.上边沾满了麝毛。现象证明,这是在昨夜,又来过麝,是一只大麝.而且生了一只小麝!村人老少惊骇:麝已被打死了,两只.竟然还有麝在生新的一代。又不在山上生,不在河畔生,偏要到矿洞来生,这不能不是一桩怪事!
一时.逝去的往日的那种对麝的恐惧,又重袭××村,人人议论:难道电影厂的到来,并未抵消这凶灾吗?故谈麝色变,谁也不敢担保这村子会不会又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剃头匠自矿队建立后,一直负责拖拉机交运矿时的过秤、装卸,听到这可怕的流言,心里也阵阵发紧。他已经不止一次听见有人在非议自己的女儿,他也看出女儿的身子是比以前笨拙了许多,但他不敢问云云,也不敢问老母。他害怕如果老母什么也不知道时,突然说知,她会经受不住而气昏身亡。入冬来。她添了咳嗽病,几乎连炕也不敢下。现在,他立即将灾难联系到了老大身上,由老大又联系到了云云身上,就慌慌张张赶回来.坐在老母的炕头。老母说:“这么早就回来了,脸色这么难看的!”
剃头匠说:“没什么,云云呢?”老母说:“到老大那儿去了。”剃头匠说:“又去了!你要管管她,别让她疯疯张张的。”老母倒说:“箍盆子箍桶,能箍了人吗?”剃头匠说:“云云没给你说什么?”老母就奇怪了,问道:“什么事?”剃头匠难了半日,还是去将门掩了,偷声唤气地说:“娘,我说一句话,你可千万不要生气。我咋看云云身子不对了?这女子也大了,她和老大也是干柴见火……”没想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