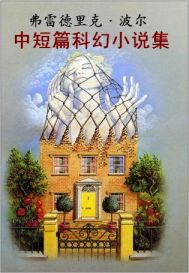台湾当代小说、散文精选集-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九岁那年春天,常闹肚子痛,吃过晚饭肚子痛就哭。由於我经常在夜里吵闹不肯睡,父母亲都不怎麽理我,
等到有一晚我又肚痛又发高烧,他们才请医生来看病。那英国医生来了,检查之後说,是急性盲肠炎,要马上到医
院去开刀。我听了,心惊肉跳,大声哭叫,心里想,我平常在床上吵闹说肚子痛,有时是夸张一点,这次真的闹出
事来了,完了,完了,可不可以自首,说我是哄哄大家的?无奈他们把我推进医生的汽车,直驶上海滩一家医院。
医生把罩子蒙在我鼻子上,滴下麻醉药,那药的气味难闻透顶,我用劲想把罩子拉开,但是医生紧按着不放。
手术台上有个电灯亮得很刺眼,好像过了很久,我才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那麻醉药的气味仍然在我肺里,我头昏,想吐,腹部被胶布绷得紧紧的。我想起昨夜的
经过,不禁眼泪滚滚而下。妈妈坐在床边,指看一个玻璃瓶给我看,里面装着我发炎的盲肠。我看了倒放心了。那
不是骗局。我果然患了急性盲肠炎。
下午爸爸带著姐姐妹妹来看我,他看见我非常沮丧的样子,就讲个笑话引我笑。谁料到笑起来肚子就痛,但是
不能不笑,真是啼笑皆非。妈妈说,〃 不要跟她讲笑话了。〃 爸爸才停止。
我在医院大约住了十天,等伤口痊愈,拆了线才回家。妈妈叫大师傅炖白鸽汤给我进补,黄妈对我特别好,喂
我吃豆腐乳拌鸡蛋面,非常好吃。起床走到浴室从窗子看出去,花园里的树木已经长出绿油油的叶子。我好像曾经
离家很久。回家真好。
再过些日子,我已经恢复降,肚皮上的伤口像一条蜈蚣,大约五寸长,一寸宽,红红的,左右有许多缝线留
下的疤子,像蜈蚣的脚。我跑到厨房拉起衣服让大家看。我相当得意。肚皮上有一条娱蚣,为我仅有。
从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夜里乱吵乱闹了。
9。我们要去美国!
中西女塾的学生装扮穿戴很讲究,桐姊、舜姊回家,妈妈时常带她们去绸缎庄挑衣料做旗袍,那时的大大小姐
们好像都有的是时间,慢慢地挑选衣料,和裁缝商量要做夹的还是单的,配什麽滚边,要什麽样子的钮扣,开叉要
多高。衣服做好,裁缝会亲自送来,哪里需要放大,哪里需要缩小,哪里做错了裁缝会用长长黄黄的指甲在衣料上
按上按做记号,口里轻轻说,「有数了,有数了。」无论妈妈和表姊们怎麽指摘他,他都毫无表情,一直细声说,
「有数了,有数了。」然後把旗袍包回去改。像那样的裁缝一定被女人指摘惯了,炉火纯青,所以脸上一点表情都
没有,但不知会不会有一天,像陈旧的飞机一样,由於金属疲劳,突然分裂,整个人垮了下去?
桐姊中西女塾没有毕业,便和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吴师基结婚,师基兄也是厦门人,他父亲是商人,他们在厦门
结婚之後,师基兄便帮他父亲做生意。
舜姊也没有毕业就出嫁了。宗惟贤是北京人,他在纽约任副领事,回国省亲时在交际场合遇到父母亲。母亲听
说他三十出头,还没有结婚,便介绍美丽的舜姊给他认识。不久之後,舜姊便时常打扮得漂漂亮亮,脸上抹著香香
的雪花膏和薄薄的脂粉,戴著玉耳环,坐在客厅等惟贤兄来接她出去看电影吃晚饭,宗惟贤一来,她的眼睛就亮起
来,两人大概是一见钟情。宗惟贤变成常客,他一来,黄妈就当他面说,「宗先生又来了!」大家笑哈哈地欢迎他。
惟贤兄和舜姊结婚之前,厦门来了青天霹雳的消息。外公的豫丰钱庄由於海外和内地来往的公司欠巨款不还,以致
倒闭。讨债者封了廖家的产业。妈妈和舜姊为家里人很伤心,舜姊夜夜躲在澡房里哭。
妈妈为舜姊预备许多要带去美国的东西。我从学校回来,就看见餐桌上摆著许多衣料,那长指甲的裁缝来来往
往赶著做新娘礼服和要带去美国的旗袍,家里热闹得使我忽略做功课。我在学校无论大考屑没有得过比「乙」等
低的分数,现在却连连来几个「丙」。「糟糕了」,我打著南京口腔对黄妈说,「我的成绩越来越坏了。」
「不要紧,」黄妈说。「等廖小姐结了婚,你再用功,成绩就会好起来。」
舜姊的婚礼是在一家酒店举行的,惟贤兄的父亲从苏州赶来。我和妹妹是花童,我们穿看粉红色的丝质西装,
技著短披肩,我取下眼镜,手拿花篮,走一步停一步,在红地毯上徐徐撒花瓣。舜姊结婚之後就上船去美国。大家
都哭得很厉害,因为不知道什麽时候才会再见面。
没想到,舜姊去了美国之後,过一年我们也去了。那是因为父亲所作的《 吾国与吾民》 在美国出版之後,被视
为关於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出版这本书的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和赛珍珠夫妇觉得父亲应该去美国走走。
父母亲决定举家到美国去住一年。我听说要坐大轮船去遥远的美国,非常惊讶。不必上觉民小学了!要离开亲
友,把佣人辞掉,家具寄存在二伯和六叔家里。有千头万绪的事要做,姐姐都帮妈妈的忙。她一向很听话,大家都
说她很像大人。爸爸为我们买了学校规定的课本,预备一年之後从美国回来我们可以插班。姐姐那时在工部局女中
读一年级。父母亲买了许多大箱子,除了衣服之外,爸爸要带去许多书。
妈妈非常高兴,理东西的时候唱起西洋歌来。大概是因为上海的社会很复杂;亲戚朋友多,也有许多麻烦。那
时,父亲在国内的名气已经非常之大,他创办的《 论语》 、《 人间世》 、《 宇宙风》 三种刊物为当时文学创新风格,
但也招来许多批评。《 人间世》 提倡发抒性灵的文章,而《 宇宙风》 则融汇《 论语》 、《 人间世》 的气质而无逊。
母亲觉得到美国去走一趟是好的。
外婆知道我们要去美国,就托人带来肉松让我们带去美国吃。父亲说,去美国别的可以带,却不可带肉松。妈
妈不相信,大声说,「怎样不能带肉松?」
「美国海关不准外国肉类进口,说是怕有微菌,带进传染病。」爸爸说。
「肉松怎麽会有微菌,带传染病?」妈妈惊叫起来,一时动摇了她去美国的决心。「我们把外国人叫做番仔,
实在有道理!」
我不能想象到美国去住会是什麽样子。在外滩,我看见过那些庄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里面是外国人开的大银行、
大商行和大酒店。美国是那个样子吗,我只接触过一对洋人,是父母亲的英国朋友,艾利司顿夫妇。有一次他们要
来喝茶,母亲关照厨房洋人喝茶是要加牛奶和糖的,或加柠檬片。爸爸说,洋人的鼻子好大,我们不要一直看他们。
他说有一次一位中国太太请洋人喝茶,因为心里只顾不要看那人的鼻子,过分紧张,於是在倒茶的时候,问那洋人,
「你要加一块或是两块糖在你的鼻子里?」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艾利司顿夫妇来饮茶的时候我们倒没有出洋相,
他们问我话,我的回答限於Yes 和No。 ,我只觉得他们有一股骚味。洋人是像在电影里看见的人吗?女人穿从背後
拉链的晚礼服,和男人亲嘴或打男人的耳光?还是像传教士长得那麽丑?小孩子是不是个个像秀兰邓波儿那麽可爱?
大概在我们离上海之前一个星期,三伯带著子女从厦门来了。三怕要接办《 宇宙风》 半月刊。他们住在家里,
使我们在百忙之中更加热闹。我初次和伊蕙姊和伊祝已见面。伊视祝和我同年,非常调皮,喜欢皱起鼻子向我做鬼
脸,我也要在他面前出锋头,像跳芭蕾舞一般,用脚趾尖走路。
上船的前一天,我们搬到旅馆去住。搬出依定盘路的家的时候,妈妈过度紧张,不知道电源没有关掉,就用剪
刀剪断楼上的电线。砰然一大声,把大家吓住了。电力触到剪刀,把刀片烧了个洞。幸亏妈妈没有受伤。
我们搬到旅馆之後,亲友川流不息地来看我们,送糖果饼乾,还有人顺便在浴室洗热水澡。下午陪妈妈去珠宝
店,她想买一只玉镯子,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到了六点,我们坐汽车到码头。在那里又有许多送行的人,我们乘
小汽艇驶到停在海上的「胡佛总统」号轮船,看见那艘两个烟囱的大轮船,我兴奋得手足发冷。我们真的要走了!
上了大船,大人又和亲友们寒暄,爸爸在大厅里叫柠檬汁给大家喝。侍者是个身材高大的美国人。我在上海所看见
的外国人都是有地位的,没想到也有当待应生的外国人。
送行的人到了十一点才走完,我们走回房舱,发现房里堆满花篮,舱门几乎打不开!爸爸叫人把花篮拿到饭厅
去,大约有三十个,第二天摆满饭厅的长桌,舱房里还有许多礼物,我数了十八盒糖果。
第二天醒来,轮船已经在海洋上驶着。
10。 突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我喜欢在甲板上散步,走到船尾让强风吹拂我的头发,靠左边走,风把我的头发都吹到前面,靠右边走,风把
头发都吹到後面。
船上有许多外国老太婆坐在甲板上晒太阳,鸡皮鹤发,浓妆艳抹,露胸露背,我看了觉得很滑稽。中国老大大
哪里会这样显丑?
船到夏威夷时停一天,在我们还没有醒来时已经靠岸。七点钟,茶房敲门叫大家起来,因为要排队检查护照。
到了十点钟,有人送来几个花环,是要套在颈上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认识什麽人。上岸的时候,
居然还有二十多人等著欢迎父亲,而且有记者用闪光照像机给我们照像,又有人在我们的脖子上套花环。这些中国
人请我们去吃午饭,饭後带我们乘一艘玻璃底的船,看在海里的珊瑚和热带角,后来又请我们吃夏威夷大餐和看土
人表演草裙舞。那大餐倒没有什麽可吃的。我们不敢吃生鱼,还有一种冷的浓汤是芋头做的,不用汤匙而是要用手
指沾起来吃,我们也没有吃。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来一只冷螃蟹,足有一尺宽。我们都饿肚皮,於是爸爸设法把
螃蟹剥开,怎麽剥都剥下开,最後他把螃蟹竖在衣柜的抽屉中,用脚把抽屉猛然踢进。螃蟹是轧碎了,抽屉旋钮也
轧碎了。我们吃著蟹肉,从房舱窗口望出去,船已经开动了。
「为什麽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又送花又送螃蟹给我们吃呀?」我问。
「那些人是华侨领袖,他们招待我们是因为爸爸是名人。」妈妈说。
船到旧金山时,又有记者上来用闪光照像机为我们拍照,还有书店派一个人来接我们。一上岸,就知道这是美
国了。处处是白人,搬行李的,开汽车的,卖报纸的。美国人不再是个个有地位的。那书店派来的人把我们带到一
家旅馆,乘电梯到十八楼。爸爸说,房间是十八美元一天,那是六十块钱。我的天呀!
在餐厅吃午饭,有许多美国人都在看我们。那时的美国和现在不同,没有多少中国人家会住进一流旅馆,何况,
妈妈和我们都穿长及踝部的旗袍,也许这也是引入注意的原因。不但如此,妈妈还戴著她那副独一无二的无框眼镜,
是用夹子夹在鼻梁上的,只有一边有一条很细的链子钩在耳朵。那副眼镜是她在德国的时候配的,她很喜欢,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