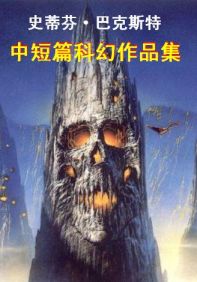高行健作品集-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摹渡胶>返焦爬系牡乩碇尽端ⅰ罚饬樯讲⒉皇钦婷挥谐龃Γ鹱婢驮谡饬樯降阄蚬︒纫蹲鹫摺D悴⒎怯薅壑玻阅愕拿艋郏愕孟日业侥腔谙阊毯凶由系奈谝列≌颍胝飧隽樯奖鼐耐ǖ馈!�
你回到车站,进了候车室,这小山城最繁忙的地方,这时候已经空空荡荡。售票处和小件寄存的窗口都被背后的木板堵个严实,你再敲打也纹丝不动。无处可以问讯,你只好仰头去数售票窗口上方一行行的站名:张村、沙铺、水泥厂、老窑、金马、大年、涨水、龙湾、桃花坞……越来越加美好,可都不是你要找的地方。别看这小小的县城,线路和班次可真不少。有一天多至五、六趟班车的,可去水泥厂绝非旅游的路线。最少的则只有一趟班车,想必是最偏僻的去处。而乌伊居然出现在这路线的终点,毫不显眼,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地名,没有丝毫灵气。可你就像从一团无望解开的乱麻中居然找到了个线头,不说高兴得要死,也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你必须在明早开车前一个小时先买好票。经验告诉你,这种一天只有一趟的山区班车,上车就如同打架一样,你要不准备拼命的话,就得赶早站队。
此刻,你有的是时间,只不过肩上的旅行袋稍嫌累赘。你信步走着,装满木材的卡车连连掀着高音喇叭,从你身边驶过。你进而注意到穿县城而过的狭窄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带挂斗的和不带挂斗的,都一律掀起刺耳的高音喇叭,而客车上的售票员,还把手伸出窗口,使劲拍打车帮子上的铁皮,更为热闹。也只有这样,行人才能让道。
两旁贴街的老房子一律是木板的铺面,楼下做的生意,楼上晒着衣服,从小儿的尿布到女人的乳罩,补了裆的短裤到印花的床单,像万国的旗帜,在车辆的喧闹声和扬起的灰尘中招展。路旁水泥电线杆子上,齐目高的地方,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有一张治疗狐臭的特别引起你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你有狐臭,而是那广告的文字来的花梢,在狐臭之后还打了个括号:
狐臭(又名仙人臭)是一种讨厌的疾病,其味难闻,令人欲吐。为此影响朋友交往耽误婚姻大事的不乏其人。青年男女还屡屡遭到从业参军的限制,无限痛苦,不胜烦恼。现我处采用新式综合疗法,能立即完全彻底干净根除臭味,疗效高达97。5%。为您生活愉快,未来幸福,欢迎前来治疗……
之后,你到了一座石桥上,没有狐臭。清风徐来,凉爽而适意,石桥架在宽阔的河面上,桥上虽然是柏油路面,两边斑驳的石柱子上刻的猴子还依稀可辨,肯定很有一番年代了。你倚着水泥加固了的石槛杆,俯视由石桥连接的这座县城,两岸都是黑色的瓦顶,鳞次栉比,让人总也看不尽望不透。两山之间,一条展开的河谷,金黄的稻田上方镶的绿色的竹林。河水蓝澄澄的,悠悠缓缓,在河床的沙滩间流淌,到了分水的青麻石桥基下,变得墨绿而幽深,一过桥拱,便搅起一片哗哗的水声,湍急的漩涡上飘出白色的泡沫。石条砌的河堤总有上十米高,留着一道道水渍,最新的一层灰黄的印子当是刚过的夏天洪水留下的痕迹。这就是尤水?它的源头则来之灵山?
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橙红的团团如盖,通体光明却不刺眼。你眺望两旁山谷收拢的地方,层峦叠蟑之处,如烟如雾,那虚幻的景象又黑悠悠得真真切切,将那轮通明的像在旋转的太阳,从下端边缘一点一点吞食。落日就越加殷红,越加柔和,并且将金烁烁的倒影投射到一湾河水里,幽蓝的水色同闪烁的日光便连接一起,一气波动跳跃。坐入山谷的那赤红的一轮越发安祥,端庄中又带点妩媚,还有声响。你就听见了一种声音,难以捉摸,却又分明从你心底响起,弥漫开来,竟跳动了一下,像踮起脚尖,颠了一下,便落进黝黑的山影里去了,将霞光洒满了天空。晚风从你耳边响了起来,也还有驶过的汽车,照样不断掀出刺耳的喇叭声。你过了桥,发现桥头有块新镶嵌的石板,用红漆描在笔划的刻道里:永宁桥,始建于宋开元三年,一九六二年重修,一九八三年立。这该是开始旅游业的信号。
桥头摆着两趟小吃摊子。你在左边吃一碗豆腐脑,那种细嫩可口作料齐全走街串巷到处叫卖一度绝迹如今又父业子传的豆腐脑,你在右边又吃了两个从炉膛里现夹出来热呼呼香喷喷的芝麻葱油烧饼,你还又在,在哪一边已经弄不清楚了,吃了一颗颗比珍珠大不了许多甜滋滋的酒酿元宵。你当然不像游西湖的马二先生那样迂腐,却也有不坏的胃口。你品尝祖先的这些吃食,听吃主和小贩们搭讪,他们大都是本地的熟人,你也想用这温款的乡音同他们套点近乎,也想同他们融成一片。你长久生活在都市里,需要有种故乡的感觉,你希望有个故乡,给你点寄托,好回到孩提时代,捡回漫失了的记忆。
你终于在桥这边还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找到一家旅店,楼板都拖洗过了,还算干净。你要了个小单间,里面放了张铺板,铺了一张竹席子。一床灰棉线毯子,不知是洗不干净还就是它本色,你压在竹席子底下,扔开了油腻的枕头,好在天热,你不必铺盖。你此刻需要的是搁下变得沉重的旅行袋,洗一洗满身的尘土和汗味,赤膊在铺上仰面躺下,叉开两脚。你隔壁在吆三喝四,有人玩牌,摸牌和甩牌都听得一清二楚。只一板之隔,从捅破了的糊墙纸缝里,可以看见虚虚晃晃几个赤膊的汉子。你也并不疲倦得就能入睡,敲了敲板壁,隔壁却哄了起来。他们哄的并不是你,是他们自己,有赢家和输家,总是输的在赖帐。他们在旅馆里公然聚赌,房里板壁上就贴着县公安局的通告,明令禁止一是赌博,二是卖淫。你倒想看看法令在这里究竟起不起效应。你穿上衣服,到走廊上,敲了敲半掩的房门。敲与不敲都一个样,里面照样哈喝,并没有人答理。你干脆推门进去,围坐在当中的一块铺板上的四条汉子都转身望你,吃惊的并不是他们,恰恰是你自己。四个人四张怪相,脸上都贴的纸条,有横贴在眉头上的,也有贴在嘴唇鼻子和面颊上的,看上去又可恶又可笑。可他们没有笑,只望着你,是你打扰了他们,显然有些恼怒。
“噢,你们在玩牌呢,”你只好表示歉意。
他们便继续甩着牌。这是一种长长的纸牌,印着像麻将一样的红黑点子,还有天门和地牢。输的由赢家来罚,撕一角报纸贴在对方指定的部位。这纯粹是一种恶作剧,一种发泄,抑或是输赢结帐时的记号,赌家约定,外人无从知晓。
你退了出来,回到房里,重新躺下,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泡四周密密麻麻的斑点,竟是无以计数的蚊子,就等电灯一灭好来吸血,你赶紧放下蚊帐,网罗在窄小的圆锤形的空间里,顶上有一个竹蔑做的蚊帐圈。你好久没有睡在这样的帐顶下了,你也早过了望着帐项可以睁眼暇想或是做梦的年纪,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冲动,该见识的你都�一领教了,你还要找寻什么?人到中年,该安安稳稳过日子,混上一个不忙的差事,有个不高不低的职位,做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安一个舒适的小窝,银行里存上一笔款子,月月积累,除去养老,再留点遗产?
2
我是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邛崃山的中段羌族地区,见到了对火的崇拜,人类原始的文明的遗存。无论哪一个民族远古的祖先都崇拜过给他们带来最初文明的火,它是神圣的。他坐在火塘前喝酒,进嘴之前,先要用手指沾了沾碗里的酒,对着炭火弹动手指,那炭火便噗哧噗哧作响,冒起蓝色的火苗。我也才觉得我是真实的。
“敬灶神爷呢,多亏的他,我们才有得吃喝,”他说。
跳动的火光映照着他削瘦的面颊,高高的鼻梁和颧骨。他说他是羌族人,底下耿达乡的人。我不便就问有关鬼神的事,只是说我来了解这山里的民歌。这山里还有没有跳歌庄的?他说他就会跳,早先是围着火塘,男男女女,一跳通宵达旦,后来取缔了。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这又是我不真实之处。
“不是文化革命吗?说是歌词不健康,后来就改唱语录歌。”
“后来呢?”我故意还问,这已经成为一种积习。
“后来就没人唱了。现今又开始跳起来,不过,现今的年轻人会的不多,我还教过他们。”
我请他做个示范,他毫不迟疑,立刻站起来,前一脚后一脚踏着步子唱了起来。他声音低沉而浑厚,有一付天生的好嗓子。我确信他是羌族人,可这里管户口的民警就怀疑,认为申报为藏族或羌族的都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好多生孩子。
他唱了一段又一段。他说他是个好玩的人,这我也信。他解脱了乡长的职务,重又像一个山里人,一个山里好热闹的老头子,可惜过了风流的年纪。
他还能念好多咒语,是猎人进山时使的法术,叫黑山法,或是叫邪术。他并不回避,他确信这种咒语能把野兽赶进设下的陷阱,或是让它踏上安的套子。这使邪术的又不光是人对野兽,人与人之间也用来报复。如果被人使用了黑山法,就注定在山里走不出来。这就像我小时候听说过的鬼打墙,人在山里走夜路,走着走着,眼面前会出现一道墙,一座峭壁,或是一条深深的河,怎么也走不过去。破不了这法,脚就是迈不出这一步,就不断走回头路。于是,到天亮才发现不过在原地转圈。这还算好的,更糟的还能把人引向绝境,那就是死亡。
他念着一串又一串咒语,不像他唱歌时那样悠缓从容,都喃喃呐呐,十分急促。我无法完全听懂,却感受到了这语言的魅力,这种魔怪森然的气息就弥漫在被烟子熏得乌黑的屋子里。火舌粘着炖羊肉的铁锅,将他那双眼睛映得一闪一闪,这都真真切切。
你找寻去灵山的路的同时,我正沿长江漫游,就找寻这种真实。我刚经历了一场事变,还被医生误诊为肺癌,死神同我开了个玩笑,我终于从他打的这堵墙里走出来了,暗自庆幸。生命之于我重又变得这样新鲜。我早该离开那个被污染了的环境,回到自然中来,找寻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在我那个环境里,人总教导我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又必须忠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真实。而我的错误恰恰在于我脱离了生活,因而便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而生活的真实则不等于生活的表象,这生活的真实或者说生活的本质本应该是这样而非那样。而我所以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就囚为我只罗列了生活中一系列的现象,当然不可能正确反映生活,结果只能走上歪曲现实的歧途。
我不知道我此刻是否走上了正道,好歹总算躲开了那热闹的文坛,也从我那间总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逃出来了,那屋子里堆满的书籍也压得我难以喘气。它们都在讲述各种各样的真实,从历史的真实到做人的真实,我实在不知道这许多真实有什么用处。可我竟然被这些真实纠缠住,在它们的罗网里挣扎,活像只落进蛛网里的虫子。幸亏是那误诊了我的大夫救了我的命。他倒是挺坦诚,让我自己对比着看我先后拍的那两张全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