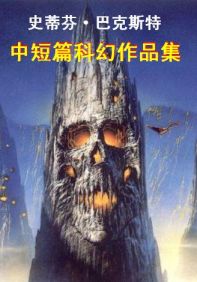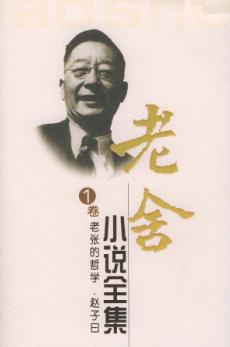高行健作品集-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财富。这些意思他以前和我谈话时也讲过。可现在我突然觉得这种话在一些人眼里也许就是异端吧?我就说:“你把笔记本借给我看看。”他说:“你都拿去吧。”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他进大学以后的十多个笔记本都翻阅了一遍。里边有大量的数学公式、各个学科的新成就和新观点的摘要。这些摘要许多我看不懂,不少摘自于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的科技书籍和资料。他这时已经能用四种文字对照着字典看专业书籍了。摘录之外,还不时记下他自己的一些见解。当然,大量的是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设想,间或也有一些抽象的议论。可基本上都是关于科学的方法论的一些感想,偶尔发几句牢骚罢了,大概针对班上和学校里的事情发的感触。比方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可人吃的是粮食和肉类,屙出的却是粪便。什么也不生产的人,只消耗能量,把高能转变为低能,最多只不过肥田。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学科,研究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对社会能量的无效的消耗,将会比宇航学对人类的贡献更大。”
“什么意思?”我问他。
他笑说:“发发牢骚,没什么意思。”随手就在那句话上打了两道叉。
我又问他:“你做这些笔记有什么用?”
“这已成为一种习惯了。过一个阶段,我就把笔记本再翻阅一遍,检查前一段的学习,看自己得到了哪些新的思想和启发。也许将来写什么东西或思考问题时,可以开阔思路,这就是我储存记忆的电脑。”
这种笔记本来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习以为常的事。可有人准是看过他的笔记,汇报上去了,而且歪曲、夸大不知到什么地步。他毕业以后也一直受到歧视,我想都同他的这些笔记有关。也许汇报上去的那些摘录,现在还存在他的档案里。而他那些真知灼见,一些对未来的发明的设想,却不会有一个字的记载。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人。
“你以后别把这些笔记随手乱扔,用完就收进书包里。”我说。
“这笔记里有什么?”他问。
他真是个傻孩子。老实说,看了他的这些笔记,我更理解他了。他总渴求着新知识、新观点。他的脑袋像一部奇妙的机器,把知识吸收进去,就产生许多新鲜的见解。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继续把他的事业做下去,他会出很大的成就,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叙述者的话
当你经历了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十年的动乱,当你眼见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和那些迟钝的目光;当你遇到那种狂热的武斗和随之而来的无谓的牺牲;当你亲自体会到你最亲爱的人的亡故带来的那种空虚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深深的绝望;当你感到自己被欺骗了,白白耗费着自己的生命,那小儿女的眼泪的辛酸就算不得什么了。当你终于见到了那铅灰色的天空下奔腾咆哮的大海,那漫天的波涛,你就会知道你一个人的悲哀是怎样微不足道。海潮从天边滚滚而来,一道道向前推移着,又都撞碎在褐色的岩石上,在你脚下溅起无数的水沫,肖玲因为没考上大学那一点辛酸的眼泪自然就算不得什么了。考试,就连她那柔弱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公鸡的话
我陪着她在长着荒草的城墙根下走着,她低着头。过完暑假,就要回学校去了。我安慰她说:
“考试并不总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水平,在一次考试中失误了,那有什么,明年再考。”
我又告诉她怎样复习功课,反复讲了许多安慰她的话。她依然默默不语,总低着头。我不忍心见她这样,拉了一下她的胳膊,在路灯下站住了。
“你应当有信心。”我说,“我相信你明年准能考上。”她抬起头,昏暗的路灯照着她苍白的面孔,我看着她,心痛极了。你说有什么办法能够安慰她?我只蹦出了一句:
“就是你考不上,不管你将来做什么,在哪里,我都和你在一起!”
她望着我,眼睛湿润了。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便拉住她的手,走到灯柱后面,她靠在灯柱上,闭上了眼睛。我吻了她。我们谈恋爱这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吻她,咸酸的泪水流到我的嘴边。我说:“你怎么了?”她摇摇头,仍然闭着眼睛,随后靠在了我的怀里……
我们如醉如痴,在城墙下走来走去,一直将近半夜。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在她家门口,葡萄架下,黑暗中,她又让我吻了她。如今葡萄藤已经早铲除了,架子也拆掉了,这屋里进出的也都是陌生人了。可我永远记得她柔软、无力的嘴唇和头发中的清香在我心中留下的那种颤动和温暖的记忆……
肖玲的信
亲爱的:
你给了我生命的勇气,我会振作起来,我会乖乖地听你的话,把
功课复习好。你放心,我会注意身体,我每天还要锻炼。我现在给自
己安排了一个日程表——早晨六点起床,然后在阳台上做早操,读四
十分钟的俄文,再替奶奶上街买菜。早饭以后,读一小时的古文,主
要是背诵课文,九点以后复习历史或地理,下午就看你指定给我看的
那些参考书和小说。一星期写一篇作文。累的时候唱唱歌,画画画。
晚上的时间属于自由支配,或是陪爸爸、妈妈和奶奶聊一会天,偶尔
也去看电影,但绝不在下午。
我现在又觉得充实了,总是忙碌得很。我给你绣了一块手帕,绣
得不好,可花却是我自己设计的。你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吧?当然,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绣花的。
吻你!
你的玲
(全文完)
通往灵山的路--和高行健相遇
作者:赵川
上
坐在午后懒散的阳光下,读流亡作家高行健的《灵山》,像是很多年前的某个下午,在上海一条弄堂的晒台上,看著眼前重
重叠叠的红瓦屋顶,由老人家细哼童谣,在背上轻柔抚拍,慢慢进入满是阳光馨香的梦乡。就这样读著书,从已理顺的现实秩序
和规范下,退回到朦胧、参差和无序的纯真里。
历史,在高行健的笔下化解开来,从有头有脸的教条下瓦解,流淌成一个个平行的生命章节,或传奇或平凡,还原到它们本
来不甚清楚的层叠面貌。风土史实,传闻传奇和由各种人生经验组成的片段,在通往灵山的路上,交错穿插,偶然与必然相间,
有无法抹去的已成的现实,也有若即若离的臆想世界,它们咿咿呀呀,纷至沓来。
那灵山在哪里,小说的主人公不是要去寻找灵山吗?
他孑然一身,游盈了许久,终于迎面遇到一位拄著拐杖穿著长道袍的长者,于是上前请教:
“老人家,请问灵山在哪里?"
“你从哪里来?"老者反问。
他说他从乌依镇来。
“乌依镇?"老者琢磨了一会,“河那边。"
他说他正是从河那边来的,是不是走错了路?老者耸眉道:
“路并不错,错的是行路的人。"
……
(高行健《灵山》第六十七节)
小说里的灵山更像是一个通往虚无目标的过程,或者这正是弥漫在《灵山》里的禅意,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灵山》里,带自传色彩的“我”,和由“我”演化出的如“我”影子般的“你”,在中西南边区漫游,刻意要去寻找一
片原生态的净土,原生态这个词在小说的多个章节中出现,灵山就像是这片净土的化身。由于“我” 或“你”无不带著想接近
和进入的念头,小说似乎意指那就是完美的境界,世界原本就应该那样。
但“我”或“你”,还加一个来历不明的“她”,始终都只能周折在通往净土的道路上。在这条路上,人的精神世界,个人
身世,所经过地界的身世--地方史志或神话传奇,自然或风物,盘缠地铺展开来。那些故事交错纵横,一个个章节,一段段叙
述,它们不在意怎样承接隶属,也不在意源自哪里,又流汇何处,当然总也可以作更进一步的寻本探源。故事本身也像这种漫
游,之间不层层递进,也不引导出任何冲突或企图走向深层。它们存在的目的也像是无目的,它们近乎盲目地编织一起,连惯或
不连惯,都不经意地成为周遭真实中的组成部分。借用文学评论家赵毅衡在评述高行健戏剧创作时的话来说,“如果他(高行
健)也在追求意义,那么这些意义似乎也是同水平的,无深度的,或者说,不经意间信手偶得的。”(赵毅衡《建立一种现代禅剧》)
那天在午后和 的阳光下,这些纷乱的篇章,当它们在眼皮下流过的那一刻,凡人的历史,也包括逝去了或依旧还在的他们
的精神,就在这股股细流交错的章节间,不仅驻足或通过,而且被神奇地耸立起来。
我相信这就是灵山,大概也就是我们的原生状态。
“一个清晰的思想固然美妙,但它始终意味著浓缩含意,斩段了零散的头绪。而在现象世界里,零散的头绪极为重要,因为
它们交织在一起。”(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历史总被一些人理顺了琐碎的头绪,弄成一具可随意塞入意图的光滑壳
子,但在《灵山》里,我看到了高行健想将历史回复到其原生态的努力。
下
十几年前,当我还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已很为社会上求变的气息所动。高行健在80年代初写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较
晚一些时候出版的《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以及他的『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等戏剧作品,都是我所熟悉的,那
是那个时代里求变气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悉尼大学陈顺妍博士 Mabell Lee 翻译的《灵山》英文版 〃SOUL MOUNTAIN〃 ,今年六月已由澳洲的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在
澳洲和新西兰出版发行。一九九七年,我还没有读过《灵山》中文原著,只从澳洲文学季刊《 HEAT 》第四期上,看到了陈顺妍
博士的部分英文节译,和她的介绍性论文“高行健的《灵山》”( GAO XINGJIAN'S LINGSHAN / SOUL MOUNTAIN )。80年代末
我离开中国,当在悉尼读到的《灵山》的英文节译时,已时隔多年,而且还隔了语种。他的东西读来竟是有些神奇。神奇的不仅
是他在小说中的叙述手法,和由这种手法带出的似真犹幻的故事,也是隔了这么些年,和他的作品在这个无法预想的环境里再次
相遇的心境。岁月变迁,人事沧桑,为自己也为别人,总不免有些感慨。
又隔了两年,我去巴黎时去看了高行健。
高行健住在巴黎一个很高的地方。他在电话里说是一栋白色的高楼,塔楼,最高的,像塔一样,你看到了就知道了。
那天我下了火车就开始下雨,他说要穿过的那片公园根本就是个山坡。我湿漉漉喘嘘嘘走上坡顶,脸上眼镜上都是水,果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