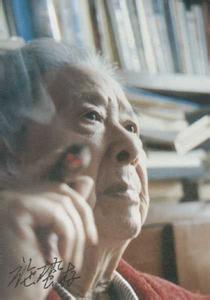施蛰存作品选-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语都很好,据说他讲日语,纯粹是东京话。望舒和这两位同学,天天在一起,跟樊国栋神父(PèreTostan)读法文,课余休息时,大家谈文学。梁洌Я⑻赣⒚牢难В醪硬ㄌ溉毡疚难А�
当时在震旦本科读书的有李辛阳、杨琦、孙春霆(晓村)、樊华堂、陈志皋,也都成为望舒的好友。
樊国栋神父负责的法文特别班是很有名气的。在他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下,一个不懂法文的中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升入大学本科一年级,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学生,一起听法国教师(都是神父)的课。樊国栋神父每天上午来讲两堂课。第一堂课是复习上一天的所授的课。每个学生都要背诵他上一天布置的课文。一般都是一页至二页《法文菁华》里的文学作品,如雨果的一首诗,或拉马丁的一段散文。背不出的学生,被他挥出教室,到草地上去自己温习,直到自以为背得出了才回来。回进教室后再背,背不完篇,还得出去。有些学生,直到下课时间还无法背出,那么到明天再背,可是明天要背一篇旧的,一篇新的。樊国栋神父的第二堂课是授新课文。他的方法是把新课文读一遍,学生一起跟着读一遍。如是者三次。然后分别叫每个学生站起来独自读一遍,他校正了读音方面的错误。如是者叫五六个学生读过,大约已过了大半小时。于是他讲解课文的意义。用法语讲,有时用英语,有时在黑板上写几个汉字。英法文距离本来不远,有英文基础的学生,只要他在关节处略一讲解,就容易懂得,讲解完毕,他就交代明天要背诵的段落。每天下午一堂课,是中国教师来讲授的,完全是辅导课,如果学生对上午的课有什么不懂,就请中国教师再讲讲清楚。上午的上课时间是九时至十一时,下午是一时至三时,由教师自己掌握,可以连续讲二小时,也可以分二节。
每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樊国栋神父带来一份法文资料:一段历史,或一篇哲学论文,或其他散文,写满三大页,约七八百至一千字。他把这份复印的资料发给每一个学生,然后自己读三遍,学生跟着读。读后就交代,这是星期六上午要默写的作业。因此,每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晚上,每一个学生都要抽时间来熟读这篇长文,到能背诵为止。
星期六上午九时去上课,樊国栋神父给每人发了考试纸,大家坐下来默写。写完交卷,即可离开教室,一星期的学业完了。星期五上午的课不布置背诵作业。所以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直到晚上,是全部休息时间。不过学生中的天主教徒,星期天上午还得上教堂做弥撒。
特别班的学生不多,每年入学不过二三十人。上课一二个月后,因功课跟不上,自动退学的,总有好几个。这批学生,不住在震旦本科学生宿舍内,而住在震旦大学对面一片操场角上的一排古老楼房内。这是七开间二楼的中式楼房,特别班学生都住在楼上,四人一间,很宽敞。楼梯口一个房间是樊国栋神父住的。他不但负责特别班学生的教学,还负责生活指导。他住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学生上楼下楼,他都看见。他经常在走廊里漫步,隔着玻璃窗注意寝室内每一个学生的行动。在规定自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寝室内的学生在谈笑,他就会敲着窗子喊:“读书呀!读书呀!”如果在规定休息的时候,例如下午四点钟以后,晚饭以前,如果看见还有学生在寝室内做功课,他会开门进来赶他们下楼,到操场上去散步。
戴望舒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教学方法下很快地学好了法文。一九二五年复,特别班结业之后,望舒准备去法国留学。震旦大学给了他一个文凭,凭此可以进巴黎大学听课。
但是赴法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望舒的父亲是杭州中国银行的交际员,月薪不高,没有能力供给望舒赴法留学。中国银行董事某某同意用贷款的方式给予帮助,要经过申请、审议许多手续,迟迟没有核准。
这时,我在大同大学读三年级,杜衡读五年制的南洋中学刚毕业。三个人一合议,决定过一年一起去法国。杜衡家道丰裕,我的家庭是小康经济。三人一起去法,我和望舒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可以依靠杜衡,不至于困窘。况且当时法郎比值便宜,如果每月有一百元,甚至八十元国币,在法国可以维持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和杜衡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望舒为了等候我们,升入震旦大学法科一年级。我和杜衡也在樊国栋神父的严格训练之下苦学法文。樊国栋神父能读中国古文,他正在把中国古代散文或唐诗译成法文。他知道我和杜衡的古文知识比别的学生高。他给我们布置的每周作业常常是要我们把一篇古文译为法文。记得我译过的有《阿房宫赋》和李白的几首《古风》。樊神父的中文虽然不坏,但到底是个外国人,不容易了解汉字的许多用法。他把李白诗“徒此挹清芬”的“徒”字译作“你的学生”。
他拿出译文给我们看,我们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告诉他这个“徒”字是“徒然”的意思。
由此,他每星期分配我们译一篇古文古诗,利用我们的译文,为他自己的译文加工润色。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这件事是望舒开始联系的,我不很知道经过情况。解放以后,屡次审查我的政历,要我交代谁是我们入团的介绍人。可是望舒已去世,我无法说明。但仿佛是一位上海大学的同学陈均。当时上海还在军阀统治之下,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无论国民党左派或右派,都是“匪徒”,都在“应予逮捕”之列。不过震旦大学在法租界内,军阀的凶手,非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同意,还无法直接进入租界抓人。但租界当局,也并不允许居民有政治活动的自由,只要没有扰乱治安的群众运动发生,对其他地下活动,就不很注意。在这方面,法租界较英租界宽容得多,因此,二十年代许多革命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潜迹在法租界。
我们三人加入共青团和国民党后,不久就每人领到一张国民党员的党证。当时在上海有两个国民党党部,一个是国民党右派,党部设在环龙路(南昌路)。另一个是国民党左派的,党部设在陶尔斐斯路,隶属于这个党部的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即所谓“跨党分子”。两个党部相去甚近,但都是保密的。
中国共产党另外有领导机构,在卢家湾一带,我们曾到西门路,白莱尼蒙马浪路(马当路)一幢里弄民房中去开过会,每次都到了一二十人,各不相识。这两处地方,大约是团部所在。
关于团员工作的一切通知,都是由一名交通员送来的。这个交通员是一个伶俐的青年,他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口,悄悄地塞给我们一份通知,一份简报,或一叠要我们散发的传单。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八九点钟,三人一起出去散步。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
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震旦大学学生,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但反共,也反国民党。天主教学生中比较进步的,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党员的吸收下,加入了国民党右派。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冬季,震旦大学生中有了三个政治派别。我们这一边,人数似乎最少。由于各小组互不打通,我也不知道当时震旦大学有多少共产党团员。但是尽管如此,好像我们已被注意了。
我们的寝室一共住四个人,我和望舒、杜衡外,还有一个苏北人,姓孙,也是特别班学生。此人非常庸俗,我们平时很少和他谈话。仅仅保持表面的同学礼貌。有一天,我们发现每个人的抽斗都被翻乱了,枕头、被褥,也有凌乱的迹象。肯定是被检查过了。当时,那姓孙的不在室内。不久,他回来了。一坐下,就开他自己的书桌抽斗,一只,两只,乱摸了一阵,就叫起来:“谁来翻过我的东西啦?”于是他问我们。我们说:我们的东西也有人翻过了。这样,彼此都是受害人,证明我们的东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我们还是提高警惕,对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台路一个里弄内,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空着,没有人祝门口贴着“招租”条子。我们到经租帐房去一问,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没有别的条件,水电已经装好,只要先付一个月房租,当天即可迁入。原来当时法租界空余房屋很多,震旦大学附近都是冷静地段,虽在白天,马路上也极少行人。电车从霞飞路(淮海中路)转入吕班路,往往已没有乘客了。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幢房屋,其时学期已将结束,我们以回家度寒假为理由,从宿舍里迁入这幢房屋的楼上厢房。厢房挺大,我们每人买了一床、一书桌、二椅子,还合资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房间里还是空空洞洞的。现在,整幢房屋还有三大间空着,外加灶披间。整个楼下是客堂、厢房,各一大间。楼上是正楼一大间。我们在大门上及里弄口,贴了一个“余屋分租”的条子,打算做二房东,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请房客负担了去。招租条子贴出了几个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女女来看房子。他们一看,我们这个二房东,只是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女眷,没有老校都就不声不响的走了。空房始终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马路口碰到松江同乡钱江春。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他的夫人吴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个里弄内。吴佩璋是美专学生,因此他俩住得靠近美专而远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江春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说,有人在组织松江同乡会,正要找一间会址。过几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来联系,租下了我们的楼下厢房一大间。当晚,这个人就把床板铺盖搬进来,住在那里。此后一二天,看见他搬了两张长桌和几只条凳进来,显然是开会用的。又过了几天,后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松江同乡会通信处”。我心中纳罕,我是松江人,为什么不来请我加入同乡会?而且钱江春也不来。楼下厢房里经常有人出入,有时有十多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打搅,不知他们是何许人。一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在后门口碰到一个人刚闪出来。一看,是侯绍裘。彼此都是熟识的,不能不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绍裘说:他知道我在楼上,不过因为事忙,还没有时间上楼去看我。松江同乡会还在筹备,将来开大会时一定来邀我。当时,我知道他和党有关系,却不知道他的活动情况。他不知道我是共青团员。因此,匆匆一晤,彼此未通声气。岂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烈士侯绍裘。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知道当时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实在是柳亚子和侯绍裘主持的江苏省党部。
这时已及阴历年底,表面上,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