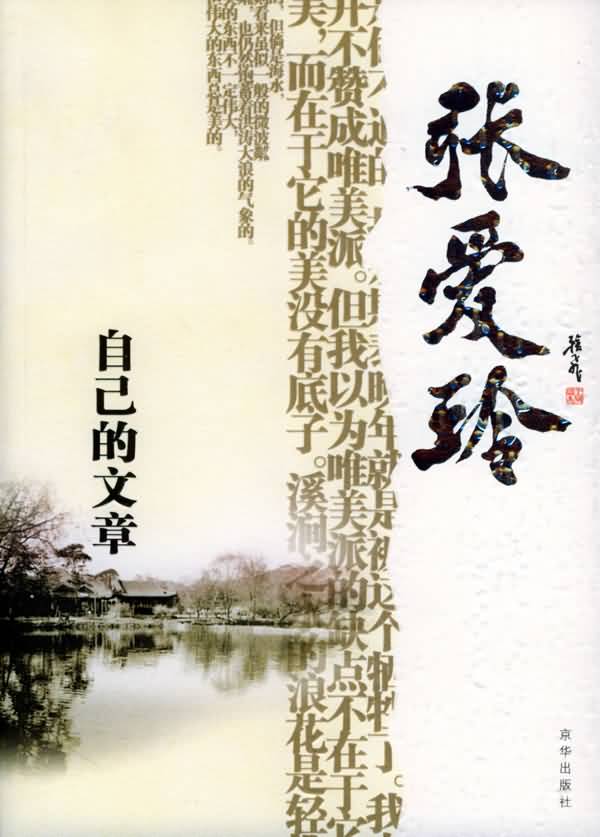张洁文集-第9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
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
嘁!”
我想她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
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她
去世后我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
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大
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而反尔。这句话,她
又是只说了半句。因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
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
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她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手术完美无
憾”的现实吗?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有人相信吗?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
天特别不舒服。”
我看着她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痛,略显迟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
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
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
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会一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
有什么不舒服了。”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
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
是手术后一种虽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
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早从那时起就开始应验了这个预料。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
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
这一反复出现的情况,她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
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
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
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
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
话。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
她也就缄口不言了。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
的女儿也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
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
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虽然妈去世
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报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
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
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她是否不忍再用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
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后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
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闹”;
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判断的这一瞬间,唯恐怕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
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
那我也不能原谅我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
儿不舒服?
为什么我总是相信不相干的人比相信自己的妈多?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
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的珍贵,我特
地留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
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
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验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
和科学作对,无是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
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
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
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你哪儿不舒服”吗?
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
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
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
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
这真是“死无对证”了。
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不还是我自己的错!
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小阿姨在一旁说“她说是这样,等一会儿再
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
清二楚?
我为什么就固执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
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
的病;
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
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
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后这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
不如不做手术。”
这样,什么样呢?
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
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
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
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可是人都不在了,
再说什么也白搭。
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
就是为了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他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蚂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
的固执和心理障碍?
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她说我错了,她也听不
见了。
她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
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我常常眦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
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
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逝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
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她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她
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她。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
余生不断地反省,而母亲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
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无法替她感同身受。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她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
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
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
情。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
不住地去想。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这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
是天意。
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
她说。
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
了,还有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
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来开导开
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容对妈说,她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
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
后,只好对胡容一诉哀肠。
胡容试着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她,她就从椅子上
站起来了。她不过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
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地一声跌坐下
去,便说:“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
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很危
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
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力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
来,她就是不扶。”
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多多锻炼
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
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
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
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她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她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