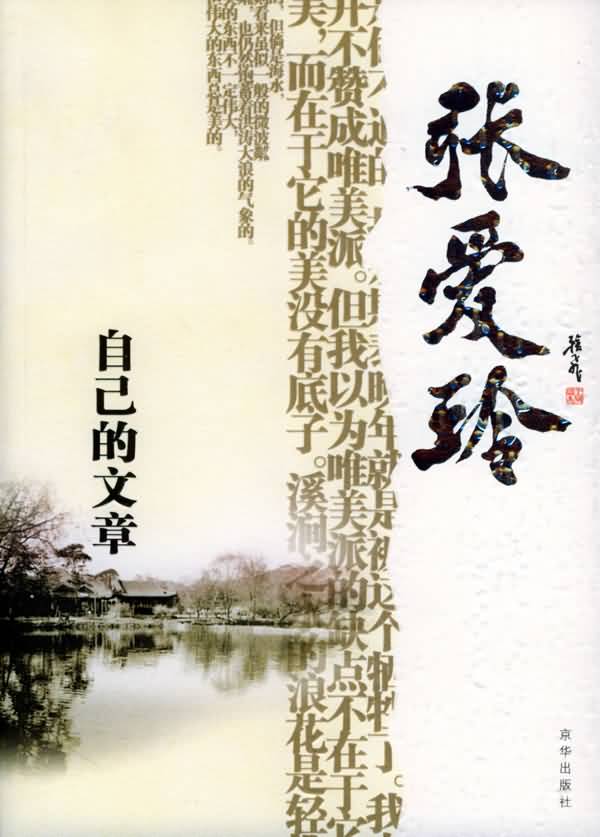张洁文集-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点加以分析,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丰富我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
社会主义特色、民族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
“谈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应用到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来,有些同
志总担心会出毛病,认为这些是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洋玩意儿’,我
们中国共产党人使不得。其实,这是一种偏见。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是无
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列宁把心理学作为构成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基础科
学之一……”
郑子云在讲些什么呀那些个名词、概念全是吴国栋没有听到过的。
吴国栋对凡是自己弄不懂的东西,都有一种反感。这些让他反感的话,出自郑
子云的口中,更让他感到一种压力。虽然郑子云说他不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讲话,
谁要真这么认为,谁就是个傻瓜。这话,不过说说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部长,
谁能拿他的话不当话呢这么一来,吴国栋没准就得重新调整那些多少年也没出过
娄子,磨得溜光水滑,几乎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转下去的观念和做法。郑子云说的那
套,谁知道它灵不灵啊!而且郑子去在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热情,在吴国栋看来,
是超越身份和地位的,是有损部长的威严和分量的。一个部长,有这样讲话的吗
两眼闪闪发光,还瞪得那么大,两颊泛红,声音激昂,一句连一句,前面一句话简
直就像让后面一句话顶出来的。整个给吴国栋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
这就使吴国栋对郑子云的讲话内容,越发地怀疑,越发地觉得不可信。他不由得环
顾四周,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念去寻找,寻找什么平时在厂子里传达文件和政治
学习时司空见惯的扎着脑袋打瞌睡、闷着头织毛活、嘁嘁喳喳开小会、两眼朝天想
心事、鬼鬼祟祟在别人后背上划小王八、大明大摆看报纸的情景全都没有了。好像
郑子云把人人心里那个型号规格不同的发动机,全都发动起来了。别管是赞同的、
反对的,全都支着耳朵在听。难道郑子云讲的话里,真有点镇人的东西不成每每
说到人的问题,郑子云总免不了有一些激动。
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经历过很多运动。他时常惋惜地想起,在历次政治
运动中,那些无辜的、被伤害了的同志。他们其中,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比如在延
安时,曾和他住过一个窑洞,就是灰土布军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潇洒、整洁的那位
同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文化大革命”
初期,因为不堪忍受那许多人格上的侮辱:什么假党员、什么叛徒……自杀了。听
说他在遗书上写过这样的话:“……我不能忍受对我的信仰的侮辱,然而现在,除
此我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我的信仰的尊严……”
第二十五章
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同志,虽然有些孤傲。
然而孤傲一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人都有自己的脾性,只要无妨大局。难道一
定要当个没皮没脸的下三烂,才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这是谁说的他忘了。他的记忆力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以前,凡是他看过的书,他
认为重要的段落,几乎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
是啊,我们有很多的人,有不论水淹或是火烧都不可以毁灭的信仰,然而人在
富足的时候,却容易挥霍。
难道他是个守财奴!要知道,人,这是创造财富的财富,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在
实际工作中认识这一点。侮辱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侮辱;不尊重别人,也常被别人
所不尊重。难道马克思曾将这行径,列入过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吗
唉,经不错,全让歪嘴的和尚给念坏了。
他自己就像处在这样一个两极之中的钟摆。郑子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他早已
变得粗俗,还有些官僚。否认吗不行,存在决定意识。哼哼哈哈,觉得自己即使
不是全部人的,至少也是一部分人的上帝;对那些不是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
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同志,情感上总有一段距离;听到某人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立
刻有一种不自觉的戒备……逢到下级没按自己意愿办事的时候,他照样吹胡子、瞪
眼睛、拍桌子、打板凳……反过来,他也照样挨上一级的训,俯首帖耳,不敢说半
个不字,别看他是个副部长。
他心里明白,他可以在一天之内什么都不是,如同别人,如同那些什么都不是
的人一样。
当然,现在他还是个副部长,他得抓紧时机,把他想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好。
郑子云想起田守诚,想起部里的一些人,和那些离心离德、钩心斗角的事情。
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这一个角落而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希望是黄金。不是还有杨小
东那些人吗新陈代谢,总是这样的。
好像到了深秋,树叶的绿色会变暗、发黄,最后还会脱落。但是到了来年春天,
又会长出鲜绿、鲜绿的嫩叶,在同一棵树上,却不是在同一个树节上、枝桠上。
汪方亮微微地笑着。郑子云的话,在他看来是书呆子的呓语,咬文嚼字、天方
夜谭、理想主义。他最好去科学院当个什么院士,当部长是不合适的。
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但像郑子云这样的一个“洋务派”
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办洋务一向以失败而告终。汪方亮觉得郑子云对中国的
国民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从郑子云讲到的内容来看,大概是下了不少功夫。为什
么不拿出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呢要干大事情,不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不行
的。中国人从汉代开始,于的就是“重农抑商、舍本求末”的买卖。哼!螺旋式的
上升。否定的否定。渗透在整个民族遗传基因里的小农意识。
在部里,人人都说汪方亮是“拥郑派”。按照他的能力,他的才情,他能甘居
谁人之下呢汪方亮不过是拥护改革而已,只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和郑子云,走到
一块来了。
郑圆圆从来没见过父亲工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在社会生
活中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照她的想象,无非是开会——那些常常是只有决议,没
有结果的会议;作报告——根据××号文件和××号文件的精神;划圈——可以不
置可否;传达文件;诸如此类,而已而已。她只能从家里了解爸爸,而在家里,她
觉得郑子云像好些个上了年纪、又有点社会地位的小老头一样,肝火挺旺,急急躁
躁,谁的账都不买。前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全家人都上了床,他却忽然从自己的
房间里跑出来,咚咚咚地跑下楼去,说是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喊,是不是遇见了小流
氓手里什么家什也没拿,就那么跑了出去。就凭他睡裤底下露出来的小细腿脖子,
是小流氓他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好像那些小流氓全是纸糊的,只要他伸出一个手指
头就能把他们捅个大窟窿。不一会儿,自己颠儿颠儿地回来了,其实什么事也没有,
想必是他自己昕岔了。
夏竹筠不过随意地开了句玩笑:“没准是哪个女人在楼下叫你去赴约会吧,那
么积极!”
郑子云大发雷霆:“我怎么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变成了个大老娘们儿
了”然后“砰”的一声摔上了自己的房门,震得墙上的石灰、水泥簌簌地往下掉
渣子。
夏竹筠在他门外又是吵骂又是擂他的门,闹得全家一夜没得安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的阿姨让“造反派”给轰走了,妈妈在机关里“全
托”,郑子云在机关里“日托”。有次过什么节,方方买回来一只活鸡。圆圆是不
敢杀的,方方既然是当时家里最年长的妇女,只有硬着头皮去干那理应是主妇该干
的事。她拿着那把锈迹斑斑,早已没了锋刃的菜刀,往鸡脖子上匆匆地瞄了一眼,
闭着眼睛抹了一刀,便赶紧把手里的鸡往院子里一丢。那鸡非但没死,还歪着个脑
袋在院子里乱飞乱扑,吓得方方和圆圆躲进屋里,关好房门,担心那鸡会不会从意
想不到的地方钻进屋来。郑子云拿了一片刮胡子的刀片,很在行的样子说:“用不
着那菜刀,这个刀片就行。”他倒是挺从容,一把抓住了那只发了狂的母鸡,把鸡
翅膀往后一拧,鸡脖子往手心里一窝,拿起刀片就往鸡脖子上抹,抹了几下也没见
血。他脸上那种大包大揽的神气,渐渐地被恼怒所代替,立刻从厨房的门后找来一
把斧子,“吭”的一声,把整个鸡头剁了下来。他为这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生出来
的认真的恼怒,真是好笑极了。可是郑圆圆不敢笑,他那种死不服输的劲头,简直
到了连开玩笑都不懂的地步。
也是在那段没有女人当家的日子里,郑子云常常指着厨房里的那些作料瓶子对
圆圆说:“瞧见吗这个瓶子里装的是肥皂粉,可别当成盐放进菜里去!”他心血
来潮,难得地炒了一次菜,油都冒烟了,葱花还没切;炝了锅,又发现菠菜还没洗,
最精彩的是他偏偏把那瓶肥皂粉当成了盐。当肥皂粉在锅里泛起泡沫的时候,他就
像在参观一台刚出厂的数控机床,背着手问道:“嗯,它起沫了,它为什么起沫
是不是加盐之后都要起沫”
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把那个装肥皂粉的瓶子挪到别的地方去。
而他自己不动,别人是不敢动的。
郑圆圆一阵遗憾:她作为他的女儿,她对他的了解是多么的肤浅啊,这里才是
真正的他,热情、追求、执著。郑圆圆转过头去看叶知秋,镜片后面,叶知秋那双
小而浮肿的眼睛,竟也闪动着一些光彩。
叶知秋感到了郑圆圆的注视,回过头来,对郑圆圆说:“你有个多么好的父亲,
你应该很好地爱护他。”
她的语气里,有着深深的遗憾,好像她深知郑子云不论在家里或是在工作岗位
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照应、理解和支持。
这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人,怎么会比郑圆圆自己,比她的母亲想得更周到呢
看着郑圆圆那探究的目光,叶知秋加了一句:“像他这样的人,不仅仅属于他自
己和他的家庭,他应该属于整个社会。”
爸爸在别人的心里,竟是这样重吗十几台录音机在收录。
陈咏明那黝黑结实的脖子,像鹅一样执拗地向前伸着。那头灰白的头发,并不
使他显得老迈,反倒增添了男人成熟的美。看他那样子,不再大干上十五年,他是
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杨小东歪着脑袋,像孩子似的半张着厚厚的嘴唇。上一代人,对他们这一代人
有多少误解啊,以为打动他们的不过是吉他、喇叭裤……问题是社会能不能拿出来
真正引动他们的东西。
那个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表情十分严肃,很有派头上了年纪的男人,大概是
个大学教授吧,好像在听学生的论文答辩,时不时地皱皱眉头,是不是觉得郑子云
有些提法还不够严密呢最触目的是吴国栋,好像一个吃斋念佛的清教徒,不知怎
么一F从天上掉进了沸腾着人间一切淫邪欲念的地狱,恐怖得几乎精神失常。一双
眼睛,张皇无定地溜来溜去,好像要找个豁口逃将出去,好笑极了。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