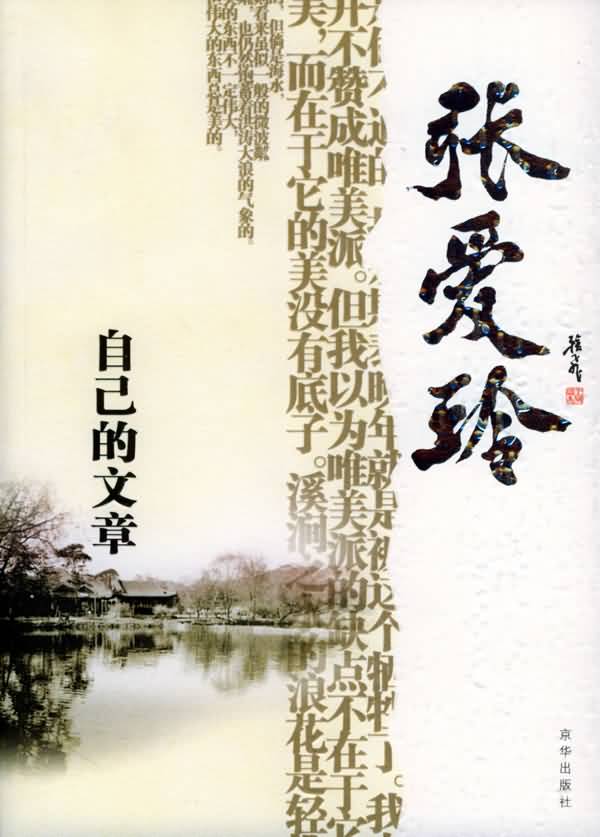张洁文集-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相当惨,不过那老头子似乎十分坚强,从没有对这位有大来头的人物低过头,直到
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就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个官司也非打下
去不可。”
这件事一定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因为在那个冬天里,还刚近五十岁的母
亲一下子头发全白了。而且,她的臂上还缠上了一道黑纱。那时,她的处境也很难。
为了这条黑纱,她挨了好一顿批斗,说她坚持四旧,并且让她交代这是为了谁?
“妈妈,这是为了谁?”我惊恐地问她。
“为一个亲人!”然后怕我受惊似地解释着,“一个你不熟悉的亲人!”
“我要不要戴呢?”她做了一个许久都没有对我做过的动作,用手拍了拍我的
脸颊,就像我小的时候她常做的那样。她好久都没有显出过这么温柔的样子了。我
常觉得,随着她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那几年她所受过的折磨,那种温柔的
东西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也或许是被她越藏越深了,以致常常让我感到她像个男
人。
她恍惚而悲凉地笑了笑,说:“不,你不用戴。”
她那双又干又涩的眼睛显得没有一点水份,好像已经把眼泪哭干了。我很想安
慰她,或是做点什么使她高兴的事。她却对我说:“去吧!”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生出了一种恐怖的感觉,我觉得我那亲爱的母亲似乎有一半
已经随着什么离我而去了。我不由地叫了一声:“妈妈!”
我的心情一定被我那敏感的妈妈一览无余地看透了。她温和地对我说:“别怕,
去吧!让我自己呆一会儿。”
我没有错,因为她的确这样地写着:
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
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去向他们质
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我们便这样地分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
担那非人间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为了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为了你将重新为
这个社会工作,为了爱你的那些个人们,你都应该活着啊!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三
反分子,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者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你呢?
我已经不怕说出这三个字。
纷纷扬扬的大雪不停地降落着。天哪,连上帝也是这样地虚伪,他用一片洁白
覆盖了你的鲜血和这谋杀的丑恶。
我从没有拿我自己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可现在,我无时不在想,我的一言一行
会不会惹得你严厉地皱起你那双浓密的眉毛?我想到我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生活,
像你那样,为我们这个社会——它不会总像现在这样,惩罚的利剑已经悬在那帮狗
男女的头上——真正地做一点工作。
我独自一人,走在我们唯一一次曾经一同走过的那条柏油小路上,听着我一个
人的脚步声在沉寂的夜色里响着、响着……我每每在这小路上徘徊、流连,哪一次
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肝肠寸断。那时,你虽然也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你还在
这个世界上,我便觉得你在伴随着我,而今,你的的确确不在了,我真不能相信。
我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又折回去,重新开始,再走一遍。
我弯过那道栅栏,习惯地回头望去,好像你还站在那里,向我挥手告别。我们
曾淡淡地、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像两个没有什么深交的人,为的是尽力地掩饰住我
们心里那镂骨铭心的爱情。那是一个没有一点诗意的初春的夜晚,依然在刮着冷峭
的风。我们默默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远。你因为长年害着气管炎,微微地喘息着。
我心疼你,想要走得慢一点,可不知为什么却不能。我们走得飞快,好像有什么重
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我们非得赶快走完这段路不可。我们多么珍惜这一生中
唯一的一次“散步”,可我们分明害怕,怕我们把持不住自己,会说出那可怕的、
折磨了我们许多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
一个活着的人会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更不要说到其它!
不,妈妈,我相信,再没有人能像我那样眼见过你敞开的灵魂。
啊,那条柏油小路,我真不知道它是那样充满了辛酸的回忆的一条小路。我想,
我们切不可忽略世界上任何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谁知道呢?那些意想不到的小
角落会沉默地缄藏着多少隐秘的痛苦和欢乐呢?
难怪她写东西写得疲倦了的时候,她还会沿着我们窗后的那条柏油小路慢慢地
踱来踱去。有时是彻夜不眠后的清晨,有时甚至是月黑风高的夜晚,哪怕是在冬天,
哪怕峭厉的风像发狂的野兽似地吼叫,卷着沙石噼哩叭啦地敲打着窗棂……那时,
我只以为那不过是她的一种怪僻,却不知她是去和他的灵魂相会。
她还喜欢站在窗前,瞅着窗外的那条柏油小路出神。有一次,她显出那样奇特
的神情,以致我以为柏油小路上走来了我们最熟悉的、最欢迎的客人。我连忙凑到
窗前,在深秋的傍晚,只有冷风卷着枯黄的落叶,飘过那空荡荡的小路的路面。
好像他还活着一样,用文字和他倾心交谈的习惯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
直到她自己拿不起来笔的那一天。在最后一页上,她对他说了最后的话:
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
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
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亲爱的,等着我,我
就要来了——。
我真不知道,妈妈,在她行将就木的这一天,还会爱得那么沉重。像她自己所
说的,那是镂骨铭心的。我觉得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
的一种力量。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不朽的爱,这也就是极限了。她分明至死都感到
幸福: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
如今,他们的皱纹和白发早已从碳水化合物变成了其它的什么元素。可我知道,
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着。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
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
那是任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
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
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
每每我看着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我就不能抑制住自己的眼
泪。我哭,这不止一次地痛哭,仿佛遭了这凄凉而悲惨的爱情的是我自己。这要不
是大悲剧就是大笑话。别管它多么美,多么动人,我可不愿意重复它!
英国大作家哈代说过:“呼唤人的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应答。”我已经不能
从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他们应该或是不应该相爱。我要谴责的却是:为什
么当初他们没有等待着那个呼唤着自己的灵魂?
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
哟!
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既然世界是这
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可能有互相不能应答的时候,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
生?可是,那是多么悲哀啊!可也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悲哀的办法!
我为什么要钻牛角尖呢?
说到底,这悲哀也许该由我们自己负责。谁知道呢?也说不定还得由过去的生
活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旧意识负责。因为一个人要是老不结婚,就会变成对这种意识
的一种挑战。有人就会说你的神经出了毛病,或是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或是
你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或是你刁钻古怪,看不起凡人,不尊重千百年来的社会习
惯,你准是个离经叛道的邪人……
总之,他们会想出种种庸俗无聊的玩意儿来糟蹋你。于是,你只好屈从于这种
意识的压力,草草地结婚了事。把那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
的脖子上去,来日又会为这不能摆脱的镣铐而受苦终身。
我真想大声疾呼地说:“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
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
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
等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选自《工人日报》1979年7月16日)
第一章
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送过来。案板上,还响着切菜刀轻
快的节奏。
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
融着太阳的暖意。
发了几天烧,身子软软的,嘴里老有一股苦味,什么也吃不下去。
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一点儿
顺心的小事,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
比方说,一个好天气;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看了一部好电影;电车上有个吊
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现在呢,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病后的好胃口
;莫征周到而又不露形迹的关切。
多亏莫征。如果没有他,谁能这样细心地照料她呢抓药、煎药、变着法儿地
调换着伙食的花样……但这番感慨莫征是不要听的,他会拿眼睛翻她,还会不屑地
从鼻子里往外喷冷气儿,好像她是卖梨膏糖的。
她高兴。不由得想说两句无伤大雅的废话——你叫它耍贫嘴也行,或是唱几嗓
子。她试着咕咕噜噜地哼了几句,不行,嗓子是嘶哑的,还带着齄齄的鼻音,两个
鼻管里仍旧塞满了没有打扫干净的浊物。
她索然地发了一会儿呆,便收起了心。真的,一个人,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
能太过放肆。这种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不知不觉地带到办公
室,或者是带到公共场合里去,就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指责或非议。何况她在别人眼
里,已经是个行为荒诞、不合时宜的人物。
她愣怔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久已忘记的法文,不禁高声地问了一句:“今天
中午吃什么”
莫征在厨房用法文嚷道:“红菜汤、腊肠和面包。”
这孩子真不赖,竟然没有忘记。这当然因为他自小生活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有教养的家庭——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正地成了一个孤儿,就像她一样。
可教养又是什么呢在那几年,它是一种容不得的奢侈品,是资产阶级这个词
汇的同义语。
人类真是一群疯狂的傻瓜,为什么要创造文明呢要是还停留在洪荒时代,或
是还用四肢在地上爬行,一切大概会简单得多。
莫征的父母,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文教授。五十年代中期,叶知秋做过他们
的学生。那时,莫征只有三岁多,很像英国电影《雾都孤儿》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奥利佛尔。穿着一套浅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