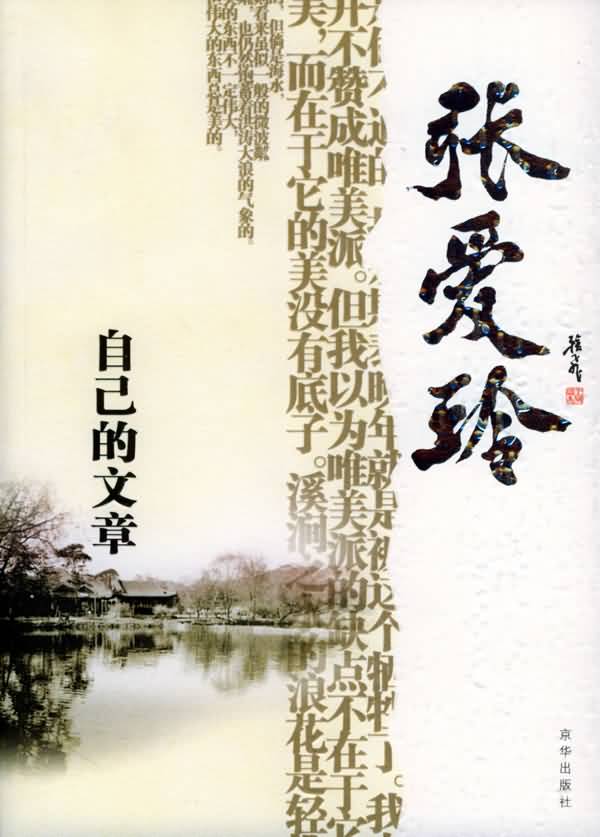张洁文集-第29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宅子里很安静,只二三亲朋在料理后事。见中宫驾到,也都回避而去,灵堂里只留下她独自一人。
装殓后的一痴,仿佛变作了另一个人,不,他是回到了儿时,谢天谢地,再也不是那个动辄“臣……”如何、如何的“中书令”了。
贾南风将紫檀木盒放进棺柩,贴在一痴身边,算是“骨肉还家”。本以为,这个紫檀木盒会是她的陪葬,想不到还是让他带了走,可见一切都有定数。
一痴确实没有多少东西留下,真应了赤身而来、赤身而去那句话。只留得横卷一幅,却无题名。外有封纸,纸上写有“留交”二字,留交何人,不得而知。
渐渐展开,慢慢看来,画中竟有一个女人,谁呢,难道是那“留交”之人?贾南风心有不甘,定睛细看,画上的女人竟是自己,而且颇得神韵。非邪非正,好一个本性之人。
神妙!神妙!
再看下去,又看出一心的悲凉。
从他们的青春年少到诏他进宫,一一画来。
其实她又何曾让他侍奉,又哪里舍得让他侍奉?不过想想,也许这就是一痴理想的、他们之间的关系。
把持朝政十年,从头过眼。心黑手辣的阴谋;捉襟见肘的伎俩;面对你死我活无可奈何的挣扎;狠下毒手时的彷徨犹豫;四面楚歌时的孤助无援……让她几乎无颜面对的过去。然而这都算不得什么,最为难得的是一痴画出了她万般的“身不由己”。
她的一生,全在这句话里了。
何为人生之大悲?不过“身不由己”。
再看下去,贾南风更是无法把持自己:寂寞芳心、栏杆倚遍;一往情深、终不得愿……这么说来,她对一痴的情爱,一痴是一清二楚的。
果真一笔一墨都是情,是他不曾对她言说、也是她不敢奢望的情意。虽与一般人、或她心向往之的男女之情,很不相同,但有情如此,她也该知足了。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将她亲自操刀为他净身的细节一一展现,这才知道自己彼时的癫狂,又见她拥着一痴的“宝”一路狂奔,分不清是从她手腕上流出的血,还是从一痴“宝”上流出的血,总之是他们的血,顺着她的朝服流淌下来,点点滴滴洒在她狂奔的路上。滴在路上的血,很快就开出一串又一串、散发着异香的小小的花朵。
原来那最要紧的,留也留不住的东西;那“远去”的声声漫漫,是他们混杂在一起、分不清你我的血,滴洒在路上的声响,难怪自己要变作一个留也留不住的脚步,从此不知何去何从地流浪而去。
另有《心赋》一阕,长短四六。骈偶、音律、句式、韵仄十分讲究,字形方正,笔画平直,气度庄严。
初看文不对题,细品足见用心良苦,她不能不说这是一痴对她的最完美的回报了。
她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
那“留交”人又是谁?
说到底,这幅横卷是不是留给她的,又有什么两样。既然是她得到这幅长卷,她可不就是那“留交”之人。
四
果然不出所料,司马玉死后不过一个月,宫廷政变,贾南风立刻被废黜为庶人。
首先冲进宫内,将她擒拿在手的,自是那赵王司马伦,而后她就被囚禁在为皇族设置的监牢金墉城。
贾南风料到,处死她的办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就是饮下金屑酒。
也无不平不公之憾,即便她死在今日,八王又能苟延残喘几日,说不定过不了几日,就得与她共享同一坛金屑酒。想不到斗了十年,最后还是没有输赢。
最后的日子说来就来,那日黄昏,数名土兵,抬一只酒坛,随在赵王司马伦身后,进了监牢。
贾南风对这酒坛太熟悉了,刘皇后本该与她同饮这坛酒,可是没等这坛酒送来,便绝食而亡,这个对手,实在令她佩服。
现在轮到她了。
她看了看近前的士兵,估算了越过她和士兵之间这段距离的时间,觉得还有把握,便探身前去抽取土兵身上的佩剑。
可她哪里快得过身手迅捷的士兵,人们一拥而上,按住了她的手。
贾南风轻喝道:“住手!”
那声断喝,既不激昂、愤慨,又是一个废为庶人的、前皇后的声音,可是听来,生生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后。刀剑在握的男人,像是听到她还在其位的命令,个个垂下了手。
她那双眼睛,毕竟是一双有过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眼睛,此时此刻,那双眼睛恰似万张满弓上的待发之箭,让人不敢相向。
可惜、可叹、可恨,如今只能引而不发了。
“不要用你们的脏手碰我。”贾南风威严地说。一点没有死之将至的惶恐、怯弱、不安。
她转过脸去,用宽大的袍袖,遮住自己的面颊,如吹奏一曲长箫,舒缓、从容地将那杯金屑酒慢慢饮下,然后随手将酒杯一掷,再没有回过头来。
临死前,她还来得及烧掉那一阕《心赋》,又将一痴留下的横卷,紧拥在怀。
她轻抚那幅横卷,想着自己没有白白用一生来相守这个人,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不管后人如何诟骂,都是值得的。
又想她英雄一世,辣手一世,叱咤一世,却死得如此无光无彩,她恨,她好恨呐,恨得她血脉贲张,恨得她翻转了五脏六腑……
这时她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声响。
即便杀几头公牛,将公牛的鲜血洒遍每一个角落,也无法化解它的阴气的金墉城,除她之外难道还有另一个活人吗。
没有一些勇气的人,如果被囚禁在这个城堡里,即便不喝那杯金屑酒,恐怕吓也得吓死。
她竟还有力气张望,是期待一个有人味儿的临终关怀吗?
原来是十多只耗子,它们匍匐地走了过来,又四只一排、缓缓地绕她而行,最后蹲坐在她的脚下,不停地抖动着它们的长须。
是为她哭泣、还是为她送葬?
如此说来,她走得不甚凄凉。
难道这不比一个所谓有人味儿的临终关怀更好吗?她该知足了。
满腔鲜血涌了上来,她尽力将头移开,以免污秽一痴的画卷,这样一幅言而不尽的画卷,原该留给后世,但愿后人可以尽数这幅画卷的故事。
可是来不及了,贾南风已经没有一丝力气移动自己的身体,哪怕仅仅是自己的头部。
人生不过如此,于是一腔鲜血,伴着多少此生未了的爱恨情仇,以及不曾与人言说的怨艾,泉涌般地喷上一痴的画卷。
贾南风的最后一瞥,留在了一痴的画卷上,心里最后闪过的念头是:
到了阴间,如何向一痴交代。
到了来世,难道还不能拥有一痴?
尾声
一
毛莉走了。而且坚持把她带来的半幅画卷,留给了叶楷文,丝毫没有奇货可居的投机意识。换作他人,即便不敲骨吸髓,也会开个让他一时难以付清的价码。
真对不起,她一定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这结果又会带给她或她的家人怎样的影响……但愿后果没那么严重,毛莉难道不是一个洒脱的人吗。
但无论如何,没有他或他这半幅画卷,毛莉可能还会像大部分人那样,不疼不痒地活着。
无论如何,在毛莉因故不能面试那会儿,让职业介绍所,另外推荐一名清洁工就好了,谁让自己对人的品格有那样的爱好,难道他雇用的是一位总统,而不是一名清洁工,尽管自己的品格不怎么样。
那样一来,这幅一分为二的画卷,也就没有了相逢的时日,或是又得错过不知多少世、多少代人了……
随着毛莉“咔嚓”一声门锁之后,叶楷文便跌坐在了沙发上,就这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地思忖着,更不知如何消受眼下的事实。
不论对接后的那幅画卷,如何震慑叶楷文,并把他推上狂奋的巅峰,这一会儿他却不由自主地掉进了落寞和迷茫。
长久以来的一份牵挂,竟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
曾经的牵挂,如晚秋时分的缤纷落叶,被一阵又一阵秋风卷走,留下一片灰茫茫的空野和萧瑟。
曾经的心思,如万马奔腾、生命力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暴风骤雨,突然被拦腰切断,只剩下点点滴滴,那生命的残余,让人好不凄惶。
叶楷文本是满登登的心,空了。
此后,还有什么能如此这般地填充他这种人的心?
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
叶楷文最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算是对所有不能“解”的事体,做个罢手。
好冷啊。
该把壁炉点燃。这样想着,便从沙发上站起……两条腿,竟不听使唤,就像在长途跋涉中耗尽了体力,如今到了终点,再也扎不出一丝气力来支撑自己。
眼睛也不好使了,像是患了重视,眼前的景物一变二、二变三地来回变幻不已。
不过他还是逞强地站了起来,先将壁炉点燃,又选了一瓶上好干红葡萄酒,斟上一杯,在沙发上重新坐下,缓缓地饮了起来。
酒是好酒,又是平日里喜爱一个牌子,今天却没了滋味,但他还是无心无绪地喝下去。此时,不喝酒又能如何?总得让自己的手里、其实是让自己的心里,有点抓挠。
喝了一杯又一杯,一瓶酒几乎见底,可还觉得阴冷,便在燃着的柴堆上,又加了一些柴段和一块固体汽油。
壁炉里的火,轰地一下旺起。平日只做毕剥之声、扮演温馨角色的壁炉,突然进发出极不安分的、繁多的声响。
这繁多的声响,让并不多愁善感的叶楷文,突然多愁善感起来。
望着扑烁的火苗,叶楷文禁不住暗暗发问:“什么是火焰的生命?”
又,“这些燃着的树干,曾经生长在哪里,河流边、山涧里、还是高山上?”
不得而知,无从得知。可是燃烧的树干,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大。
在那些声响里,叶楷文听见了河的流淌,河水在石块上的碰撞,碰撞后的飞溅、飞旋;听见了狂风穿过山上茂密的树林,被搅扰的树林发出了狂吼……
甚至听到一声断弦,不知当年这棵树在世的时候,树下曾发生过什么?
又一声高昂的、螺旋般向上盘旋的尖叫,人的还是兽的?
甚至还有一声长达数秒的哨音,猛然间,叶楷文还以为自己开了电视,而电视里正在播放足球赛,小贝又为“皇马”进了一球……
燃烧的树干听起来各有各的脾性,有些脾气暴戾,有些阴阳怪气,有些缠绵低回,有些虚张声势,有些张狂不已……
本以为它们早都死了,河流、山涧、高山、琴弦、尖叫——不论是人的还是兽的,还有哨音,毕竟不知多少年代过去。
原来它们并没有死去,而是归隐在碎尸万段的树干里,当树干燃烧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可不就失去了最后的栖身之地,怎不发出最后的绝响。
火焰炸裂,爆裂,轰然塌落,闪出刺目的火花……不过是生命最后的挣扎、释放,最后与化为灰烬的树干,同归于尽。这才是它们真正的死亡……也许未必,也许它们的生命又会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指不定又以什么方式再次与他相逢相遇。
人生的每一个拐弯儿、角落,不都藏满了奇迹、玄机……
想着,想着,叶楷文突然觉得有人站在了身后。不,不是人,而是一股阴气,在他身后游荡。周遭的气氛也变得疹人起来,作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