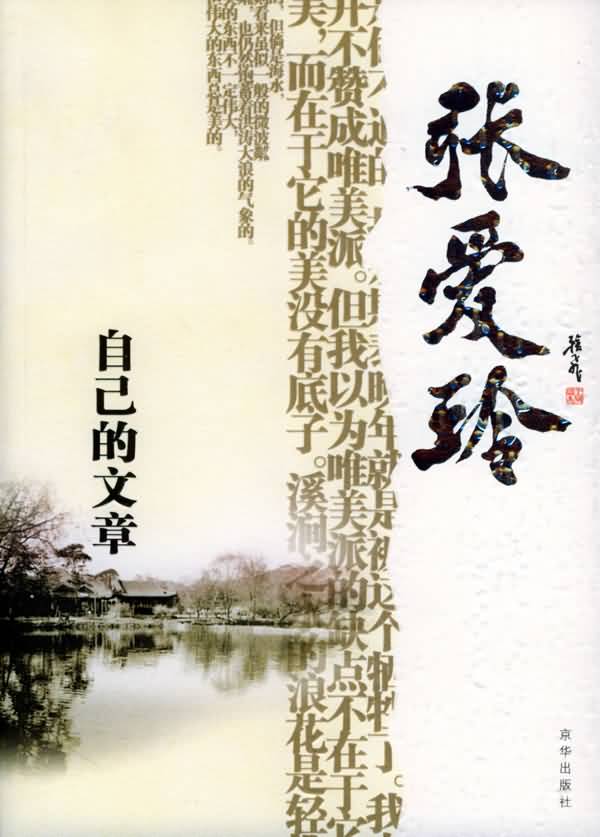张洁文集-第20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仁夫妇的四箱子衣物,顾秋水把它们一起运回了桂林。应该说顾秋水还算干过一些实事,比如说与朋友一起探望过住在建干路、被国民党软禁的叶挺将军,返回路上还游了桂王坟,吃了一顿野餐,边吃边讨论了抗日倒蒋的问题。
在桂林还遇到延安抗大的一个同学。顾秋水不使打操这个同学为何没有紧跟延安人马却辗转来到桂林,也许像他们一样“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许另有任务打人国民党或民主党派?经这同学介绍,他认识了蒋介石桂林某空军航空大队的几个驾驶员。小伙子们都很精神,很帅气,一律美式皮夹克,又是东北同乡,顾秋水就把他们介绍给了邹可仁,成为邹家的座上宾。于是邹可仁就有了策动他们驾机起义、营救张学良将军的想法。因为看守张学良将军的卫队,除副官一人是特务之外,那一连多人都可以做工作。他们还真的和张学良将军联系上了,但是张学良将军说:“不,我这个人一辈子光明磊落,死也要死得光明正大。”
人没救成,邹太太却爱上了其中一位飞行员。
一九四三年六月,作为李济深的特使,顾秋水还曾到北平、天津敌占区活动。中心工作是争取华北、东北的伪军,认清前途,脱离伪政权,不要投靠蒋介石,策动他们先搞地方独立,然后以李济深为盟主,联合各方实力,组织新的抗日集团,进一步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因为当时李济深的实力很强,想取蒋而代,所以极力联络东北军,而邹可仁他们当时的策略也是“倒蒋拥李”,可以说——拍即合。说起来大家都是反蒋,其实各有各的算盘,所以顾秋水出生人死的华北之行,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而且邹可仁只给他带了很少的钱,连回程车票都买不起,只好让邹可仁再寄。他不得不在一个小城等了半个月,才收到回程旅费。
当顾秋水通过这条号称“死亡之旅”的封锁线时,只知道抱怨邹可仁将这样危险而徒劳的任务给了他,却没有为两年前叶莲子带着吴为穿过同一条封锁线到香港找他的危险艰难,闪回过一丝同情。
此外,他们,也就是顾秋水在桂林的工作,乏善可陈。
3
叶莲子和阿苏既不过话也不吵架,也从未诉说过这种生带给她的痛苦,即便常常作为顾秋水练拳练脚的靶子,照旧一个不出声音,整天半合着眼睛,似乎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像是一心一意想着什么而又什么都没想的样子,很难得见眼珠灵活一转之间的闪光了。
只有吴为非常没出息,在顾秋水的拳脚下总要发出鬼哭狼嚎的曲调,使耐受力十分强的叶莲子也感到了承受的极限。
阿苏也时起烦恼,知道顾秋水现出这样的兽相是为了她,心里便渐渐有了负担,可又下不了决心一走了之,她舍不得顾秋水。再说她又孤注一掷地把一切押给了他,只好昧着良心混下去。
顾秋水有时也思量这三个人的日子,认为自己并没有安心坑害这两个女人,眼下的情况是环境造成的。说了归齐,他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顶多是娶个小,或安两十家,或三个人一起过,如此而已。叶莲子为什么想不开?瞧她那个哭丧脸!也许这本来就是逢场作戏,都是临时的事,所谓“乱世男女,聚散如水”,将来给阿苏找个工作送她走就完了,时间一长,什么都会过去。
要是阿苏知道顾秋水这一番思量会怎么想?人财两空的她又怎么活下去?吴为几乎一天来一次鬼哭狼嚎,这让叶莲子反省到,孩子没有艾务为这个婚姻承受她不应承受的暴力。再说桂林终究不是香港,语言不再是她工作的障碍,便恳请金奉如帮她在柳州找了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带着吴为出外谋生。
这不是叶莲子和吴为的第一次合作,还在香港时,她们就组成过一个比之革命党人的战斗性、吃苦耐劳性也不差的小分队。与和顾秋水一起生活的日子相比,叶莲子出走柳州的感觉无法评估,对吴为来说绝对是翻身得解放。
柳州有柳江,江上有桥横跨南北。因叶莲子就职的小学在桥南,她们也就租住在桥南河沿东侧一户人家的阁楼上,距学校不算太近。远近的问题只能从房租考虑。
阁楼上只住着叶莲子和吴为。到了夏天,柳州的阁楼就是一个烤箱,但凡有一点钱的人谁愿意把自己放进烤箱?
除了常常要跑警报,似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防空洞却在柳江之北。日本飞机像一个忠实的、夜夜归家的丈夫,而不是那种“不回家的人”越是晚上,空袭警报越多。架在柳江上的柳州桥,成了叶莲子和吴为往返跨越最多的一座桥。
其实警报第一次拉响她们就动身了,可日本飞机总是不等她们通过那座桥就飞临上空,有时她们甚至还在桥的这一方。越是在不该闹的时候偏偏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让叶莲子觉得没有指望的呆为,在该哭、该闹的非常情况下反倒安静起来,甚至比有些成年人还冷静,让叶莲子十分意外。这可能得益于她在“家乱”中的历练,那真是一种全方位的训练。比之顾秋水制造的“家乱”,“战乱”又有什:么可怕的?飞机当空时,不用叶莲子说,吴为就会比叶莲子更迅速地扑倒在路边的草丛里,躺倒之前还不忘记拉叶莲子一把。她侧着头,静静注视着天上的飞机和探照灯交错的光柱,看着轰炸机排成整齐的队伍,三架一组,游戏似的忽上忽下、时远时近,而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忽聚忽散,交织成一组又一组网状图案。
有一次,她们正挤在桥上,“兴致勃勃”地向对岸奔跑,日本飞机就到了头上。一枚枚炸弹目的明确地向柳江桥扔了下来,叶莲子扛起吴为,在沉默的人流里,人贴人、人挤入地奔着。
落进江里的炸弹,冲击出巨大的水浪和一股股水的飞柱,桥身颠簸起伏得像是一条任人随意抛上抛下的链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冲向空中的水柱,断裂后又劈打下来,淋湿了她们全身。老桥早就被炸断了,供人们逃亡的这座桥是新架的简易桥,桥身很低,两边没有栏杆。有人掉进了柳江,所幸她们还在桥上没头没脑地跑着。跑,似乎成了她们的惟一目的,从未想过炸弹已然在头上开花还有什么可跑,对岸的防空洞还有什么意义。
不知什么东西燃烧起来,一桩桩火柱突然竖立在桥的四周,火焰和火星在桥旁、在江中,如暗红钓菊花,一朵朵绚丽绽开。
就像家乡人说的那样,叶莲子真是命大,密密麻麻的炸弹,有些即便紧擦桥身而下,却竟没有一个扔在桥上。
如果不是那场火灾,她们可能就这样虽然担惊受怕,但可不再受制于顾秋水地过下去。
那天睡到半夜,“砰——”的一声巨响,接着就浓烟四起,空气里弥漫着各种物体燃烧的气味;接着就是木头,而且是不饱满的木头哗哗剥剥燃烧的欢叫。起初叶莲子以为又是日本人的空袭,炸弹命中了这栋小楼,便一把抓起吴为,往楼梯口跑去。这时细弱的火苗已钻过楼梯的每一条缝隙,一旦钻过缝隙,便多姿多彩地蓬勃起来——叶莲子这才知道是失火了。
同时也明白了,她们被困阁楼。可她没有呼救,此时此刻谁能听见阁楼上的呼救?即便听见谁又能来救她们?
尽管火苗从楼下而来,可她们只有冲到楼下这一条活路,这真有点像她在生活里的位置。没有办法,只有抱起吴为,迎着火苗往下冲。
下到最后一级楼梯,发现进出一楼与阁楼之间的门被房东锁死,她和吴为是无望从大门逃生,只好烧死在阁楼上了。
她倒不是十分悲伤,谁说这不是一种恩惠!可是吴为呢?!
又反身往阁楼上跑去,细弱的火苗瞬间就发展壮大为火焰,几乎贴着她们的脊背追撵着她们。
返回阁楼还是投有出路,下意识地冲上阳台,这才看见大火如一条巨龙,在整条街上斜里、横里,恣意地蜿蜒、窜动,所到之处立刻火焰腾起,这一处火焰与那一处火焰首尾相连,十分壮观。
再往楼下一看,天井像一口被包围在火焰中的“黑井”,可这也是她们逃离阁楼的惟一通道。
叶莲子不知哪儿来的爆发力,三把两把就把阳台上糟朽的栏杆拽下来,然后把吴为往下层屋顶上一扔。就像后来的武打片那样,吴为安稳地飞身落下,又在那屋顶上不惊不慌地飘然站定。
不知什么动力驱使,叶莲子回身冲进阁楼。进了阁楼才明白,她是要抢救那点可怜的家当,至少得把抽屉里那点钱抢出。在她一片混乱的脑子里,这个念头似乎比死亡的危险更固执地纠缠着她。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之所以将生命置之度外去抢救所谓的钱财,不过是以此验证一下顾秋水。好像另一个理智得不像是她的脑子的脑子告诉她,在生命攸关的时刻,那个叫做丈夫的男人是、不能靠的。这个理智得不像是她的脑子的脑子,只在非常条件下才会出来工作。
五岁左右的吴为没有死守在那屋顶上,而是随意走动起来,是寻求一条活路,还是好奇,还是对危险的不解?
柳州的房瓦像是又薄又脆的炸薯片。她那双小腿有多少力量?可她轻轻一踩,就把那些瓦片踩裂了。赤裸的小腿小脚陷进瓦碴儿,碎裂的瓦片却像刀子般锋利,毫不怜惜地将她的小皮小肉划破。血滴如一滴滴红色的泪珠从腿上渗出,汇成一条条细流,顺着小腿蜿蜒而下、纵横交错,真是一张白纸上好画最美丽的图画。
她向东而行,迎面碰上一堵吸盘似的火墙。对于这个操蛋的人生,她也许比死不改悔的叶莲子悟性更高,也许冥冥中有人指点一进入那火墙其实正是脱离苦海之道,所以不知后退,继续前行。可是一头扎进阁楼以生命来验证顾秋水的叶莲子,却还有一份神经如雷达般跟踪着吴为。她的血在吴为的血管里喊了起来:“站住,站住。赶快离开!”吴为站住,折回来又往西走。西面的火坑如盛开的血色玫瑰,暗色的花蕊中央,应许了多少她那不长的生命不曾见识过的、暧昧的欢快。在这关键时刻,叶莲子又启动了那个制动闸。
不论东、西,都可以让吴为葬身无地。可她并没有尿裤子,不但不恐惧,还与火焰镇定地对视,眼睁睁地看着火焰热烈狂放,一路扫荡过来,所到之处是燃烧的热情和热情燃烧后的灰烬。或许她的灵性感知超过了肉体感知,就在这一刻,她接受了烈焰的教唆,日后她异常奔放的热情和直至化为灰烬方才善罢甘休的作派,可能与亲历这场弥天大火有关。
她的悲观主义也可能始自烈焰与灰烬的反差,烈焰断裂后的挣扎、惨淡、冷寂,如逆风中二支摇曳的烛,以生命之无定又让她心生悱侧。
这烈焰又似乎是为孤零人生进行的一次洗礼。经过这样的洗礼之后,吴为的人生是注定孤零了。不过两三分钟时间,阁楼已是满室浓烟,什么也看不见了。火苗从地板四周和一条条地板缝里蹿了上来,每条地板缝里都是一溜火苗,每条地板都像是镶了一条火边。
平时穷得要什么没什么,可现在叶莲子却觉得富有得不得了。她只有两只手,不知取哪一样为好,哪二样都是她们母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