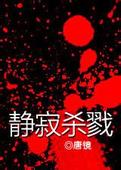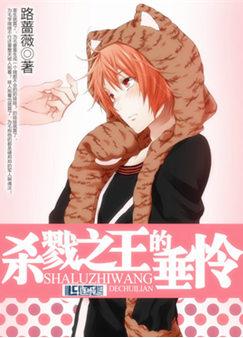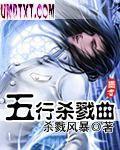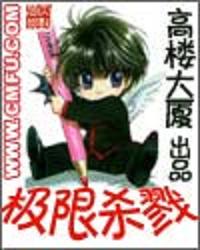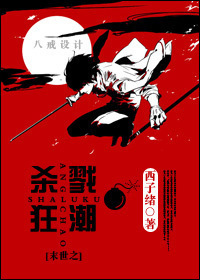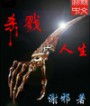面对面的杀戮-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惺俊懊挥胁斡搿U庥胨牡赖鹿巯嚆!K朗粝虏换崽埃簿兔挥凶柚顾牵亲叩酱遄拥牧硪槐咦讼吕矗跤舻乜醋诺亍!甭骄蹩硕ぢ罂ㄋ固刂惺浚铡霸侥侠媳凑健保抖臼勘鞑椋禾骄棵谰秸镄小罚úㄊ慷伲�1972),页29。另一名不愿参与弓虽。女干、屠杀的士兵只是走开了一小段距离: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36。类似地,一个排长原是摩门教的牧师,他能“容忍弓虽。女干的发生。不是说他自己会去做,只是他不会去管,军令在上,他一个人算得了什么?”陆军埃德·墨菲中士,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48。同样地,无论军阶、军种如何,战士如未能保护好平民同样会被视作残忍。年轻的泰里·惠特莫是名来自田纳西的黑人。一次在执行“搜索奸敌”任务时,他见一个小女孩和她弟弟在一旁看着美军在毁掉他们的村子。“我们把她放到树下就走了,”说这话时他有点迟疑,“我不知道——也不想说——但我想她一定被他们杀了。我先走了。不想亲眼见到这一切。我知道,就是我在场也会有人将她毙命——我不忍心看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先走了。”泰里·惠特莫,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76。其实,他完全可以救下那个小女孩和她弟弟:他没有,他选择了走开。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20
也有战士试图干预对平民的滥杀,但这样的人少而又少。尽管如此,在美莱就有人“积极阻止”:他就是休·C。汤普森准尉,1968年3月16日屠杀发生的那天,他正驾驶侦察机飞临美莱。看到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围困、被枪杀,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他就意识到向受伤者身上扔绿色发烟弹、表明他们需要医治根本无济于事:没人会向他们提供救助。早晨十点刚过,他发现一群妇女、孩子正冲向一个掩体,后面全副武装的士兵紧追不舍。他意识到一场血腥屠杀又免不了,于是把直升机停在掩体(这会儿村民已进入了掩体)和追兵之间,下机质问领头的中尉。那名中尉说只有向掩体里扔手榴弹才能把他们赶出来。汤普森当时很激动,不太理智。他一边呼唤两名机载枪手准备拿美兵练枪,一边只身(他没带武器)进入掩体,劝里面的人出来。接着他把这拨人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这时他仍很气愤,又让机组人员回到此前有人遇难的壕沟,去看是否有人还活着。他们在血污中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一个两岁大的婴儿被压在死尸下面,于是又驾机把婴儿送到昆嵩市的一家平民医院。
汤普森所做远比“规避”暴行要多:他试图阻止平民被杀,也履行了报告的责任。当天下午,他递交了一份行动报告给顶头上司和空军第123营2连的指挥官(他们都觉得他有点“夸大其事”)。他跟师炮兵部队的牧师讲述了这件事,后者许诺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将这件事公之于众。其实,汤普森并不反对杀人本身:就在大屠杀的早晨,他还看见一个自己疑为是越共的人,于是一直驾机追赶并向其射击。玛丽·麦卡锡,《麦地那》(纽约,1972),页74。但他认为,杀虐不能等同于战斗。面对虐杀,他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无论精通国际法的律师还是枪炮后面的士兵,要判定某一行为是否算得上暴行都不容易,但一般认为,近距离无端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是不对的,虽然对其发生军、民都有责任。不能否认,暴行在各个层级都有发生,但尤以杀害俘虏为多。尽管如此,战士一般还是能在虐杀和战场杀人间划出条界限,而且也无意把前种行为描摹成能欢快的战斗。其次,即使有人未参与施暴,他们也极少抗议。休·汤普森在美莱表现出的义愤带着种老派、稍显古怪的色彩,在当前讲求实际的军事体制下已不太合拍。在精明、讲求实际的军队里,漠然的旁观者虽只是在身体或精神上摆脱了那些骇人的场面,却直能成为“高尚”抗命者的代表。与之相比,那些积极干预、试图阻止屠戮的士兵反倒让人不安,他们的作为暴露了残酷环境中人的丑恶,并不时提醒我们,人虽能描述杀戮和漠然,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挺身抗命者的愤慨或无数冤魂的苦痛。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
在那儿,可以尽情欢笑——
因为死成了荒唐,活着更甚。
我们拿刀剖肉露骨满是力量
不觉恶心,悔意更无从谈起。
威尔弗雷德·欧文,“自辩”,1917威尔弗雷德·欧文,“自辩”,收乔·斯托尔沃锡(编),《威尔弗雷德·欧文:诗全集及断片》,卷1(伦敦,1983),页124。
陆军中士布鲁斯·F。阿奈洛——朋友叫他“布迪老兄”——曾在越南驻扎,“特能打仗”。他先后获过紫心勋章、银星奖章、军功奖章、一枚南越陆军颁发的奖章和一次射击嘉奖。他性格有点反叛,一向穿着邋遢,口袋露着女友的红色吊袜带,铠装防弹背心后背画着个大而多彩的卒,意在称颂“和平”,也是为了纪念他最心爱的唱片:鲍勃·迪伦的《卒在棋中》。阿奈洛曾公开表示,他很高兴被派遣去搜查地道,看里面是否有藏匿的武器或食物,这样就可以避开地上的杀戮。他曾恳求自己的守护神“放松一小会儿,让我受点小伤”。所有可以躲避的方法他都考虑过,其中包括故意负伤。
经验告诉我,平日里行事要低调。经验还告诉我,受伤了要高调。被流弹击中能休息两个礼拜。只要两枚紫心奖章,你就能永别战场。
他甚至想过逃跑,但也知道这只是意味着得舍弃战友而并无法逃离整个部队。他看不起上级,嘲讽他们试图“亵渎(我们的)头脑”,自己“杀人成瘾”却让别人去冒生命危险。他说自己那些奖章不过是“这愚蠢的战争游戏”的一部分:“我是英雄吗?军功章买不来面包,也没有办法让良心稍安,”他在日记里坦承。
读阿奈洛的日记看不出他是个杀人高手,备受上级器重,虽举止“不像军人”,但“最能带兵打仗。脑子很清楚。”阿奈洛的问题在于他还年轻,对事情太敏感。他四岁就死了母亲,之后和兄弟一块被父亲送进孤儿院。由于少人关爱,他一接到女友的信就止不住啜泣。“这太美好了,”他在一次收信后写道,
我无法描述接信时的心情。我的高兴劲,再多的字也无法表达万一。光信封我就要读它三天。拆了信,把信头再读三天。然后每句话三天。这样就能撑到下封信。
但战斗慢慢改变了他;他变得“有点冷……甚至冲着小孩也大喊大叫。”当地一名妇女的米被缴了,他会可怜她,帮她讨公道,但也承认常常感到太累了,也就管不了枪口对着的是谁,特别是如果不声不响就可以了结人的性命。他的同伴回忆说,他们都觉得
手榴弹挺好……虽然也是杀人,却没那么直接。不是一枪一个那样打。你不必盯着具体的人,然后开枪把他撂倒。只消拉一下引线,把手榴弹扔出去,就炸开了。碰着谁准是非死即伤。阿奈洛就喜欢那样——手榴弹可以不直接地杀人。
阿奈洛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有战争,而且毫不掩饰对越共的仰慕:“他们的事业值得他们献出生命,这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又不垂涎这块地方,”他一语惊人。一次浴血奋战后,他在诗里写自己是个“傻瓜/……陷在/毁灭之眼”。他试图“诉说自己的感受/在地狱般的日子里”却不能:
其余留在了惊恐的眼里
以及每个人
空空的脑际。
“太多的血,”是他另一首诗的开头,诗的结尾是:“我没理由地杀人!”
从诗里可以看出,阿奈洛满是对杀戮的悔恨。他讲自己是怎么拿尸体胡闹,奸淫妇女,一个排怎样“逢人就杀”以超过别的排的“杀人记录”。一切都是“粗野、荒唐、无谓的杀戮。良心却安然不受谴责。”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境况(见插图13)。在1968年5月2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巡逻所见:
看到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就喊,“看天”(意思是“过来”)。他转身看我,眼睛立时瞪大——然后撒腿就跑——我开了枪。他顺着条小道跑了有一百米,手里捧着流出的内脏。想起自己方才的举动我就想吐……并不自以为得意。
次日,他在日记里试着为自己的举动正名(却做不到):
我还是我吗,抑或不是,我太紧张了——弦绷得太紧,太易受惊扰,容易生气,——嘘!别说了。我太紧张,因为再过几天我就要轮休了。
跟随罪感而来的是对报应的恐惧。阿奈洛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在像草间独自爬坡,走啊走,就是走不出越南。还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和一个越共战士并肩站在山坡上。两人都“眺望远方,看远处的起伏,看碧蓝的天之类”。他对那个士兵说,“你的国家太美了”,越共兵回答说,“嗯,谢谢。我也觉得这儿不错。”然后,两人转身直视,突然意识到对方原来是敌人。梦中,阿奈洛说,“我们互相开了枪,因为我们是敌人。”几天后,在山间搜索一家手雷厂的过程中,他遇难了,在越南只呆了七个月,死时还不到21岁。陆军布鲁斯·阿奈洛中士的日记及与密友戴夫·朗的谈话,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1—19。首载《工作刺激杂志》,1971年5月15日。
对布鲁斯·阿奈洛这样的战士来说,无法弥合血腥的战争和内心道德信念间的鸿沟使他们身心俱疲。然而也正是这些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努力使他们得以继续战斗。“不可杀人”的戒律声如洪钟、斩钉截铁,实际却成了杀戮的头条准许,至尊的禁令反倒激起了被压抑的欲望。在构成我们道德世界的诸多习常法则之外,还有宗教箴言和司法训令,后两者对塑造战场上的表现至关重要。战时,有的杀戮行为是被禁的;但不划出一块禁区,杀戮怎么能得到支持,最终被宽恕?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2
个 体 罪 感
个人悔罪在军事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极端暴行应受指责的看法在现代战史中已无立身之地。杀戮过后,公众恳求举国赎罪已成常例,要想寻求自我谅解只有在阴湿的教堂壁龛或遮暗的私人卧室里才成为可能。历史学家不愿提及个人在战争中的责任,甚至认为质疑在战争中大开杀戒的士兵的“良心”“颇成问题”。乔治·克伦,“纳粹大屠杀:口是心非”,收艾伦·罗森伯格、杰拉尔德·迈耶斯(编),《纳粹大屠杀回声:对黑暗年代的哲学反思》(费城,1988),页255。这样的顾忌本来正理应当,(我们下面会看到)倒是士兵自己不时提出个人应负责的问题。有的甚至强要回答。
与之相对的是军方发言人在谈到责任、悔罪时的坦诚态度。除非发生不必要的暴行,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