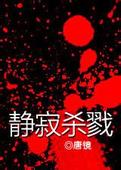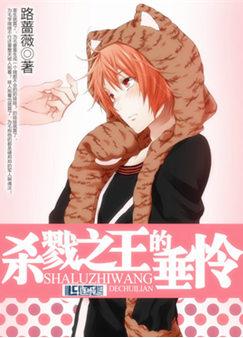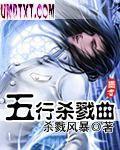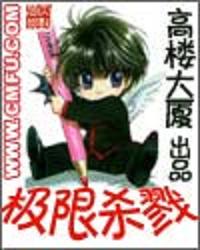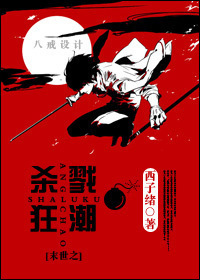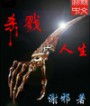面对面的杀戮-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形荆妒罚锥兀�1971),页8及84;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61;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在宋美拒绝开枪士兵的故事”,《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2月14日,页116;陆军威廉·皮尔斯中将,《美莱调查》(纽约,1979);“谁该为美莱负责”,《时代》,1971年3月8日,页19。
卡利并不特别“喜欢”杀人,“冷血地”屠戮毫无抵抗能力的百姓就连最卑劣的人也会觉得不太合适。即使这样,在两次世界大战和越战中,暴行仍是一大特点。像1968年3月这天北越连队多数人的暴虐行为,是没法用理性分析的。对其最恶心的追述例见马丁·格申,《杀或被杀:美莱实情》(纽约,1971)。无异于涩情文学,充斥着施虐狂、窥淫癖追求轰动的取向,无非是说那天他们这些“双重老兵”(因为他们首先奸淫、然后杀害了当地妇女)在美莱体验的性乐不过是短暂的,且搀有对自己的厌恶,算不得罪恶深重。许多法律、历史层面的分析又总是一笔带过,这对受害者是一种残忍:同情竟在死刑犯(他们“都是人嘛”)而非受害人一边。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暴行的主使其实符合我们对勇士的一般想象,而抗拒这些暴行的许多士兵倒远非我们可以期待的道义力量,他们的超脱同样是一种残忍。战场不是没有道德律令,不过热心参与是它的惟一形式。
“战争是残暴的”
在20世纪,国际法、法庭裁定、军队条例和道德准则共同阻止了各种针对平民、战犯的有预谋但无意义的屠杀,且(自1944年以来)要求目击了此类行为的士兵向上级报告。目前,战争法已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法律体系,研究者难以记数。最有帮助的有杰弗里·贝斯特,《人与战争:武装冲突国际法的近现代史》(伦敦,1980);杰弗里·贝斯特,《战争和1945年以来的国际法》(牛津,1995);理查德·霍姆斯,《论战争和德行》(普林斯顿,1989);迈克尔·沃尔泽,《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纽约,1977)。越战比较麻烦,因为双方没有正式宣战,而且参战方也不是两支或两支以上可以分得清楚的部队。但从1965年开始,美国政府宣布该战争为一次武装国际冲突,北越军队是敌人,越共是北越交战政府的代理人。自此国际法可以适用。就本章而言,最重要的包括《海牙公约》(1899和1907)、《纽伦堡原则》(1946)和《日内瓦公约》(1949)。根据《海牙公约》,若敌军战斗人员业已“放下武器或不具备任何防卫手段”则不应伤其性命。公约还要求对每一名战俘均应给予“人道的对待”。《纽伦堡原则》第六将杀害或虐待平民或战俘的行为均界定为战争罪。1949年《日内瓦公约》认为“没有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员,包括已投降或因伤病、羁押等原因已丧失战斗能力的武装部队成员,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人道地对待”,该公约还特别禁止“对生命和人身施行暴力,特别是各种形式的谋杀、碎尸、虐待和酷刑”。利昂·弗里德曼(编),《战争规则:文献史》,卷1及2(纽约,1972),页225,229,314,318及526及《纽伦堡原则》,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107。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3
除国际法外,军队还有自己的各种规章、条例。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军队都禁止滥杀平民、已解除武装的人或伤员。越南的情况要复杂些。负责驻越美军的指挥、控制和补给的美军越南援助指挥部在1966年3月3日以前发表的指令只涉及他国军队违反《日内瓦公约》、针对美国士兵犯下的战争罪。直到其1966年发表了204指令才把美军对别人犯下的行为也视为战争罪。该指令明确指出
针对业已投降的武装部队人员或因伤病等原因未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员的蓄意杀戮、拷问、非人道对待或蓄意对其身体或降造成极大痛苦或严重伤害的行为,均为战争罪。
此外,粗暴对待死尸、攻击未设防地区或非军事目标,还有劫掠也都被界定为战争罪行,知悉其发生的任何军人都有义务向指挥官报告,且“越快越好”。陆军乔治·普鲁少将,《法律之于战争:越南1964—1973》(华盛顿特区,1975),页76。
但最难的不是确定战争罪行的构成要件,而是确定谁应负责。全面的回顾,见陆军威廉·帕克斯少校,“战争罪的长官责任”,《军法评论》,62期(1973),页1—104。“长官负责”的托词(“只是执行命令”)一直不绝于耳:但能站得住脚吗?在英国,1749年的军规就指出,军人只须执行合法的命令。但拉沙·奥本海在《国际法》(1906)第一版中却说“如果部队成员遵照上级命令犯下罪行,其人不应受罚,只有其上级才应负责”。1914年版的《军法便览》第433节也要求战士绝对服从上级军官的任何指示。这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1944年合法命令的概念才重又被人接受,这样战士个人也要为违背“无可置疑的战争准则”和伤害“人类普遍情感”的行为负责。拉沙·奥本海,《国际法:专题论文》,卷2,页264及英国《军法便览》,1914年及1944年,14章,433节。在美国,军规一直没有触及上级命令的问题,直到1914年版的《陆战条例》说明,武装部队成员因执行政府或长官命令而违反战争法享有豁免权。但这一规定在1944年被推翻,新添的345。1条款认为士兵个人应负责,但如只是奉命行事,在“确定其刑事能力时应予考虑”。对这些变动最好的论述见格文特·卢伊,“上级命令、核战争和道德律令”,收理查德·瓦色尔施特朗(编),《战争与道德》(加利福尼亚,1970),页115—134。1956年的美国陆军野战手册也认为,不可以用上级命令作为开脱的借口,除非被控个人“当时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该行为是非法的”。《美国陆军野战手册》,“地面战法则”,1956年,509节。美国《军事法庭便览》(1969)认为,“在正常执行合法任务时”杀人情有可原,但如该行为“明显超出其权限,或凭常理可判断该命令为非法”则无可原谅。美国《军事法庭便览》(1969),197节。在世界范围内,《纽伦堡原则》(1946年)指出“任何人犯下违背国际法的罪行,其后应为此负责并准备接受惩罚”,“只要可以作出道德选择,则依照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本身并不能免除其在国际法上的责任。”第一、四两条原则,《纽伦堡原则》,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107。
虽有法律、规章、公约的限制,战争暴行还是大行其道。越南的战事虽不能说是无节制的纵欲和屠戮,驻越士兵(尤其是美国的正规军和澳大利亚部队)也曾否认那里的战事特别血腥,例见陆军约瑟夫·安德森上尉的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33;肯尼思·迈多克,“越界?——澳军暴行问题”,收迈多克(编),《越南忆旧》(悉尼,1991),页151—163;乔治·莫瑟,《倒下的士兵:重塑两次世界大战的回忆》(纽约,1990),页110。美莱所发生的一切仍不是孤例。许多军人(美军如是,澳军亦如是)都承认自己曾嗜杀无度。步枪手巴里·克瓦纳是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艾冯山谷派往越南的,他用让人不敢轻信的语调叙述了在越南的那些“倒霉的日子”,天天得和一个“新到的、又高又壮的澳大利亚人在一起,他就知道把两盒子弹全射进一个挑水的十来岁男孩的身体里。那个男孩固然可能是越共,可至于用两盒子弹吗?”克瓦纳还说,某个晚上他们排听到“灌木丛里有人在跑”,就开了火。第二天早上“发现不过是邻村一队走失的女学生。那个高大的澳大利亚人接着开枪把几个活着的也打死了,这样丑闻就不至于传出去,”克瓦纳回忆说。步枪手巴里·克瓦纳,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更多的澳军暴行,见派特·伯吉斯,“心里仇恨的村子”,《年岁》,1976年8月21日,页16;伊恩·麦凯,“战争的实话和谎言”,《广告人》,1976年8月5日,页5;艾伦·拉姆齐,“如何不用担心,去爱越共”,《国民评论》,1976年8月6—12日,页1046。其他士兵只能悲哀地发现自己的良心正逐渐受到侵蚀。一名澳军准尉回忆说,他刚加入越南共和国军某部时,长官每杀一名战俘,自己“都要嚷嚷”。但不久就变了:
现在,长官会先看看战俘,再看看我,那眼神意味深长,彼此都心照不宣。我会出去溜达几分钟,等我回来时别人会告诉我,那战俘试图逃跑,被枪毙了。澳军准尉,引自杰拉尔德·斯通,《没有英雄的战争》(墨尔本,1966),页131。其他澳军的例子,见亚力克斯·凯里,《澳大利亚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8)。
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4
驻越美军要更残忍。“我们灭过整个的村子,”一名黑人特种伞兵描述说,“我们(都)怕下一个是不是会轮到自己被送上军事法庭或被要求出庭给出不利于自己人的证据。”小阿瑟·伍德利,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1。一名老兵在一首名为《我的谎言》的诗中写道:
那可能性当然
是存在的
她或许很纯朴。
但我只能奉命行事。
而且即使
真实与美好的东西,
也不能有例外
所以,
乘她还没有走远
还没有从眼前消失,
我做了
自己
该做的事。克雷格·威登,“我的谎言”,收简·巴里、W。埃尔哈特(编),《非军事区:老兵在越南后》(宾夕法尼亚,1976),页24。
奸淫、拷打和谋杀常常见诸报端。例见比尔·阿德勒(编),《越南来信》(纽约,1967),页42;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不是孤例:每位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3—15;理查德·博伊尔,《龙之精华:美陆军越南折翅记》(旧金山,1972),页137—139;唐纳德·邓肯,《“绿色贝雷帽”之抨击战争》(伦敦,1966),页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埃里克·诺登,《美国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6);“事关特种部队”,《新闻周刊》,1969年8月25日,页26—33。到上世纪60年代末,人们对越战的失望已与日俱增。这时,许多老兵站了出来“指证”在公众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