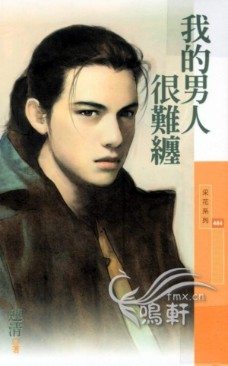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当然不止一个两个的。如果只有一个两个,就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刚才说过,“淫心”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既然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免死狐悲,物伤非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因此,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理快活”了?
其次,过激才有效。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辱致死。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
如果说在“文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鸡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奸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一件是在那“淫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一件是在议论那“淫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淫”证己之“贞”。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不过,义愤再强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如果口水吐到“奸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所被其“污”么?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一)荤话与风话
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奸夫淫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辱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两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奸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
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如此积极主动地去捉奸,趋之若鹜地去看奸,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颇感兴趣。没有兴趣,是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没有艺术兴趣的人不会去看画展,没有科学兴趣的人不会去看实验,对于性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也不会去看捉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捉奸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的兴趣。
性兴趣的产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其实也包括性与性爱在内。古人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食(饮食)与色(性爱)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人们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尝百味,吃遍天下,却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面,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做爱毕竟不能像吃饭那样大张旗鼓,大摆宴席。然而问题在于,可以公开谈论的“吃”,其实主要是一个“做”的问题(做饭和吃饭),而不能公开讨论的“性”,却又恰恰是一个“让人来说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书中所指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而言语,被说出来。事实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压抑的时代,“说”也是一种宣泄,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轻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用“说”来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忏悔”,而在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田间地头、茶楼巷口的“闲话”。
中国人爱说闲话,尤其爱说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
什么是“闲话”呢?说是人们在闲谈时说的话。所以,但凡一切与正事或公事无关的闲事,一切个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为闲话的话题,而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看作闲话。男女关系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对于议论者而言又是与己无关的闲事,又不能公然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官话”来讲,当然多半也就只能变成闲话。闲话虽然“无关宏旨”,但又必须“饶有趣味”,大家才乐意去讲。男女关系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当然也就会成为闲话的“热门话题”。
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无非两大类。一类是涉及到自己身边人身边事的,往往带有非正式议论批评的意思;另一类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只是谈今说古,泛议男女,是闲了没事说说好玩,供听者一乐的。前一类现实性强,是热点,但要有机会(身边发生了“搞男女关系”的事)。所以,平时说的多的,还是后一类闲话。
后一类闲话,又分有情节的和无情节的两种。有情节的通常叫“荤故事”,没情节的则叫“荤话”。荤话包括各种与性有关的俚语、俗话、民谣、小曲、典故、暗号、谜语、歇后语,也广义地包括“荤故事”。中国历来就有这类荤话,有的“文学水平”还很高。比如,抗战期间,有人撰对联一副赠新婚夫妇,曰:“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从字面上看,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娘子关、珍珠港两大战役,“美人”也可以理解为“美国人”。但用于新婚夫妇,又显然别有含义,是不折不扣的荤话了。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荤话”的特征:含糊其词,一语双关,多用隐喻、象征、借贷等修辞手法,让听者在似与不似之间自由想象。清人李渔在《答同席诸子》中云:“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中国的民众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美学著作,在这方面倒是“无师自通”。他们深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