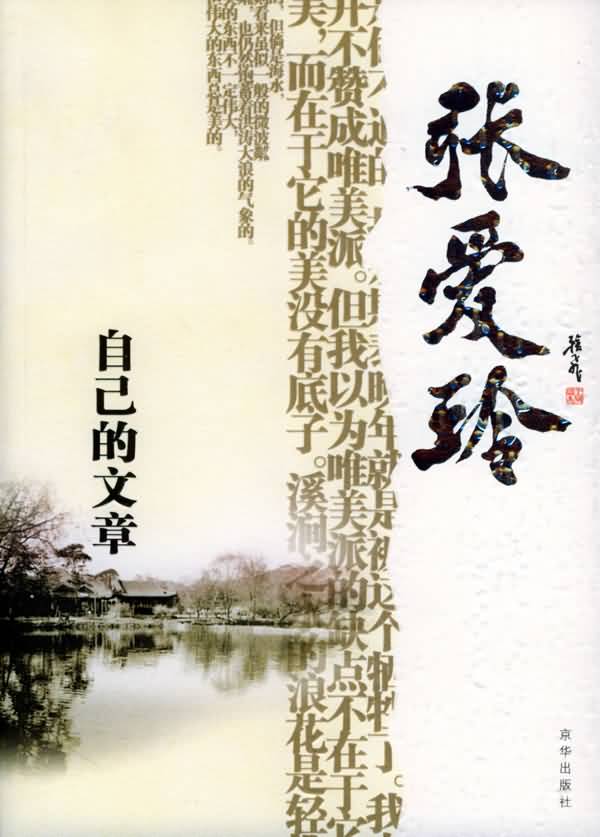池莉文集-第8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相信有正必有反,有阴必有阳,有虚必有实,有水必有火,有上必有下,有盈必有亏,有动必有静,有昼必有夜,有得必有失,有黑必有白,有寒必有热。我相信有存在,也有不存在,有物质,也有反物质。我相信所有的可能性。我永远被新奇的不同寻常的事物所吸引。我因此而不断地怀疑与幻想。
我们的所知有限是很多事物可以证明的。时间就是一个证明。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大众化的通俗的标准衡具,人们通过钟表的形式来感知它,以免弄乱了大家集体上飞机的约定。但是事实上,时间不仅仅是线性的和通俗的。在人的个体生命里,它可以停止,比如死亡;可以倒流,比如回忆;可以缓慢,比如痛苦;可以膨胀,比如幸福;可以分裂,比如我曾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姑娘同时又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调皮孩子。它还可以由空间的转换而改变速度,比如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登上某座山峰,可是一架飞机在瞬间之内就完成了一切。而现在人们只是简单地把时间贯串在一起,就大胆地指着它说它是历史,这使我没有来由地联想到了医学。西医的迅速发展神奇得就像上帝,几乎所有的人为了保命都得去吃药。事实上所有的药物既治病又生病,毒副作用无法可解,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一旦生病就赶紧去吃药,只有少数的智者去探讨和思考自己的身体到底缺乏了什么。
正因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对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评说,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个体生命去轻率地承诺重大的质问。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现实的分寸感。所以我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我的写作仅表达我个人以为的对于生活的准确感知。
我首先希望我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正常人。我能够与大多数人一样吃东西很香,穿着得体,知热知冷,知好知歹。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我尊重、喜欢和敬畏在人们身上正发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这一切皆是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它们看起来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是生老病死,但是它们的本质惊心动魄,引人共鸣和令人感动。美国的四星上将科林·鲍威尔在退休之前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安全顾问,因为在指挥“沙漠风暴”行动中的卓越表现而声名赫赫。他在退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九十名随从全部消失了,而他的妻子对他说:洗涤槽堵住了,地板上到处都是水。鲍威尔只得蹲在漏水的洗涤槽边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深有感受地说:我发现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要困难得多!而我们中国人何止是洗涤槽漏水了,我们是根本就还没有洗涤槽,正在为拥有它而一天一天地拼命劳作。我们一家七八个人,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居住在五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这种拥挤岂止是困难?完全是苦难!我们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姑娘换一件衣服都得躲进狭窄的卫生间里去,她的精神世界也得压缩到卫生间去。我们的人物关系纠缠得久远而复杂,把人的情感与心灵撕扯得鲜血淋漓。去年的年底,我去看望一位灵仙,她八十岁了,是一个文盲,眼睛里长满了白翳,脸上已经失去表情,寡言到几乎只说是或者不是,与大家对话的是她腹腔里的鬼魂。一对夫妻寻找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两个月以前遭到绑架至今还没有破案,灵仙找来了他们儿子的鬼魂,他们的儿子说我已经死了,被扔进长江里了,背上绑了石头。鬼魂还告诉他的父母,说绑架是他们的熟人干的,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结了仇,现在又嫉妒他们有钱。还有一位大学教师,他来寻找的是他的母亲。他的父母在反右运动的时候离的婚,那时候他刚满一岁,被送给乡下的奶奶抚养,他的父亲一直仇恨他的母亲,从来不肯告诉他母亲的下落。最近他父亲去世了,临终前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现在是死是活呢?
后来绑架案破案了,那对夫妻的儿子的确被绑上石头沉在长江里,绑架者也的确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熟人。灵仙没有找到大学教师的母亲,大学教师高兴得流下泪来,这说明他的母亲还活在人间。楚人的巫风之久远始于原始社会,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至今不歇。也许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我现在所说的鬼神不是通俗意义上的迷信的实用主义的鬼神,而是某种与我们同在一个生活空间的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另一种物质,好像它们需要原初的智慧去发现。大多数人的崇巫是实用与利己的,但是现在的巫至少充当了心理医生的角色。我在灵仙那儿亲睹的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内心情感,是人们在平常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会对陌生人暴露的。因此我有缘看到生命的挣扎与奋斗是何等的艰难、坎坷与悲烈。我看见了许多人的经历并将继续注视着他们的经历。我想成为每一个人。我想把自己的一辈子变成几辈子。
同时我还希望我通过有意识的修炼,能够逐渐清理掉我后天产生的私心和杂念。我希望我的心是今天的心,此时此刻的心,静如明镜的心。这样,我便可以像天真的孩子和洞穿世事的老人那样返回生命的初始和看见生命的未来,穿过因而直达果,通过果而攀援到因,许多的各种的时间都在我的面前展现,一如所有季节的鲜花一起盛开。
我希望我冲破一切人为的束缚达到自由的境界,我的思想,精神,写作以及作品的形态。
我知道写作的出发点很多。有些作品是为某种使命而写,有些作品是为某种理想而写,有些作品是为未来而写,有些作品是为功利而写,有些作品是为教化而写,有些作品是为载入史册而写,有些作品是为建立学术流派而写,有些作品是为自己而写,等等。别人为什么写,不关我的事。为什么而写都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我清楚的是我不为什么而写。只为一种内心的需要和感动。不为什么也是一种原因和存在。我说过我的所知是极其有限的,在我的视线里清晰的是别人,我总是看不见自己。我不强求我一定要弄懂自己。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我这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作,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写作是否可以顺利地成为我的职业的问题。我也不太了解作家是一个不太平常的职业和人物,可以沽名钓誉和大把赚钱。在后来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懂得了。我有一些懊丧也受到了一些诱惑。懊丧使我远离文人,诱惑使我变得有一些装模作样。谢天谢地,眩晕了一阵子,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又听到了我自己内心的召唤,重获了儿时的感觉。现在,懊丧与诱惑都没有了。我明白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们可以采取各种方式生活。人们可以用自己的任何观点来观照这个世界。我就是我。我的写作是在做一件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我在表达我对生活的感知。而如果我的作品有人阅读并喜欢,那就是为他而写的,那也就是我的荣幸。这种荣幸感使我温暖。使我感到自己的呼有了别人的应。呼应是人生的幸福之一,我为此而深感喜悦。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作品,甚至讨厌我的作品,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永远都只有一部分人喜欢你。尤其像我这么一个人,凡胎俗骨,能够得到选择写作的可能,能够得以安静地写作,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能够拥有一部分读者,这就很是不错了。
我不会对别人和自己的文学作品进行道德上的评判,也不会从社会时尚出发去纠正自己或者别人。既然生命形态各异,文学作品当然也就是各异的。我以为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不是社会集团里最重要的东西,它不是水,不是空气,不是食物,不是政治,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依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调剂。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和作品有多么重要,或者应该多么重要。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世界上的至真至美至善都天然存在,只是被积年的岁月风尘所掩盖。我的写作,为的是拂去那些灰尘,让真善美显露出光芒来。惶恐的是,我的微薄之力不知道是否能够达到我良好的愿望;写作这种劳动,不知是否能够打扫人类生活产生的大量渣滓。我还是在怀疑,当然,怀疑不会妨碍我努力地去做,这就行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汉口
细腰
目录
细腰
青奴
你是一条河
凝眸
预谋杀人
细腰
梅子雨下得柔柔的,愁愁的,淡淡的,悄悄的。暮色四合,天暗地晕,远近一片凄迷。
一个凄迷的大城市里一条凄迷的小街。
一辆乌鱼般的小轿车缓缓游来。
苍白的路灯隔了很久才有一只,寥寥几个行人的身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老长,摇晃不定。司机犯忌,生怕轧了人影子,把车开得蛇一般扭摆。
“小田,怎么啦!”车上的老人说。
司机含了一点儿委屈,说:“郭老,什么怎么啦?到了吗?郭老。”
“再往前一点就可以停车了。”
“吙。”司机如释重负。
老人说:“吙吧,往后我再也用不着车了。”
司机大惊失色:“郭老,您说这话!我可受不了!我可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势利小人,您这么多年——”
“停车。”老人说。
不待司机开门,老人就钻出了车,“咣”地一声,老人火火地反手一挥,关上车门,径直走了。
老人蜇进了一条小巷。
老人胸有成竹地穿行在迷宫般的小巷里。
在一幢墙面斑驳的房子面前,老人停下了。老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古刹似的老房子,伸手摸了摸生在砖缝里的青苔,然后叩响了两扇硕大的杉木门板上的铜环。
许久,门吱呀呀开了一道缝。屋里头关了只月亮似的一地昏黄的光。开门的老头在昏黄的光线里辨认了一下来客,让过身子,又去关那吱呀作响的沉重的门。两壶水在两个房门边的两只煤炉子上同时噬噬冒汽。一时间分不清男女的几个老人停止了各自的动作,混浊的眼珠迟钝地盯着上楼的来客。
楼梯似乎比以前更狭小更黑暗了。扶手冰冷滑腻,像条冻僵的蛇。老人不得不侧起腆着的腹部,一步一步往上爬。楼梯板颤栗了,不胜重负地咯咯呻吟。老人的脚步声回响在大屋里,嘡嘡如空谷钟声。楼下冲天升起一个老妇尖锐的痰声:“谁家的呀?轻点儿!房子要塌了,楼梯要垮了。造孽鬼们的!”
老人不闻不问,依然一步一步往上爬。
蓦然,楼梯上亮了。老人仰起头,看见了她。她立在楼梯口,专注地握着手电筒,一级级明亮着老人脚下的梯板。
老人爬完了楼梯。她抬起了头,安详温和地说:“来了?”
老人说:“来了。”
老人一阵轻松,产生了夜鸟归巢的感觉,以为自己每天都回到的是这里。
他们一前一后进了房间。她虚掩了房门。
冬天取暖的炉子还没有撤掉,炉口上坐了一只热腾腾的瓦罐。幽蓝的火苗围烧着瓦罐底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