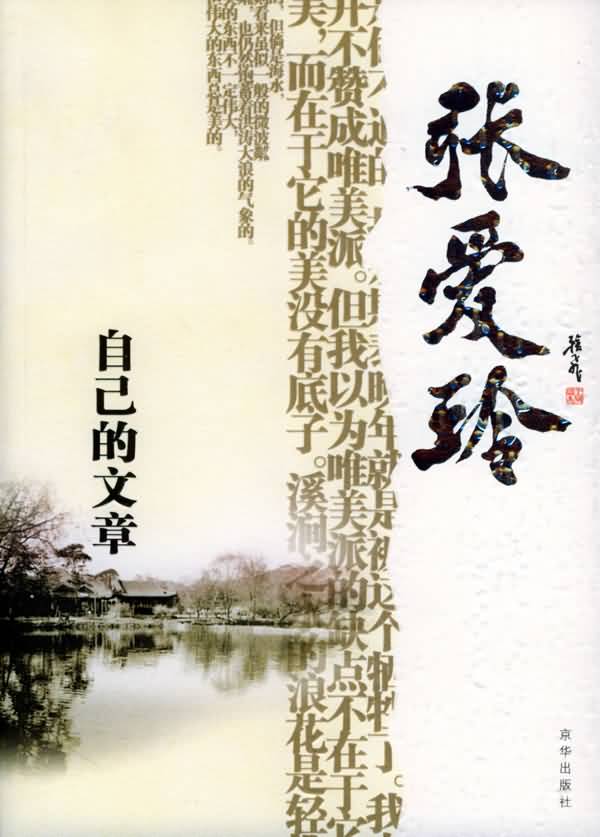池莉文集-第19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我喜欢上了我的这份工作。它清贫,可我喜欢。那我只得接受这份清贫。几年前有个学医时候的女同学来找我,约我和她辞职去开私人医院。医院的专科只设两项:美容和人工流产。她一连三天住在我家说服我。她先前计划的是让我负责美容,美容包括纹眉毛纹眼线割双眼皮隆鼻隆乳激光去痣。后来退让到让我负责人工流产。人工流产仅仅就是把三个月之内的胚胎从子宫里刮出来。利润还是平分。我仍然犹豫不决。她咬牙说:利润四六开!我四你六!
她曾经是我们班最差的学生。实习的时候做一次人流术就把人家子宫刮穿一次。我是副班长。后来我负责手把手与她共同做手术。她每上手术台必害怕厌恶地作呕。
最后我决定不干。我知道我如果干很可能赚大钱但我还是不想干。因为我更喜欢文字工作。
我的这个女同学临走时咬牙切齿踢了我屁股一脚,说:亏你从前还是班长,入党积极分子,现在改革开放,送给你机遇都不敢要。你现在算什么?弄潮儿是我了!
几年下来,女同学成了富婆。上报纸上电视老和市长省长谈项目。最近武汉市一家首饰商店进了一挂珍珠项链作为抬高本店档次的门面。是真正的天然东珠,标价五十五万人民币。人家是不准备卖的。可是我这女同学看了项链后叹口气说:多好的珍珠,应该是无价之宝嘛。小姐,我想买了它,价格可以动一动吗?
柜台内的小姐说:价格不能动。我们经理没打算卖。
女同学说:商品摆在外面岂有不卖之理?价格嘛,我看八十万好了。图个吉利。可以吗?
据说当时慌得经理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
我从电话里听这个故事时开心地大笑。但我并不后悔。我从来没戴过项链,我也不遗憾。人生最难得的其实就是一个喜欢。
看来,我是到了人生的开始固执和清醒的年纪了。
躺在松林下,我半醒半睡。我想到了那位陌生的朋友。平心而论,我是喜欢他的。这人似乎与我同在人生某一阶段。既知趣又关心他人。倘若他是个女人,我可能早已与他形影不离,结伴同游了。可惜他是个男人。男人就麻烦大了。我确实到了一种年纪。对不起。朋友。
黄昏又将来临。我该回宾馆了。临走之前,我在草帽的掩护下偷采了一束鲜花。几枝是白底洒红的药百合,几枝是红底洒黑的卷丹。我要在我石头小屋的窗台上装点一束美丽的花。
12
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
我闹不清究竟存在不存在上帝或者天主。
但是我逢庙便烧香。让我的心语随着那一缕香烟升入无垠的天空。
现有的人类起源学说说服不了我。现在的任何门类的科学解释不了我们信手拈来的最普通的现象。例如:昨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智利复活节岛上的红蟹,它们在交配之后立即想方设法吃饱喝足,然后忍饥挨饿,长途跋涉到东太平洋海岸去产卵。长征途中它们要经过山地丛林,要经过公路村庄,它们在公路上被飞驰的大卡车碾得血肉横飞。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浩浩荡荡红蟹队伍的前赴后继。是谁告诉它们远方有海岸的?又是谁告诉它们在海岸产卵最合
适?电视里的讲解员用惊叹的语气向全世界发问:为什么?
我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蒲公英为什么懂得利用风来广泛传播它的种子。
父母为什么对自己所生的孩子有那么深那么浓那么绝对的爱?
最近的《世界科技译报》上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职典礼的时候,警犬发现了白宫上空一团奇怪的云。从此这团云经久不散,而白宫的许多角落藏有一些非人类所有的类似激光的发射器,电波由白宫直接射向那团云。科学家们认为这是外星人在执行地球任务。
外星人是什么?
一六六三年八月十五日,俄国的一个叫做别洛谢斯卡娅村的教徒们正在教堂做礼拜,忽听天空一声响,他们涌出教堂,看见了天空中一只巨大的圆球。圆球在村庄上空来回移动,将一个湖泊照得通明透亮。
这是我们人类有文字记载的首例报告。后来科学家将这圆球叫做飞碟。
飞碟从此屡屡拜访地球。
一八九二年,我国清朝未年画家吴友如画了一幅“赤焰腾空”图,向后人展示的是当时南京市民蜂拥在朱雀桥头,争睹空中一团巨卵形火球的情景。画家还留有题记: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钟,时金陵城南隅忽见火球一团,自西而东,形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缓,约一炊许,渐远渐灭。
飞碟是什么?
世界成立了专门科研机构,中国成立了UFO研究协
会,然而谁能说清飞碟是什么?
我想要说的只是我的认识。我觉得有一种创造人类及地球上一切的某种智慧和力量。它已经创造好了现有的一切并赋予了程序。它还在创造新的东西。我们在它手里就如蚂蚁在我们手里一样。人的命运是由它定好的。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创造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头上有个巨大的原则。有些天性聪慧的哲学家告诉了我们一句话,说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早有人领悟了自己与自己创造者的关系。
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生有死,相辅相成。都环环相扣,阴阳相对。
一个人出生了,从婴儿到少年与父母紧密相连。成年了,与父母脱离,男女紧密相连。男女合为一体了,又形成了一个圆满,新的生命便又诞生了。
在男女之间,上天(我们姑且用这么一个代名词)安排了一种程序:男女两性情窦开启,相互好奇,神秘,新鲜,探索,接着合为一体。它把合为一体之后的熟悉过程安排为十个月。十个月,男女两性之间得到了充分的了解。这时十月怀胎的新生命便一朝分娩了。新生命出世,男女成为父母。孩子天生与父母血肉相连,这时,男女便又进入一种新的阶段,新的好奇,新的神秘,新的探索之中。
上天好像并没有安排爱情。它只安排了两情相悦。是我们贪图那两情相悦的极乐的一刻天长地久,我们编出了爱情之说。
爱情之说的不合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很多麻烦和痛苦。最常见的就是为了寻求爱情而离婚。
错误的婚姻是有的。我们可以离婚再去组合一个和谐相处的家庭。比如有的男人脾气太坏,他当然需要配一个能包容他脾气的女人。但是如若为了像文学书中描写的所谓爱情而离婚而再婚,你将肯定会发现自己上错了车,每到一站都不是那么回事,目的地与你的完全相反。
我认识一个娇美的四川女人。她为爱情结了五次婚。她向我讲叙她的婚姻史时声泪俱下。我问她:最近这次找到爱情了吗?
她说:没有。
我间:还要找吗?
她说:就为了不辜负天生我这副美貌我这多情善感,我也要一找到底!
最后她离掉了第五任丈夫,在深圳做了暗娼。结果是患了性病,烂掉了一副好皮囊。
我去医院看她,她已经完全变了人形。她说她现在最怀念第二个丈夫。因为第二个丈夫曾在半夜为她掖被子。他要做什么,一个眼神她就懂。她要做什么,一个眼神他就明白了。
紫陌红尘
北京是首都,我是外省人,我老想借出公差的机会到北京旅游一下。所以,领导一说让我出差,我忙问:“哪里哪里?”
我们领导当了我们所十年的领导,党政一肩挑。十年来我在他手下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我们领导深知我心。于是,领导说:“哪里?不是北京!”
群众哗地一笑。我头脸发涨起来。这是在所会议室,各科室干部群众一大堆。当着广大干群,领导竟不给我一点面子,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说:“不是北京我不去。我总也不是北京,你们领导总是北京!”
领导一愣,说:“你这个同志。”
领导对我的不反抗是比较有把握的,意外的是我反抗了。一个人老是满足不了要求,哪能不反抗?群众一瞅这阵势,不散会了,推开椅子过来,围在我和领导身边。我们领导应急能力很强,他伸出一根指头在油漆斑驳的会议桌上一弹又一弹,弹了两下,笑道: “说你这个同志呀,我们每次都是戴帽下的会议通知。让你去,你也不像个所领导嘛— —”
领导在他的拖腔后面紧接上一句:“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时髦。”
我语塞。人们并不认为我漂亮,领导却敢当众肯定我,这不能不使我感激。我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只由舌尖推出一个透明的水泡;我轻轻用力,水泡飞了出去,飘落在会议桌上,破了。群众明显失望。
群众主动说话了。一个说:眉红可能不太像党的领导,至于所长,我看还是蛮像的。”
一个说:“眉红年轻什么?三十郎当了。胡锦涛四十多岁,都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这人说了又心虚,连忙问旁边的人:“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常委?”
旁人说:“怎么不是?当然是!电视里看,一头乌发,多年轻。我们国家上头改革开放搞得好,下头搞得不好。”
近些年来,我们所干群关系变化很大,群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便话中带刺,领导一般也装作听不出来。但我们领导也积累了经验:任你说什么我就是不放权。群众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我们领导对群众微笑,将话题固定在“北京”上。
领导说:“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吧。北京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嘛。长城,砖头砌的;故宫,砖头砌的:亚运村,还是砖头砌的。大街,水泥铺的;街上的人,人肉做的。五官加四肢,吃喝拉撒;和全国人民没什么两样。你们看我们这黄鹤楼。我住在阅马场,抬脚就上了黄鹤楼,但我就是没去过。大几块钱一张门票,说句老百姓的话——还不如喝几瓶小黄。”(小瓶包装的黄鹤楼酒)
群众也与领导随便起来。说:“头,你这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任你把北京说得寡淡寡淡,北京人家还是首都,身份在那儿摆着,没去玩过的总是想去好好玩玩。”
大家互相挤眉弄眼。
有人就更放肆了。说:“比如现在街上的那些鸡(妓),都讲她们肮脏下流,有艾滋病,可没有见识过的人总是心向往之。”
领导顿时寒了脸,在桌上顿了顿茶杯。说:“太离谱了吧?大不像话了吧?”
群众便讪皮讪脸吊儿郎当地离开了会议室。
我呆在原地没动。我在一只旧式的高背办公椅上搁着下巴。望着椭圆形会议桌上零散的报纸,心里很难平静。报纸上三天两头揭露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腐败现象。在我这种普通工作人员眼里,揭露无异于炫耀。它激起了我的许多奢望。其实我从小是个好孩子好学生,红旗下生,红旗下长,曾把雷锋作为人生的榜样。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优秀的,是社会的动力,国家的栋梁,是单位的拔尖人物。可是现在却为了公款去北京旅游和领导抬杠。
我透过三月的新绿,懊恼地死盯着窗外乌烟瘴气的春天,想: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呢?
我如果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就会不断地被派往农村出苦差。一入夏就下乡收购棉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