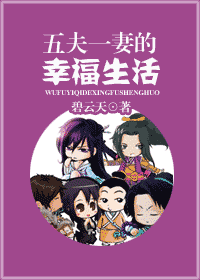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部的精彩故事:十年-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选题计划和闲聊启蒙的。
张晓莉是生活周刊最听话的女孩,规定9点上班,她准到,坐在那里读读英语也好,虽然别人都没那么守规矩,但她心里从来没有不平衡。她认真采访写稿,怯生生地望着主编,极力要弄清他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她也成了一家大报的首席记者,文字也越来越老辣。
邢海洋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兴趣多变,也使他在多个领域中游走自如,思维总有出人意料之处。关于他的恋爱故事你可以听到不下10个本子,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搞不清,但不重要,谈论时他的那份疑似真实的失落让你感动,他是一个想过出花样生活的人。其实他很重感情,曾经为了写一篇自己的感情故事,写了一夜,哭了一夜。
因为字数所限,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刚写了几个人就不得不收笔了,好在我知道有同事生动地写了他们……邹剑宇、王星、高昱、王珲、李梦苏、刘天时、卞智洪、皮昊、邹俊武、商圆还有技术编辑程昆,可爱的行政秘书高媛都是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分子。
人去人又归
1998年4月,在为生活周刊工作了近三年后,我离开了。那滋味不好受。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养育后代,人生不为自己,只想让父母晚年幸福。我努力地工作,希望有能力带着他们每年出游一次,希望年底时能奉上自己的孝敬。可是我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周刊经费严重紧张,收入水平一直上不去。1998年栏目调整,我的收入将剩下原有的一半,尽管我还担负杂志后半部分的制作、行政管理等其他一切没有人承担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离开。
新单位正在筹备引进一本优秀的科学读物,后来我做了这本《Newton…科学世界》的执行主编。直到这时,我才发现生活周刊难以割舍。我刚到新单位时,曾经有同事反感我,因为我言必称〃生活周刊〃,据说,做试刊版式那天,我说了不下十次〃生活周刊如何如何〃,想一想,那些希望有自己个性创意的同事是该烦我。由于运作不顺,我们那里也会危机频发,一旦遇到困难,我总是先向朱伟和老潘求助,一会儿来扫描一些图片,一会儿请教一点问题,他们也总是乐于助我。
2002年秋冬时节,由于种种原因我离开《Newton…科学世界》,像回娘家一样回到生活周刊。此时生活周刊兵强马壮,安贞大厦的办公环境优雅,倒真像小资文人聚集之地。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看着满屋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里真是喜欢,我自己也幸得美丽可爱的助手回晓君,我切实感到生活周刊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过去生活周刊一个月出两期杂志的经费只有8万元,要支付稿费、工资等管理成本,基本没有采访经费,偶然的外出采访大都是受人之邀。现在不同了,一个月的成本就要百万元,记者已经跨出国门采访,新闻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受到尊重。我明白,生活周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也难免再遭遇坎坷,但这飞跃还将继续着。
我祝福生活周刊一路向前。
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1)
舒可文 1995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文化编辑。时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哲学教师,副教授。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1994年有一个非常热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给我刚出生不久的小闺女洗好几次澡,那时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闲着没事的时候,不紧不慢地写了本跟艺术有关的小册子,主要是因为本来没什么别的事,有人愿意出版它,正好给家里添点进项,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闻。
奇闻之一就来自吕祥,他一直是我们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来聊天,那个夏天他时不时地说到三联书店筹办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全然与我无关。后来天气渐渐凉下来,这个话题的热度也降了下来,我记得似乎是因为投资之类的事情。到了转过年1995年,天气又热起来的时候,朱伟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在家当全职家庭妇女已经干了一年多了,新学期开始后就得回学校接着教书去。他说,那多没劲,还不如到《三联生活周刊》来。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学校开学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几次选题会上,我听着一群小姑娘、小小子兴致极高地汇报着他们四处搜集来的信息,有好莱坞某明星的什么事,有某公司的什么事,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明明是别人的事,却如数家珍,一本正经地把它们拉到和自己这么近的距离,显得非常不靠谱,总之;〃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美丽〃……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题目。接着,朱伟就要问:〃角度?〃这又让我纳了半天闷儿:有啥说啥,有根有据,还不行?不行,因为题目多数来自道听途说,大家都在说的事,你有什么理由再说它?全凭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说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头几年是个最让大家费心的词,后来改成了比较平易的〃你怎么做〃。
虽然来之前朱伟问过我,看不看一些时髦的书,我说看,来了之后我立刻感觉到他问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来以为不就找题目吗?不就写字吗?后来发觉这完全是一份新活计,根本不是我习惯的那种题目和那样的文字,好在这时候生活周刊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运行,我还有时间把旧习惯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很快,1996年一开始,生活周刊就进入了双周的运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样,揪着这辆快车,买了不少我原来根本不看的书,壮着胆子写着那些自个还没想清楚的事,感觉是中年转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反映时代进程。一个时代当然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构成,我一开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对于我来说首要的事情就是放弃原来习惯了的注意点,不能从书本上寻找说话的题目,必须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里找到可说的题目,哪怕是过了没多久的事,在朱伟那儿也被叫做〃腌兔子〃。
城市文化中,艺术被拉入我们的选题有点偶然。虽然艺术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有时候是批判者,有时候是时尚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制造者,有时候是一种价值的消解者。但那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刚从非常边缘的状态渐渐进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赚钱有各种各样的花招一样,艺术家也有各种花招制造不同的趣味,他们的着数属于艺术,反映的却是这个时代、特定文化的气质。以前在写美学题目的时候,也要拿艺术家来分析,但那只是从作品或文字记载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据都是过去时态的。而这种进行时态的艺术现象充满了魅力,大有可解释的空间,可我完全不会采访。
这时候,我的朋友邱志杰和王铭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最开始的采访是拿邱志杰练手,对邱志杰的采访让我第一次拿艺术的现在进行时态做文章,这显然符合生活周刊对新鲜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把采访归置在一个〃角度〃下,基本原样地写下来,因为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铭铭帮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给了我们家很多人类学的书,而且不论多么细枝末节的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有时候他也讲一些他在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候的趣闻,我从中获益不少。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把艺术家当成一个族群看待,他说当然。此后我试着这么做,即使是做艺术评论,也完全改为对作品阅读、对创作者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阅读,然后才有阅读者的叙事。
艺术活动在那时候的媒体上基本还是一种时尚题目,或文化新闻事件,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一种很混杂的杂烩,不一定符合传媒惯例,但朱伟还是都把它放在了〃艺术〃这个专栏里,并一直让它持续着。很快,生活周刊成了反映艺术动态的一个公共平台,也让我给自己定的题目有了长期做下去的机会。北京被〃非典〃围困的时候,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把这些东西整理成《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出版,算是我对这个栏目的一个交代。
2001年生活周刊变成了真正的周刊,那时候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城市中最活跃的产业,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开始成为50年来普通中国人第一项大的不动产。改为周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变中国》。这本来是艺术批评家黄专策划的一个展览的题目,黄专、上河美术馆的陈家刚,拉上我,讨论了好长时间,越讨论规模越大,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张欣。我已经开始查找几十年来和住房有关的政府文件、媒体报道,甚至小说里写到的居住状态,最终因为展览线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没有做成展览,却成了我们杂志现成的题目。
舒可文:中年转行第二春(2)
〃城市化进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一个到处见到的字眼,城市也进入了生活周刊的选题会,高昱最先在生活周刊开始以城市为题目做文章,他是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小伙,他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生存历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个城市在快速变化中的种种状况,这在编辑部里也成一时佳话。上海苏州河改造的时候,因为牵涉到很多艺术家工作室的搬迁,朱伟就让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给了我一些人的电话,说他们都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人,也许能给我一些帮助。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真正做采访调查的机会,虽然在家里也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沿着苏州河从东到西走下来,几乎所有的东西和采访到的所有人说的事,都是绝对具体,绝对鲜活的,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苏州河的历史和今天稍做对比,就发现,城市是一个太有意思的东西了,尤其是在它处于巨变之中,所有事先的判断都会在复杂的具体问题中变得可笑,比如对旧建筑的拆与保护这种最简单的争论,在种种的合理欲望中纠缠在一起,真不是谁高尚谁贪心能分辨得清的。那一次采访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真正的田野调查和书房做功课完全是不同的天地。后来,生活周刊又陆续以这种方式做了一些城市的话题,有顺理成章的,也有败笔。其实顺着这些题目做下去,每一个都是很大的诱惑,刚觉得有意思就不能接着做了,因为,周末就得发稿。这种节奏虽然我已经适应,但是至今仍觉不爽。
回头这么一看,快10年的光景过去了,不仅我习惯了的方法论被改造了,世界观也被改造了,从原教旨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这不仅得益于采访,也还因为我整天就和一帮比我小十几二十岁的人混在一起,转行的同时,也被他们调整着与时代进程的焦距。胡泳给我们带进了互联网文化,那时候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在全中国掀起了这个话题热,完全是由于对他这个人的熟悉,我才会认真对待这种文化,不然我会把互联网仅仅看成是一种工具。吴晓东在做《地产十年》的准备时,我仔细听看他做的准备,要采访的人和事,对比我在做《居住改变中国》时所关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虽然一个是说地产一个是说居住,但其中有很多相关的东西,他注意到的事是我完全没注意到的。小于、钟和晏爱跟我聊天说电影,即使是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她们看到的东西总是和我不一样,她们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