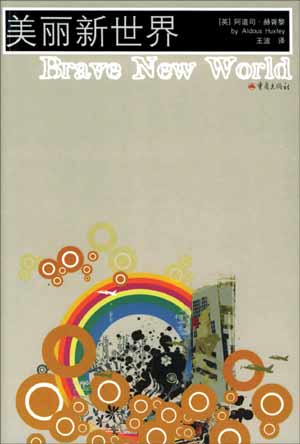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莫奈-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决不让巴黎的沙龙艺术强加于我。我生来就是一个农民,到死也是个农民。”
而莫奈,一个从勒·阿弗尔到巴黎艺术殿堂来求拜的朝圣者,一个酷爱艺术的年轻人,还未曾领略这画坛的风风雨雨。他刚刚抵达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之都,以一个乡下孩子惊奇而惶『惑』的眼光打量着陌生的四周:繁忙而热闹的大街;表情漠然、行『色』匆匆的路人;高傲无情的摩天大楼;琳琅满目、干净整洁的商店……他试图做出一点儿礼貌的殷勤,得到的仅是令人沮丧的白眼。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骄傲地漠视着脚下膜拜的人们。今天,它看见了莫奈那童真未泯、热烈而渴求的眼光,它仿佛笑了,认为自己又增添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不料,15年后,这位当初身量未足的乡下孩子却毅然推翻法国画坛上的冰冷的“艾菲尔铁塔”,用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培养出一丛新的艺术之花。
莫奈很幸运,他一开始正式作画就受到法国著名风景画家布丹的指导,他的航船一直就高扬着个『性』的风帆,在云天碧海中遨游,努力追赶画坛的前锋。
1895年5月,莫奈在沙龙展览会中流连忘返。他专心地研究所有著名画家的作品。科罗、杜米依、特罗容等人的风景画使他赞叹不已,兴奋得几乎发狂。他如饥似渴,大口大口地吞饮着大师作品中涌出的艺术清泉。他独自去拜访了好几个画家,特罗容对他作了热心的指导:
“我看了你带来的画,有『色』彩,这很好,在一般效果上也正确。但你要作一番努力,学习作画,这是一件细致的事,但你干得太随便,功夫在身,它是丢不掉的。如果你肯听我的劝告,并且认真对待艺术,你应该进一个画室学习素描。这是目前几乎人人都缺乏的锻炼。对这一道理,人们总是了解得不够深刻。同时不可轻视油画,坚持到乡村里去画速写,并往卢浮宫临摹大师们的作品,经常的把画带给我看看,凭着你的勇气,你将获得成功。”
特罗容的批评与鼓励让莫奈大受启发,但他没有接受特罗容让他进库退尔画室学画的主张。因为他厌恶画室中那股“学院风”,并深深地感到脱离生活的任何艺术活动都是没有生气的、僵化的、凝固的。他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没有生命力的“艺术”,他认为,这种艺术将扼杀他的独创精神。巴黎实在让他大开眼界。血气方刚的莫奈不会为进美术学校上正规的课,而放弃自由自在的户外活动,他就像一只习惯在高空野林中翱翔的飞鸟,无法忍受樊笼的约束。他和一些艺术界的学子们跻身于烈士啤酒店的集会,那里有对艺术问题的火热的争论。偶像在片刻之间被创造或被废弃,没有任何一种权威可以让人噤若寒蝉。美术学院愈是主张维护的神圣传统,在烈士啤酒店里便愈遭到怀疑。人们用激情代替逻辑,用热情代替了理解,充满着盎然生机和勇于探索的坚强意志。同时在啤酒桌的周围产生了无数的友谊。巴黎吸引了一大批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年轻的天才,他们在这里找到努力的方向和令人兴奋的同志关系。他们彼此受到鼓励、交上朋友,让自己在艺术上『摸』索,埋下光荣的种子。
由于莫奈拒绝进美术学校,父亲一怒之下断绝了给他的津贴。他只好靠自己的储蓄维持生活。在烈士啤酒店里有时可以见到库尔贝。莫奈欣赏他的绘画风格和用笔技巧,但对库尔贝在作品中所赋予的政治、道德的意义,却从不加以考虑。也许是莫奈年岁尚小,也许是学院派那一成不变僵硬的画风令人生厌,他所知道的便是直接由眼所见、由心所感的一切。他以天真的态度来信任一切。这就注定他一生都是一个以谦虚的心情献身于自然与艺术的单纯的人。在这段时期,他被一些专画风景的年轻人所包围,在偶尔去的画室结交了另外一些青年美术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莫奈取得了一些进步。他的鉴赏力、辨别力也随之有所提高。
1860年初,一个出自私人收藏而没有美术院参预其事的大规模的现代画展在意大利路开幕了,这个画展跟前一年官方画展形成令人惊讶的对比。这些画洋溢着生命的力量和灿烂、强烈的『色』彩,使莫奈大受感动。这些作品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新天地。他很高兴地说,这个新画展证明“我们并不如人家所说的那么腐败”。他被德拉克洛瓦的18幅油画、巴比松派画家的风景画、库尔贝和科罗的作品,还有米勒在去年沙龙落选的那幅《樵夫与死神》深深地吸引住了。站在这些作品面前,他禁不住涌出了泪水。用笔的灵活,『色』彩的调和与创造力,使莫奈获得了“一种新的战栗”。
不久,莫奈进斯维塞画院学习,这是一个从前当过模特儿的人开设的画室。是在奥菲尔码头的一所旧而肮脏的房子。画家只要出一些钱就可以在那里画活的模特儿,既不考试又无课程。不少风景画家都去研究人体解剖学。在写给布丹的信中,莫奈谈到自己工作的一些详情:“……我很用功画人体,这是很有益的事。这里的风景画家都开始发现画人的好处。”库尔贝、马奈、毕沙罗都曾先后到那里画画,莫奈很快地便跟他们相识。
跟毕沙罗一起作画不久,莫奈要去服兵役了。这对他来说并不害怕,他渴望受到战火的锤炼,渴望在异乡采撷创作的灵感。而他的父母则另有打算,他们没有原谅莫奈从家里逃走的过错。他们希望莫奈只要肯认罪,他们就可以花钱买一名替身交差,趁此机会把他拉回家,否则就要当七年的兵。但是莫奈的态度很坚决。他后来解释到:
“七年兵役是吓倒许多人的,可是却很引起我的兴趣。我有朋友在非洲军团里,他很喜欢部队生活,曾经把他的狂热传染给我,并使我对他那种冒险的爱好产生同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烈日下无尽的骑兵行列、攻城掠地,火『药』的爆炸声、马刀的砍杀,在帐篷里的沙漠之夜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抽中了签。通过我个人的坚持,我便被派遣到非洲军团里去服役。我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很美好的两年。我不断地见到一些新事物;在有空的时候,我很想把我所见的画下来。你不能想象我的知识已增加到什么程度,以及我从那里得到的见闻。在那里对光与『色』的印象开头我不能十分理解,直到后来才能分类;它们里面包含着我未来的研究的胚胎。”正是这种对艺术的执着,对生命的热爱,莫奈渴望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搏击,去吸取创作的灵感和力量。
1862年,莫奈在阿尔及利亚患伤寒病,被送回家中休养,他在这六个月的疗养期间用加倍的精力作画。父亲看到他这样固执坚持,最后只得承认没有一种意志能够压制这个青年艺术家。由于医生曾经警告说,他的儿子要是回到非洲去一定会发生不幸的结果。在莫奈休假期满之时,父母把他从部队里赎了出来,回到了勒·阿弗尔。
莫奈又有机会在海滩上自由作画了。自己一个人或者和布丹一起,这时恰巧琼坎也在勒·阿弗尔画画。这又是一位在莫奈的艺术道路上产生影响的艺术家。琼坎40多岁,高大结实、亲切而羞怯。他和布丹一样重视描绘大自然的光『色』变化和环境气氛,尤其爱画海景风光。他只有在画画或者谈论艺术时才感到舒服。对他来说,没有比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这一题材更引起他兴趣的了。他用那敏捷的双手,加以敏锐的见解,把它们转变成简劲的线条和明快的『色』点,而不反复涂改添加。琼坎、莫奈和布丹之间很快地便结成很好的友谊。夏季,他们三人一起去描绘大自然。莫奈后来回忆道,琼坎“要看我的速写,要我跟他一起画画,对我解释他为什么用他的方法,因此把我曾经从布丹那里得到的教导完备起来。从那时起,他成为我真正的老师;他完成我眼睛观察事物的教育”。
同年11月,莫奈又回到了巴黎。父亲警告他:“你要好生懂得,这次你要老实地学画。我希望你能够跟一个著名的画家学习。要是你再闹独立,我就立刻停止你的津贴,……”为了不使父亲生气,莫奈同意了这个安排,他进了格莱尔画室。
格莱尔是顽强的学院派的追随者。他总是忘不了自己年轻时求学的困苦情形,开画室以来,对学生非常宽大。他很少拿起笔来修改学生的作品,对于题材也没有偏爱,学生们爱画什么就画什么,尽量留给他们自由发展个人志愿的广阔天地,他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格莱尔每星期两次到画室里来,慢慢地在里面兜圈子,在每一个画板或画架前面停几分钟。他严格恪守学院派教规,要求学生们作画时应该以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为标准。有时他也会暴跳如雷,那只是在他看到学生们画画不重素描而过分偏重『色』彩的时候。他时常担心他的学生们会画出“恶魔般的颜『色』”。
画室有三、四十个美术学生,每天早上8点到12点都在那里对着模特儿画素描或油画。莫奈第一星期还是老老实实,他很专心地画了一张『裸』体模特的习作。第二个星期,格莱尔似乎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天赋,他在莫奈的身后,像生了根似的稳稳地坐下来,聚精会神地看他画画。然后他转过身来,把沉重的头靠在一边,用满意的口气说:“不差,真不差!东西虽然画出来了,但是对模特的特征画得太多了。在你面前是一个矮胖的人,你就把他画成矮胖;他的脚很大,你也画得一模一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很丑陋的。年轻人,我要你记住,当一个画家画一个人时,应该时常想到古代希腊、罗马的东西,把这个丑陋的人用你的想象力让他成为一个健美的男人体。我的朋友,把自然作为研究的一个因素是对的,但是它提供不出什么好处。你要知道,风格高于一切”。对莫奈来说,这个劝告使他震惊。他从布丹和琼坎那儿学得要忠实地记录所见事物。于是,他和他的老师之间构起了一道防线。莫奈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使自己的作品引起格莱尔不愉快的学生,还有一个巴黎人奥古斯特·雷诺阿。他似乎也不能够恰当地接受学院派的精神作画。一次,格莱尔瞧了一眼他的模特儿素描,就冷冷地说:“毫无疑问地,你是为了自寻乐趣而拿了颜『色』随便涂涂?”
雷诺阿答道:“什么?当然啦!要是画画不使我感到乐趣,请你相信我是绝不会去画的!”
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答复是从这个学生的心底里发出的。他和莫奈同病相怜,很快成为情投意合的兄弟。当弗列德里·巴齐依和英国人阿弗列德·西斯莱参加进来时,他们便形成了一个四“好友”集团。他们的作业愈来愈引起格莱尔的厌恶。同时他们也与画室的多数学生疏远了。那些学生大都很粗俗,开讨厌的玩笑,唱黄『色』歌曲,举行下流的化装舞会。他们不谈艺术,没有一句高尚的话,毫无崇高的理想和感情。莫奈就向朋友们说:“咱们走吧,这里不利于健康,这儿不说真话。”由于害怕父亲知道要生气,他仍按时到画室去,对着模特儿草草画一两幅速写以便应付老师的检查。
可是雷诺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