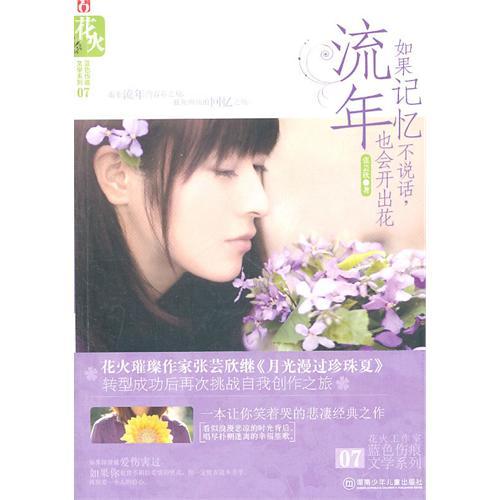开出现象学之维-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德哲学,所以导致这样的误读。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就是对“理性”概念的误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但人们有一种误解,对理性的误解。西方的“理性”,英文就是reason,德文是 Vernunft。对这个词的误解,从翻译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出,reason这个词翻译成“理性”,本来是一种音译,我们从日本人那里接受过来的。因为中国传统哲学里面基本上没有“理性”这个词。中国传统哲学里面有“性理”,有“性”,有“理”,“理”和㈠性”都有,但是很少把“理”、“性”这样两个字连用。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是从音译——。reason,把它翻译成“理性”。当然里面包含有一定意译的成分,就是把理和性都包括进来了,但是它的意思和理、性不一样,它的意思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所讲的理和性。中国偶尔也会看到把它连用为“理性”的,但是那个意思据我理解还是分开的,就是理和性,当然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但它意思并不是“理性”,而是理和性的意思。最近,田文军老师说其实也有“理性”当作一个专有名词来用的。他说我可以找给你看,他还没有给我找出来。但是我觉得即算找出来了,我也可以这样理解它。就是说像朱熹的性理,《性理大全》,性里面的理,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理性你很难说它是理里面的性,你很难这样的理解。
Reason这个词被翻译过来的最初的那个意思还是把它当作一种能力,当作人的一种属性、人的一种能力来理解的。人的理性嘛,“理性之光”嘛,每个人都具有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包括逻辑推理,包括摆脱感性的束缚、超越性这样一些意思在里面,都属于理性的功能。理性本身是一种功能。但中国人理解的理和性基本上不是一种功能,而是一种实体,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中国的“理”字,它来自于玉石的纹路,玉石里面的纹理,它本来就是“治玉”的意思嘛,《说文解字》里面讲:“理,治玉也,从玉,里声”。它一个“王”字旁嘛,“王”字旁就是玉。“里”表示它的声音,“理”本来是这样一个字源。那么它跟西方这个理性有相重合的部分,我们中国的“理”和西方的“理性”有重合的部分。哪些方面重合呢?就是像王国维所讲的,它有一种“分析作用”。就是可以分析,把对象分析出来,它的这种条理,它的系统,我们可以把它分析出来。所以,所谓的“理”它本身就是条理、规律、规则,有这样一方面的意思。你要讲理啊,你要讲规则啊,你要讲来龙去脉嘛,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你没有原则嘛,你还讲不讲理了,等等。它是一种基本原则、基本规律的这样一种意思。但是这个重合呢就到此为止了。西方的这个“理”、理性,也有这个意思,也有规律的这个意思,这就是它们重合的地方,其他的方面还有不能重合的地方。
我们曾经讲过,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就是黑格尔。他的理性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逻各斯”,一个是“努斯”,根据我的分析里面有这么两个方面。那么 “逻各斯”的方面是指语言和表达。那么“努斯”呢,它是灵魂,在希腊语里面它是灵魂嘛,它是指一种能动的超越性。灵魂的特点就是能动的超越,它自动,灵魂可以不受肉体的束缚,而且它可以超越肉体,所以它是一种超越性。而这两种意思都是中国的“理”字所不具备的。西方理性的这两个意思,一个是“逻各斯”,一个是“努斯”,这两个意思都是不能够在中国的“理”里面发现的。中国的“理”仅仅是说自然界的规律、法则。但是这个法则与语言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百物它的生长发育都有它的规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春夏秋冬都有它的规律。但是,天何言哉,天不说话。所以中国的这个天理,包括天道一一理和道在宋明理学里面已经打通了——天理、天道在这个中国哲学里面跟语言是没有关系的,跟“逻各斯”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道”字,我们用来翻译西方的“逻各斯”,但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用“道”来翻译“逻各斯”当然很好,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道”,实际上也有道说,说道的意思,但在哲学上没有哪个这样理解。在日常中你可以这样说,在古文里面、日常谈话里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哲学文章里面,没有人把这个“道”、天道理解为说道。天是不说话的,天怎么会“道”呢?天道怎么会“道说”呢?天道是不会道说的,它不会跟你说话,只会做给你看。至于这个“努斯”——灵魂,跟中国人所理解的“心性”也不相同。像苟子就讲到这个心它可以选择,孟子也讲到心是可以选择的。但只是选择而已。而灵魂——“努斯”,在西方它是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自我超越性。它是一种超越性,它体现为人的自由意志,而且这种自由意志可以为自己制定行动的法则。这是中国的心性所不具备的,它不具有这种超越的、自己制定行动法则的意思。这一点王国维在他的《释理》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搞混了。他在《释理》里面讲:“言语者,乃理性第一之产物。”就是说言语啊,说话是理性的第一个产物,这个当然不错。他说:“此希腊及意大利语中所以以一语表理性及言语者也。”就是希腊语和意大利语中用一个词来表示理性和言语。他没有说什么词,我理解就是“逻各斯”。。。逻各斯,’既是说话,又是理性,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理性。这是王国维在这里讲的一个西方的事实。但是紧接着他就说:“此人类特别之知力,通古今东西皆谓之日t理性,。”这就有问题了。他说这个是人类特别的一种认识能力,古今东西,古今中外都把它称之为“理性”,都是一样的。这问题就大了,因为所谓的这个言语和理性用一个词来表达,这只是西方的特点,中国没有。中国的“理”和语言毫不相干,甚至于是完全对立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二程”中,程颐有一句话,他说“凡实理得之于心自别。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就是说凡是实理,凡是真正的理啊,“得之于心自别”,就是你在心里面得到了,你自然会分别出来。“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如果说耳闻的和口里说出来的,那么在心里面其实没有见到。这个理你如果能够说得出来,那你就没有体会到,你如果体会到了,你是说不出来的。这就是中国人讲的理、天理、实理。实理是得之于心的,得之于心你自己就可以分别,但是你凡是耳闻Vl道的,那就不是实理了。这是程颐,程颢那里也有,他说的更明确,他说: “吾学虽有所授受,,,我的学问虽然有所授受,有人教授,有人教给我,我是接受别人的教导;但是,一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我的学问是老师教给我的,但是“天理”两个字是我自己体贴出来的,不是教给我的,不是我听来的,是我自己用心体贴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天理决不是通过言语和逻辑能够说得出来、推论得出来的,而是凭直觉体悟到的,中国的天理是直觉体悟到的。
王国维的这样一个混淆,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都做了这样的混淆,比如说:胡汉民。胡汉民就认为:宋儒把名教归人了理性。但他这个理性是现代的理性,不是中国古代的理和性,他把它们混为一谈。贺麟把康德哲学称之为“即心即理亦心学亦理学的批导哲学”,把康德哲学跟中国的心和理、心学和理学融合为一体,融为一炉。所以陈康很看不起这些人,就是说这些人老是把不1司的东西煮成一锅,搞得分不清楚了,实际上是应该分出来的。包括对黑格尔的理性的技巧、理性的狡计的观点,贺麟也把它跟中国的天理、道学、宋明理学混淆起来。还有冯友兰,把西方的逻辑理性和程朱理学糅合为一体,提出了“新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实际上就是把西方的理性、逻辑和程朱理学融为一体,但是程朱理学和逻辑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跟逻辑、语言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当然朱熹要论证的话,他还是要讲点逻辑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儒佛之辩啊,理学跟心学辩论啊。在所谓“鹅湖之会”上,朱熹和陆象山他们辩论,朱熹当然辩不赢啊,辩不赢他也没有输,因为他那个东西不是能够说得出来的,所以没辩赢也没关系。这是我们非常推崇的“鹅湖之辩”,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件,就是说两大派,理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在那里辩论,辩输了就承认输了。就是我辩不过你,辩不过你也没关系嘛,我心中自有天理在嘛,那还是我体会到的。我口头上辩不过你,这并不丢人,你口头上辩赢了又怎么样呢?无非是说你能言善辩嘛。所以说这样一种理性它跟逻辑实际上没什么关系,逻辑上你说得头头是道,不一定是对的,我逻辑上说不过你,也不一定是错的,逻辑不是一个评价的标准,至少不是唯一的标准,不是最高的标准。还有像这个金岳霖,把逻辑实证主义和中国的“道”、“道家”融会为“新道学”,有人指出来:所有这些新什么学里面,都“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什么理论困难呢?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逻辑的本体如何过渡到现实的世界?”中国人历来重视的是现实的世界,不重视逻辑。所以你讲了那么多逻辑,西方来的逻辑,你如何能过渡到现实的世界呢?过渡不过来,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基因,中国哲学里面没有这个基因,没有西方的哲学一开始就建立在逻辑理性之上的这样一个基因。中国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非逻辑的东西之上的,你怎么能从逻辑过渡来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所有这些人虽然想要吸收西方理性中的“逻各斯”精神,但是没有吸收“努斯”精神,“努斯”精神是更深层次的。外在的“逻各斯”精神,即逻辑对语言的执著,这个是通过比较表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背后的那种“努斯”精神,那种自由精神,那种超越精神,他们都没有吸收到。而在西方,这两者缺了一个,它的形而上学就会垮台。西方的形而上学都是由这两方面双方共同建立起来的。就中国传统的背景来说,中国传统哲学里面,包括理学、道学,也包括人们称之为玄学的中国哲学、魏晋玄学,从魏晋玄学以来的很多玄学家,他们哲学里面所缺乏的就是这两大因素,一个是“逻各斯”的因素,一个是“努斯”的因素,缺乏这两个成分。所以你把西方的逻各斯拿来,它就和中国哲学格格不入,跟中国传统哲学格格不入,处在相隔之中。我曾经下过一个判断,就是说宋明理学和整个儒家以及道家哲学绝对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直观类推的。孔子讲“能近取譬”嘛,类比、打比方,举最近的例子打比方,这是中国讲哲学的人要掌握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只要你掌握这个方法你就可以讲哲学了。所以中国哲学都是通过打比方建立起来的。当然也有建立一些概念的,进行概念上的建构的,但这种概念的建构,它的黏合剂还是打比方,还是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