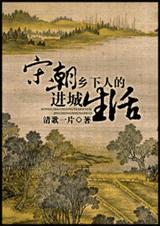地下城生长日志-第1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或许他们真的只想要一块容身之所。”开始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软化的意见,“他们一路进军却一人未杀。”
“那可能只是迷惑人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和我们全面开战。就这么放任他们,毫无疑问是自取灭亡的愚行!”
“不立刻进攻,也不意味着放任他们。我们一样需要时间来修复能量源头,或许在这件事上,我们已经失策了很久。”
“我不认为那是失策,在那个时代……”
“请允许我从经济的角度重新阐述……”
“先生们,以现在民众的士气来看……”
在百年的稳定之后,帝国的高层都学富五车,博古通今,能为自身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提出最切中利害的意见。军方依然握着大部分话语权,但财政与舆情正拥有越来越多的分量。惊怒最终平息,多方权衡之下,得出的结果几乎不变,依然和元首演讲时制定好的方针一样。
在塔斯马林州的边境线上,高墙竖立了起来。
装甲车被布置在周围,深深的壕沟与铁钉相结合,他们用人造的地下河流预防地下城的蔓延。钢筋水泥制造的高墙将塔斯马林州的边境围上,铁丝网缠绕得密密实实,每隔百米就有瞭望塔,高墙附近还有着数十米寸草不生的开放地带。每到夜晚,探照灯虎视眈眈地扫过这片空地,牵着猎犬的哨兵在边防周围来回巡视,一只老鼠也别想爬过去。
元首口中的“夜幕”最终被制造出来,帝国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异种袭击,不过考虑到这东西防不住天空,也很难在钢铁傀儡与魔导炸弹的双重冲击下坚持多久,更大的作用恐怕是防止帝国公民偷渡过去。
防线初步制造完成的时候,第一波新移民已经在塔斯马林州安顿下来,数量与质量都挺让塔砂满意,已经足以构成地下城在地上的基石。她对自身实力很有自知之明,匠矮人的魔导科技已经进入了瓶颈状态,地下城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用于消化新居民,“解放全世界”这种口号,还是别去妄想为好。
何况,高墙可不能阻断一切。
高射炮依然属于耗能巨大的罕见武器,广告飞艇固然目标太大,足够小心的无人机与飞鸟却能飞跃防线。宣传机器与化兽者德鲁伊在两边穿行,带去东南方的声音,带回帝国的消息。一大批来不及撤回的间谍留在了帝国,开始了小心谨慎的地下谍报工作,他们能在那里庇护逃不过来的异类,建立起敌营中的据点。
种子已经埋入帝国的土地中,有足够的阳光雨露让它们发芽。
帝国没法打下所有的无人机与飞鸟,除了将“收听敌机”与“收容敌鸟”判为非法之外,他们也没有坐以待毙。学院派机械师很快行动起来,以广播无人机为模板,制造出了广播机械鸟——这事儿仔细想想还挺好玩,地下城根据机械鸟发明出无人机,帝国又根据无人机改进了机械鸟,双方的技术通过战争进行了交换与升级。
那些机械鸟带着帝国方的通稿飞入塔斯马林州内部,痛斥地下城政权的黑暗,呼吁被欺骗的民众站起来。他们声称血统鉴定完全是分裂人民的可耻谎言,倘若偷渡客们幡然醒悟,勇敢回头,帝国方绝不会追究他们被欺骗后犯下的投敌之罪。同时,还有着向异种劝降的内容。
龙骑兵巡逻队每天处理着天空中的垃圾邮件,就算有些漏网之鱼,塔砂也不会向对面那样如临大敌。机械鸟公放的内容,水准远不如给元首的演讲,涉及异族的部分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怜悯还有对异族生活荒谬的揣测,龙骑兵们向来当成笑话看待,完全不需要像对面一样定期给边防军上思想课。这等内容就算真的在异族耳边循环播放,也只会招致冷笑。
倒不是说他们真的想挖苦异族,塔砂相信,帝国真的在为劝降努力,只是从未没学过如何以少数派的方式思考罢了。最主流、最强势文化的主人时常会忘却世界上还有其他族群存在,以往对少数派们不屑一顾,待到风水轮流转,别说要屈尊融入其中,哪怕想摆出一副平等的姿态,也会不自觉暴露出固有思维中的傲慢——没法藏,他们都没想过那是对异族的冒犯。
放下武器,回来吧,他们苦口婆心地、仁慈地说,我们不杀你们了!只要你们向帝国低头,我们就会容忍你们这些天生罪人的存在,允许你们夹着尾巴在帝国中担次等公民,这岂不比在那里担惊受怕好得多?
呸!在塔斯马林州工作与生活着的异族们讥笑道。机械鸟喋喋不休,拿着洗衣篮的独眼巨人想往上头踢一脚,被同伴拦住。“别啊。”同伴劝说道,“完整的机械鸟,上交的赏金多好多呢。”
独眼巨人一琢磨,是这个道理。一想到回收垃圾能得到的奖金,她顿时觉得受点精神污染也没什么了。
徒劳无益地送菜许久后,帝国才慢慢明白了劝降稿存在的问题。
“你不觉得最近的机械鸟说话好听起来了吗?”维克多说,“总有一些机械鸟成功带着观察到的信息回去,我还以为你会得更严呢。”
“没这个必要。”塔砂说,“有来有往的才好。”
“是吗,你真客气。”维克多用明显不相信的语调说,显然觉得塔砂在打肿脸充胖子。
“封锁对峙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啊。”塔砂说。
塔砂的目的从来不是裂土为王。
要想这么干,一开始就能养一堆人在地下关起门来做皇帝了,地下城自给自足的体系能支持她这样做,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塔砂没有占领全埃瑞安的野心,不过,她想让她的影响力覆盖整个埃瑞安。
帝国正在帮她的忙。
他们越研究塔斯马林州内部的情况,越没办法无视异族们存在的现实,越没法否认异族与人类的相似之处。现在大地上所谓的人类与异类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总有一天,他们得承认混血族裔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总有一天,这些带着恶意观察他们的人中,会有人意识到,不同族群也可以和平相处。
只要有来有往,流动的水总会彼此混杂,交流融合。就像一家独大的单调鱼池引入了新的品种,在竞争之中,池水活动起来。
帝国的机械鸟宣传帝国都城便捷舒适的生活方式,塔斯马林州就借机推广魔导科技学校,能培养技工的专科学校与能培养科学家的高等学校纷纷招生,而更多基础学校开办。随着魔导工厂一间间开放,对认字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当进工厂做工与进行商业活动的收益大于务农,将孩子送去学习不再是那些想谋求官职的富裕家庭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将孩子送入学堂,识字率在几年内迅速上升。
地下城的无人机永远在抓帝国的把柄,只要不幸被侦察机或飞鸟发现,那么帝国前脚抓捕了异族,后脚“帝国某处军队根据红雨探测仪结果秘密逮捕折磨公民,可怜三岁小儿命丧黄泉只因被判为异族”之类添油加醋又带着微妙证据的新闻就会被无人机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足够当地居民又恐慌一波。
红雨之前固然有人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红雨之后,每个人都了成为下一个受害人的可能,包括军队乃至军官。人们风声鹤唳,而受惊的羊群也能踩死虎狼。“逮捕疑似异种”过去被视为毫无麻烦的差事,如今渐渐变得棘手起来,以此充当业绩的官员越来越少。
双方的广播、报纸与新闻业都在口水仗中高速发展,多方面多角度的信息让双方的听众们有选择与思考的机会。帝国那边的禁令难以实行,当缺口已被打开,私底下的讨论屡禁不止。塔砂则从不阻止人们讨论,无论那些声音是善美还是丑恶,睿智还是聪明,让他们自己说去吧。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话负责,而要是伤害到了别人,那就是司法部门的事情了。
“夜幕”落下两年后,不知是否该说意料之中,撒罗教成为了塔斯马林州最广泛的信仰。
撒罗圣子塞缪尔在最初的兽人奴隶中传播了撒罗教,以光明与正义为中心的信仰开始只是一种理念结社,在后来才慢慢有了较为清晰的教派组织。撒罗教会在战争与战后都很活跃,救助伤员,超度亡者,安抚生者,劝解俘虏,填补了迷茫者空虚的精神世界,规模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寿命悠长又命途多舛的撒罗神教,在过去五百年中发生了几度变化。
天界被隔绝前,它是善良守序的神圣教派,面向所有善良种族,嫉恶如仇,同时虔诚地信仰神明,一切以神明的旨意为基准;兽人战争前后,残存下的神教变成了光明教会,圣殿骑士变成了圣骑士,由叛神者组成的教会只为人类而战,否决神之名也否定所有异族;灭法战争期间,同为施法者的牧师和法师一个下场,带着神器逃离的幸存者们在帝国角落苟延残喘,怀着怨恨与不甘开始企图复古,形成了塞缪尔养母坚持的那种,比曾经的撒罗神教更严苛的奇怪产物……
而如今的撒罗教,无疑不是塞缪尔的养母讲述的那一个。
它念诵太阳神的神名,却让人们对心中的光明祷告。圣子声称神之爱遍及整个世间,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什么种族,只要发自内心地信仰,便能得到心灵的平静。有着黑暗族裔的血统也好,用着与光明正大无关的肮脏手段也好,心怀善念便总能得救。
“如果真的撒罗看到他们在搞的事情,没准会气得一道雷劈下来吧。”维克多幸灾乐祸地说。
因为此等理由,他对撒罗圣子提交的申请全都相当热心,甚至怂恿塔砂立一个撒罗神像。“我可是亲眼见过撒罗的啊!”他兴致勃勃地说,“我想想,嗯,要黑头发,红眼睛,蒜头鼻,麻子脸,一大把肮脏的胡须和鼻毛混合在一起……”
塔砂对这等幼稚行为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撒罗的圣子,如今的撒罗教宗塞缪尔,并不要求立一个塑像。
“不应当膜拜偶像,神灵在我们心中。”他这样说,也谢绝了信徒花钱请神像的要求,“只要你们虔诚祈祷,回馈世人,那便胜过参拜神像百遍。”
曾经生嫩的年轻人已经三十多岁,看上去温柔而稳重,与那身撒罗礼服更加相衬,适合被画进宣传单里到处分发——事实上撒罗教就是这么干的。“神爱世人”,几个大字搭配着阳光下身着礼服的教宗,金发碧眼的温柔圣徒对着画面前的人张开双手,带着悲悯的微笑,这套宣传单时常一印出来就分发到脱销。它名列“十大不会让主妇随手扔掉的广告单”第一名,即便你不信教,留着宣传单也没什么不好嘛。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把宣传画贴在准妈妈的门背后,坚信在撒罗神的保佑下,多看教宗几眼能生出长相俊秀,咳,是品德高尚的孩子,也不知是出于哪门子原理。
塞缪尔在各族下到八岁上到八十岁的女性中有着惊人的人气,他已经从过去的搞笑吉祥物变成了……塔砂觉得比起高高在上的教宗,这位依然过于年轻美貌的年轻人可能更接近偶像一点——为了拯救心爱的撒罗教,一名年轻的牧师站了出来,决定成为偶像……听上去很合理嘛。
当然,塞缪尔并非徒有其表。
他曾去黑暗的墓园为战士们守灵,也曾去过人来人往的沙龙,在质疑和嘲笑中传教。他去战俘营中劝说那些拒绝合作的人,战俘往他脸上吐唾沫,塞缪尔神情平和地擦掉。
“你这个谎话连篇的叛徒!”战俘骂道。
“我曾经心存迷茫,却不曾诉说谎言。”塞缪尔说。
“是吗?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