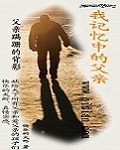消失中的江城-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里拿着烟,那是他受伤的补偿。没有人去留意他——然后中华号鸣笛,从码头出发了,争吵被忘在脑后,乘客们都在看城市在后方滑走,而轮船游入了大江的心脏。
重庆往北三英里,江流突然东转,这个拐角处的标志是一座佛教神龛,还有一座风吹日晒的宝塔,高踞于水面上。山岭开始升高了,葱绿崎岖的山岭让位于一排排留着去年水渍的石灰岩。许多山坡都太陡,无法建房,而随着船往东行,小块的农田越来越多见。农民们的房子是简单的:泥或砖的墙上是灰色的瓦顶。它们经常都在芭蕉树荫之下。沿着江的两岸,总有田台,在工厂不能驻足的地方嵌入山坡。
景色静谧美丽——不会让人屏住呼吸,然而值得回味,略显粗糙的山丘,不太规则的台田。重庆静静地留在我们身后了,突然,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了,这片风景里的一切,都是由长江厚重的力量所塑形。
因为江流在这里显出了力量。有时它宽为几百英尺,有时它被挤在窄窄的峭壁中,但水流总是强而有力。长江从西部的大山中融雪而下,在这儿它那七百多条支流已大部分融入了,就这样,它迅疾地掠过山岭。在世界上的大河中,唯有亚马逊河带入海中的水量超过它。
太阳下沉了,一阵凉风扫过江面。大多数的游客都在甲板上,看着山岭掠过。一群广东生意人拿起手机在耳边,用粤语大声说话。一个年轻女子独自靠着栏杆,她长长的黑发与粉色的短裙在风中飘舞。
空气如今干净了,只有几片云摩挲着渐暗的蓝色天空。小渔船开始泊岸过夜了,而中华号掠过了一群在潜流中赤足玩耍的小孩。玉米在山上长得高高的。玉米有两个月大了,刚刚开始进入成熟期;它的根茎带着春天的新绿,而顶上开始转为金黄。
在河岸边没有稻谷;山岭太陡了。有些多石的斜坡对玉米来说也很困难,但即便在最粗砺的坡上,也有耕耘的痕迹——至少,有一处单独的玉米地长于岩石的缝隙中。这些作物乃是垂直往下,一路从坡上排列下来的,而那些山坡都尽可能的耕平过。
在这个地方,谋生不易。那些最成功的农家往往有一栋两层的小楼,一个大猪圈,一个不小的水泥打谷场,十几处嵌入山丘的玉米地,然而即便它们也在述说着在此种植的艰辛。每片田台都由人类的努力打造而成,背后是同一族的人,许多个十年,甚至百年的工作。所有的这些都是依靠手脚,以及基本的工具。这些田台变化得十分缓慢,看起来仿佛是自然力量所形成的——一种跟大江一般坚决而有力的东西。人类的历史沉重地压在这片土地上,在中国经常都是如此。
太阳西沉中。天空耀出橙色,山岭渐暗,太阳的圆盘发出一道明亮的光带,在轮船身后的水面上。然后,在西面的山岭后,它落了。
在一个三等船舱,一对年轻男女在地板上整理他们的行李。他们可能是十八岁,也可能三十岁,就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就是年轻。船舱内有八个铺位,作上下铺布置。一个老妇人坐在一个下铺,问那一对最后两个床位是否他们的。
“我们用一个铺,”那年轻女子说。“我们刚刚结婚。”
乘客们共用床位没什么稀奇的,但那年轻女子的丈夫红了脸。那女子,形貌标致,留着短发,笑着碰碰他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貌地交谈了一阵。她们问彼此刚才吃了什么,去哪儿,在重庆干什么。新婚的夫妻要回宜昌的家,那老妇人去武汉,而两个人对重庆都没什么好话。
“很落后,”那老妇人说,摇着头。“人们的收入太低,生活费用太高。”
那年青女子表示赞同,她说重庆的交通很不方便,它不如宜昌好。
她丈夫什么也没说。他帮妻子脱去了鞋子,然后爬上床靠在她身边。借着舱内的灯光,他读起一本杂志,而她打着盹。铺位不到一米宽,而他们却躺得舒服。
夜里的江上很平静。夏日的星星今晚出来了;北斗七星在轻柔摇晃的轮船上空发着光,四分一个月亮在南面天空上悬挂着,亮亮的。江水漆黑,除了一道道的光带。现在岸边很少有房子了,而灯光则更少。大多数的光线都从江上来——河滩上的砂岩石在夜里微弱反着光,还有充气橡皮艇;江的南岸有红灯闪烁,北岸是绿灯;夜船在其间经过,它们的探照灯沉默地掠过江水。
在夜里没有水翼船,没有渔船,没有两人的小舢舨。偶尔,中华号会经过一条长长平坦的河岸,那儿有过夜的小船停靠,在岸边的竹房窗户透出温暖的光——临时的餐馆,旅店,麻将馆。货物交通都停了。
江上的其他船只多数都是大客轮,经过时,犹如亮着光的浮动小岛。有些是从上海一路逆流而上,穿越了安徽的平原,经过了湖北的湖泊,武汉的工厂,三峡的峭壁,现在,离重庆还有几个小时,它们快到家了。
过了一阵那年青女子醒了。她在床铺上转转身,跟丈夫靠近点。“你是谁?”她的声音轻柔,调皮。“你是谁?”
她丈夫咕噜着回答了,而她静静笑起来。船舱的门开着,能听到外面马达平稳的声音,还有江水拍击船底的温柔回响。“你是谁?”那女子再次低语。
很少乘客在涪陵下船。多数人都要再坐两天,穿过三峡到宜昌,或者,三夜去到武汉。涪陵好似一个停顿,在梦中——静静的大江,满舱朦胧欲睡的游客,城市的灯光从长江的幽暗中升起。
重庆出发后已过了四小时了。灯光群聚在岸边:有家,工厂,汽车。一座新建成的桥跨在头顶。轮船的扩音器响了,宣布涪陵是下一站,然后大江的梦停了,城市进入视野。
涪陵的心脏地带围绕于江上的一个小湾而建成。从这个小湾的弧线开始,城市立于陡峭的山丘上,好像窗帘透着光——有小商铺灯泡的微光,有的士车头灯的光束,有四方形窗户的黄光——而这个点亮的窗帘,落在长江的黑水之上。中华号向江滩驶去,汽笛长鸣,码头渐近。轮船一直往南,直到脱离的江水的主流,直到那长江的巨大力量被留在身后,然后,轮船泊上了码头。
第十二章
逆流而上
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马克吐温,凯特卓别林,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蓝斯顿休斯,之后,作为最后的单元,我布置了谭恩美,和一些美籍华裔的诗人。这些文学对我的学生们来说那么遥远——李普范文可,蹦跳的青蛙,以及休斯那遥远的河流——而突然我们看到了电影“喜福会”的结局,当那华裔美籍的叙述者来到了中国,跟她的姐姐们重逢了。这是中国头一次真正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演绎了莎士比亚,他们写过罗宾汉来中国,但这些只是将外国文学放入熟悉的背景中。现在,我们真的到了这里:叙述者在拥抱她久未谋面的姐姐,班上所有的女孩都哭了,而男孩们忍着泪水。
之后,我让他们写写他们的家庭,描述他们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一个叫蒂娜的女孩,写了首诗:
回头看我的祖先
一个赢弱的女子
坐于一间陋室
一遍遍摇着纺车
她不能出去
她的脚被封建主义深深困死
在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祖母出去革命
去上海,去重庆
她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文化大革命
当了红卫兵
她否定一切先进的事物
叫着毛主席万岁
许多人和琳达一样,写到了乡下的生活:
我的外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得为地主当佣人。她受了很多苦。她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足够的衣服来御寒。她的主人待她很不公平。
同样,我外祖母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她的脚被束了,非常疼痛。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三个都死于饥饿。这让我的外祖母非常悲伤。她哭了整整三天。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死于疾病。她做了三十年的寡妇,受尽了艰难困苦。
我母亲的生活比她们要好一点,因为她正好在新中国成立时出生。我的母亲不太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她对我们十分温柔。当然,她的生活也并不很如意。她必须艰苦工作以维持生计。她在寒冷的日子里出去割草喂猪;从很远的地方运煤来取暖;她一直为我们缝补衣服。她为她的家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几乎所有的卷子都是那么写的,我发觉我没法给它们打分——甚至在角落里作一个收讫的记号也不行。它们中没有什么是我能碰的,而其中一些我甚至不忍读,因为它们都太心酸。在最后,我无法把这些故事还给他们,我把它们保留下来,只是跟同学们说他们写得不错。
他们的写作,在让我想到过去时,也想到了未来。我看到了那持久无声的挣扎,把同学们带出了今天的样子,而对下一代来说,情形或许也大致如是。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是一个大学生,生活比她母亲好一点。我想象她写道,“我的母亲不是很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
下课后,我常走到校园后的乡村去。我已经停止跑步,走路的感觉愉快——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可以跟农民们聊天,看他们干活。他们常问我是否认识那个在山上跑步的外国人,而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干那个了,这看起来让他们松了口气。在插旗山上乱跑毫无意义。
在夜晚和周末时分,我遵从着我的城市路线。星期天上午已经安排得很完美了——教堂,神甫,铁匠,茶室,然后我会去南山门公园对面的餐馆里吃饺子。那饺子乃是涪陵最棒的,通常我会在十一时准点开吃,这时会有个十二人的铜管乐队在公园演出。这乐队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来,被结婚的新人所雇,因为一场好的婚礼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这里头面子大了。乐队会演奏“友谊地久天长”,以及“虔诚的人们啊”;而棒棒军肯定会忠实到访,直勾勾盯着新娘看,她上着明艳的妆,盛服出场。
在餐馆里,我通常会选择一个特别的位置,靠在墙上,望向街道与公园。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每日生活秀比乐队更佳——带着篮子的农民,带着孩子的家庭,年轻夫妻出来逛街,老妇人举着雨伞遮阳。
在周中,我经常去拜访高明与马福来,两个春节时我在公园里认识的朋友。高明是个艺术家;他二十六岁,几年前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他很有天赋——他的寓所里满是他自己的油画,多数都是欧洲风格。他自己在涪陵有生意做,他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字大块的霜玻璃上作画,蚀刻上花卉,竹子,大熊猫,以及其他中国人喜欢的图案。一般说来,这些玻璃会被裁开,用作餐厅或者公寓的装饰。高明对这项工作特别在行,这就是说,他做的玻璃特别的俗气。这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按照客人告诉他的去做,通常,客人们会叫他能用多少颜色就用多少颜色,能画多少形状上去就画多少。
他的客户们乃是涪陵的富人,有些时候,我会陪伴他去客人们的家,去运货或者收订单。每个城里的富人似乎都有一致的装饰方式,以某些物事为富裕的标志:高明的玻璃作品,华丽的吊灯,围绕着巴洛克式的天鹅绒与石膏像,怪异的木质格子棚,挂着塑料的葡萄与藤蔓。另一个普遍的装饰,乃是一个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