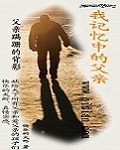消失中的江城-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不是亚当想要的效果,但好歹这些单子里也有许多关于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亚当细细解释说,你们可以“写任何想要的主题”。
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头写出了上面的文章。亚当和我坚持工作,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努力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城市
在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它则和其他的中国小城类似——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
没单车的原因在涪陵到处是阶梯,而处处阶梯的原因是城市被紧压在两江交汇处的大山脚下。狭窄的街道从河岸开始延伸,呈Z型爬上山坡,看似痉挛一般,而且太陡了,单车用不了。汽车的交通在那些急弯处搅成一团。所以那些长长的石头阶梯才是涪陵真正的大道,承载了这里大部分的交通———逛街的人们拾阶而下,不时停在商店门口瞄瞄看看;搬运工则往上爬,肩膀被竹篓或一捆捆货物压弯。
几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务都可在这些台阶边找到。有商店和餐厅,补鞋匠和理发匠。低处有一排阶梯上道教的算命先生成行。另一排则有三个牙医的家,他们在一张桌子上用生锈的工具做事,注射器里有不明的液体,金属盘子里有一排烂牙———像是一种恶心的广告。有时会有个农民停下来拔牙,在一通激烈的杀价之后,会有一群人围观。所有事情都是公众的事儿。一次理发总是伴随着一个观众。每一个买卖的价钱都会被路过的人评论。生了任何病,都可以去找一个露天位的中医,他在某一台阶的高处有个固定的位置。他的立足处有一把凳子,一个装满了瓶子的盒子,还有一张写满了大字的布单:
替您排忧解难
特别治疗:鸡眼,黑痣,耳屎
手术———无痛,无痒,不流血,不影响工作!
涪陵不是个容易住的地方。年长的人在台阶上休息,喘气。要把任何东西运上山都是要累断背的工作,是以城里到处是搬运工。他们用扁担把货物平衡在两肩上,和1800年代中国的情形并无区别,当时英国人叫他们“苦力”,从中文而来的,意思是,“辛苦的力量”。在涪陵这儿,和四川东部的所有江城一样,这些搬运工被称作“棒棒军”。他们身着制服(中国农民的那种蓝色服装),身带交易的武器(竹竿和一圈圈廉价的绳索),他们总是群体出动,相互作伴。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如同和一个军团砍价。即便没有激烈竞争他们的工作已足够艰苦,是以他们互相照顾;这里没有正式的公会,然而苦工们非正式的纽带却更显联系紧密。在中午时,当大部分人在休息时,棒棒军们会坐在城中的马路两旁,坐在他们的扁担上,抽烟,聊天,打牌;他们的休闲气氛,与其说是放松,不若说更似战斗的间隙。
他们的大多数乃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到码头来尝试自己的运气,通常情况下,会有他们的妻子或兄弟在家里看田。在冬天里总会有特别壮大的棒棒军洪流,因为那是农村的淡季,农闲季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手哪儿都不缺,在他们那种沉默的无孔不入的存在中,有一种怪异的气氛。他们会一群人站在电视机店门口,盯着一排荧幕墙看。若有一个外国人在街角的排档吃饭,立马会吸引十个棒棒军围看。若在码头发生了什么争吵,他们会立刻聚集起来,所有人身着蓝色,手中握着扁担,非常用心地倾听。偶尔会有个小小的杂技团停留在涪陵,在河边的平滩出扎下帐篷,帐篷前的广告或多或少会主打些脱衣女郎,而总会有一整队的棒棒军往帐篷的缝隙中瞅。一次汽车事故不算真正的事故,直到一组棒棒军赶来观看。他们是一群安静的男人———即便最惨烈的车祸有时也不能让他们开口———而他们也从不介入。他们就只是那样看着。
但看到他们的工作,就足以明白为什么他们老停下休息,因为在这个艰苦的城市里,没有比他们的工作更艰苦的了。运一次货他们大约得到一两块钱———美元和人民币大约是1比8——每次,这些工人大约要往台阶上面运一百磅的货物。他们都是矮小粗壮的人,他们的身体被山城和工作所塑形。在夏天他们赤膊干活,你能看到扁担已把他们肩膀的皮肤磨得如同皮革。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浸透了汗水,在冬天里他们身上冒出水汽。在卷起的裤管下他们的小腿筋肉高高鼓起,好像那儿绑了棒球。
涪陵是个腿的城市——棒棒军粗糙弯曲的腿,老人的罗圈腿,小姐们柳条般的细脚踝。爬阶梯时你得看着自己的步子;你会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买东西,你也没看一眼这里的建筑。这城市就只是台阶和人腿。
而这里许多的建筑都不值得一看。在乌江的两畔,还有一小块旧城区,在那里,有古老的木石结构的房子,顶上铺着灰瓦。但这片区域在缩小,很稳定地被一众毫无特征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这里有些高楼,七楼或更高,然而和中国许多新建筑结构一样,它们都是用蓝色玻璃和白色瓷砖廉价拼成。而即便你真在涪陵建起座漂亮的新楼,很快它也会在煤灰覆盖下褪了色。
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涪陵城市建筑的主体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实上,这城市已经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这里是巴国的首都,一个后来被汉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给它留下一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汉朝叫涪陵,晋朝叫吉县,北周叫汉平,隋朝叫凉州,唐朝叫抚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时叫重庆,在清朝叫抚州,中国民国1912年成立后,叫作涪陵。
但这些朝代都过去了,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建筑可以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其发展吞没了其历史。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为了装人,那二十万人,每天在爬阶梯,在拥堵的交通中奋斗,工作吃喝,买卖。
清晨。一个凉爽的上午,城市被轻霾笼罩。退休的老人在小公园里打太极,在近南山门的地方,这里是中央枢纽地带。涪陵相对显得安静,这是最安静的时分了。已经有了稳定的交通量,总是有许多司机揿喇叭;但道路还不拥堵,城市的噪音还未释放出力量来。这是一个愉悦的早晨。
退休的人们排列成整齐的几排。一只收录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缓慢做着运动,姿势优雅。公园很小,说是公园不如说是城市的休息地来得恰当。这儿有昏迷不醒的灌木丛,筋疲力尽的花儿,以及伤心的草。但它们不是维护得不好,破坏公共财产这种问题,在涪陵是不会有的。问题乃是出在空气,煤灰如毯子般笼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着呛着了。几乎没有什么会惨过涪陵的树了,它的叶子灰暗,迟钝,好像刚从阁楼里取出来。
当阳光开始渗透城市的轻霾,城市的轰鸣声开始升起。喇叭声,电视机店铺的吼叫,磁带摊的嘶喊,路旁小贩的叫卖声。在南山门的东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缓期执行,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盲人拉着二胡,音乐轻柔而如针刺。
二胡意为“双弦”,这就是全部了。一个简单乐器的简单的名字:一个圆筒状的木质发声盒,盖了层蛇皮,上头一个直挺的把手上有两根弦,延伸到整个乐器那么长。它看上去像是个简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这对弦有宽广的音域,若拉得好,音乐令人心魄。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约四十上下,但脸看起来更老些;黝黑,起皱,双目紧闭。他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衣服和绿色帆布军鞋。他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旁边有块布,写满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岁的女儿站在一旁,手中一个罐子里钱半满。一小群人聚集过来,因为二胡的音乐,即便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也充满了力量,足以让人们停步,聆听。他们读着写在布上的字:
一个家庭的简短故事
我在二十岁时结了婚,在二十一岁时我失去了双眼的视力。结婚11年后,我有了个男孩,然后,在1988年12月2日有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我的老婆和我共同养育着两个孩子,希望能靠家里的田地国货。但我们家里缺乏人手,我们碰到了麻烦,因为稻谷收入总不稳定。我的女人必须竭尽全力来拉拽她身后的所有人,到最后,她活不下去了。为这个原因,我们在1996年1月8号逃离了家乡。
因为我双目失明,每一天我都难以过活。在1996年3月2日,我被迫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老丈人家去。我的儿子十四岁了,因为没钱我们无法送他上学。我希望你们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哥哥姐姐们,伸出你们的援手。我千恩万谢。祝你们事业成功,长命百岁。
二胡继续拉着。音乐自如起落,声音从蛇皮盒里流出,从不被急速的车流人流,电视机声所淹没。最后那男人停住了。他轻轻放下二胡,掏出了他的烟管来。他用手指触摸烟草卷,叫唤他的女儿。她小心地点着了烟管。盲男人深吸一口,后仰休息,城市上午的轰鸣声围绕着他。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在涪陵我教英国和美国文学。我也会上写作和口语的课,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教文学上。这儿有两个班的的三年级学生,我每个星期各教四个小时。我们的课本从贝奥武夫开始,穿越十二个世纪和一个大洋,以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收梢。
有非常多的内容要覆盖。和平队给我的建议说不要对这类课程抱太多的雄心,考虑到我们的学生们的背景,他们的英文基础有限。建议说我们应当借用文学来做重要的语法知识练习,但这个主意我不喜欢。我知道在语言的文法方面,我不算一个很好的老师,而莎士比亚则会更糟。我学文学太久了,不会把当它当作工具。
但我还是有一些担忧。这些学生毕竟是从乡下来的,而的确的,他们的英语,尤其是口语,有时很不行。上课的头一天,我让他们写下所读过的英文书的标题,英文或翻译的都可,我还问了他们想从我的课上学到些什么:
我喜欢海明威,老人与海。我最想学海明威。
我最想学海伦凯勒和莎士比亚。
我想读杰克伦敦和他的荒野的呼唤,狄更斯和他的双城记,欧亨利和他的最后的叶子,莎士比亚和他的李尔王(他让我哭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简爱,夏洛特布朗特作的。我不晓得那是哪个年代的作品。我喜欢简。她是个普通的女人,有着不普通的追求。她敢于反抗舅舅的老婆,反抗她的表哥。她是个进步的女性。
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英文作家。我读过他的一些书。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可怕的故事。罗密欧和朱丽叶彼此相爱。但他们的家庭相互憎恨。
我还读过“永别了,武器”,海明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