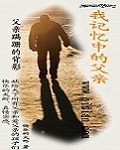消失中的江城-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鼓,来吸引客人。马拉的车往小餐厅里运送煤炭,而太阳明亮地升起于建筑的瓦顶,缓慢的,这尘土飞扬的城市热起来了。
榆林的主路要经过三座明朝的塔楼,而街上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墙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么高。我从没在中国见过保存那么完好的古城,然而城里没有其他一个外国游客。
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
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么?”我问。
“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
“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
“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
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的儿孙。
罗家住在主街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里,几座砖房围着一个中央的庭院。现在,那里住着家庭的七个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罗,而这建筑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大变过。在老人的家里,人们依然睡在传统的炕上,一种旧式的砖床,在冬天里用煤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人乃是来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来这里对抗城墙外的蒙古人。他们来到这里驻扎,是为了将外国人挡住,而他们的后人还是受到了外国的影响——传教士在解放前将老人的父母转化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挂在他的老炕上方,一个奇特的文物。
老人的儿子叫罗小雷;他年纪在四十多,在本地编辑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女儿刚从榆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毕业。他们都是友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他们的家。他们经常给我一份早餐,吃完后,我们会坐在他们起居室的阴翳下喝茶,吃西瓜。
罗小雷在文革期间蹲了五年牢,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亲被发配到沙漠的偏远地区呆了十年。老人对这段经历没说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无意义之外。这通常就是人们关于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费的时间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发现和罗家人坦诚交流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不那么轻信,也因为我不久将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为我所说,所做负多少责任;我可以随便晃荡,碰到任何人说任何想说的话。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儿人们会跟踪我的记录,而且我总会想到我还有一年时间要呆在那儿。在中国,有一个家当然会带来不少好处,但也有些缺点。
一天下午,罗小雷问我,对于在中国教书我有什么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多数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说,“尤其是我喜欢我的学生们。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孩子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那也很好;我的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这体系会影响到我的学生。许多人的想法都是狭隘的。”
孔老师教给了这个词,在接近学期末的时候,而它总结了涪陵生活的许多困难之处。罗小雷点点头。“也许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说。“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你知道我们没见过多少外国人。”
“我知道,但那儿还有些别的问题。他们的书很烂,有时他们所学的不是事实。”
我问他坐在身边的女儿,他们在中文系里学不学孔子。
“不,”她说。
“但你们学马克思?”
“是的。”
“这和涪陵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是外国的观点,而孔子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没人再去学习他了。”
“你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学马克思么?”她问
“是的,但就一点点。许多美国大学生都会学,因为他是个哲学家。”
“你们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怎么想?”
“多数人会觉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这个词汇,而她知道我想说什么。
“实用,”她说。
“是的,不是很实用。”
“我同意,”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学习都是浪费时间。”她掠起脸上的头发,望向她的父亲。他在想着些别的什么,然后他意识到了女儿期待他回应,微微一笑。他是个灰发的男人,戴着圆眼镜,眼里亮闪着回忆。
“是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用。”而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荫凉处吃着西瓜,没有说话。
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随着一个惯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访罗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厅吃饭。那餐厅的饺子不错,还有便宜的当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个风格强悍,不说废话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后喝酒的地方常能见到的那种。她戏弄我,说我的口音一半外国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进门,她就开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国籍,年纪,中文名字,单位,以及工资。通常客人们会对我的工资之低发表评论,然后买一瓶酒给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会解释和平队的性质,而我们是来帮助中美建立友谊而非赚钱来的,这只会鼓励人们给我买第二瓶酒。我想要付第三轮的钱,通常以失败告终。在那之后,我们会握手,说些改善两国关系的话,然后我会回到旅店里,睡到夜凉。
我在榆林的最后那天,有两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进了餐厅,开始给我买酒。其中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说我可以叫他们同志。那天是礼拜五,他们刚刚上完了早班,在附近的一家工厂。
我们每人都很快喝完了两瓶啤酒,在接下来的一瓶,那两个男人开始脸红了,讲起中国的历史故事来。王同志告诉我禹帝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治理黄河的人。这个故事我曾在教科书里学过,运气很好,因为王同志讲着讲着就混上了方言。我不断点头,表示我听懂了,而每过一阵,赵同志会插嘴:“说普通话!你说方言他不会懂的。”
王同志会点点头,说上几句普通话,然后又转回方言,关于禹帝英雄般地建起了沟渠和防洪堤,在黄河的两岸。这故事的要点在于,禹帝干得那么勤奋,以至于他经常经过家门口却无暇停步拜访。这真是个要命的工程,控制黄河。
最后河流受到控制了,而王同志坐下来喝光了他的酒。他们买了许多瓶酒,我们的桌上满是空瓶。中国小餐馆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会清理那些空瓶,直到你离开,那就意味着路过的人可以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个下午搞了多大的破坏。这显得很有面子,而我们今天干得不坏。
“你听懂了这故事么?”赵同志问。“你不懂,是不是?他总在说我们的方言!”
我说一切都很清楚,然后从我的课本里背出了那些段落。
“你看,”王同志胜利宣告。“他全部听懂了!”
突然,有一股急迫的需要,王同志要向我展示他的投资,在街下面不远处,店主同意帮我们保留桌子。他们都是高大的男人,而我走在他们当中,三个人踉跄走在鹅卵石地上。在经过罗先生的摊档前,我向他招手致意。我不知道我们要到那儿去,或者那投资是什么——他们只是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同志的投资。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酒后我们出着汗,在街上走着。
我们进了一个门口,爬上了狭窄的楼梯。在二楼,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小女孩穿着轮滑,在硬木地板上转圈。
“这个,”王同志说,“就是我的投资。”
他骄傲地看着溜冰场,然后跑去了柜台,跟工人说话。
“这投资太大了,”赵同志悲悯地低语道,当王同志出了接听范围。“他借了很多钱。他永远还不了!”
我能看出王同志在跟工人说着我,我有点紧张,想听听。
“他们没有多少顾客,”赵同志低语道。“昨晚,这里有人打架,一些玻璃碎了。他要亏上很多钱!”
王同志拿着轮滑鞋来了,递给我。“来,”他说。“你来滑。现在。免费。”
我结巴了,解释说我不会玩这个。“你当然会玩!”王同志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有点腿受了伤,而他们则提出带我去看医生。街下面有一家,赵同志说,而中医乃是非常有效的。我解释说我了解中医的好处,因为一个中国医生叫我多坐少动,避免像轮滑这样的运动。在许多礼貌的建议与抵抗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回到餐厅,坐下来,继续喝酒。他们看上去没觉得不爽;王同志很高兴他给我秀了他的投资。空瓶子还在桌上。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盯着我的眼睛。
“何伟,”他叫着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唯一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嵋山上,我的印象很不好。他很肥,而他总是使唤别人。‘做这个!做那个!’有工人抬着他上山,好像一个大地主。但你不同——在碰到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坏,但现在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被感动了,为自己那个医生的谎话觉得愧疚。但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白谎,也许那也行了。我谢了王同志,相互敬酒。
“还有,那个峨嵋山上的美国人很白,”他说。“他的皮肤那么白,长得那么难看!但你其实有点黄——你看上去像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好多了!”
那个夏天,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好。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习,课程不是很难,而这城市有许多的公园,我可以在那儿买一杯茶,和当地人聊天。每天,温度都是摄氏三十五度。政府好像有一项政策,如果温度到达了三十七度,则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们总是宣布说官方的温度是三十五度。我经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到兴庆宫公园,在那儿要杯茶,向工人们询问气温。
“三十五度,”他们会说,用报纸扇着扇子。
“昨天的温度呢?”
“三十五度。”
“你觉得明天会是多少?”
他们会转转眼珠子,告诉我去喝我的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笑话。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来控制气温的国家,虽然两年后,北京的气象台终于开始宣布真实的气温了。当地的报纸欢呼这一发展,作为是迈向对市民说真话的重要一步,也许它的确是的:今天是气温,明天是天安门事件。但政府也让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过是神话而已,所以新的温度没有带来任何假期。它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热。
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象的最热的那种,在晚上我没法入睡,但即便是那么炎热的夜晚,这个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当一名地理学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个暑期的项目。她来西安和我共渡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看了城市的历史古迹。我总是告诉人们她是来帮中国人找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