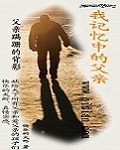消失中的江城-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
大坝对于那些不幸住在河岸两侧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会去惹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已经因他们的历史而变强韧了,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触及这城市的重大变化都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太平天国的战士从东边儿来,国民党从南京而来,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起始于北方,顺着长江的河谷而至。三线工程来了又走了,横扫一切。在最近的几年里,新鲜诱人的产品沿着长江,由重庆顺流而下,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外国人也开始在涪陵的下城区马路上亮相了。你只能接受这些变化,顺应它作自我调整,因为你无法控制。这就像长江一样,它从某一它方而来,往某一它方而去。未来的有一天,它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能应付。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大江的上升会带来什么问题么,而他就和孔老师一样,看似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嗯,”他最后说,“船会浮的,所以不会有事。”
这里有一种观念,即大坝单纯只是件好事。它意味着电力,那代表了进步,这就是对涪陵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事儿了。完工的大坝所制造的电力,据估计,相当于一年五千万吨煤的耗用量,这对一个严重污染的国家来说,可不算是个小的收益。在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死亡乃是与肺病相关的。有些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望着长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它奔流的日子可数了。但还有许多的日子,当浓雾笼罩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
在冬日里,我对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当这儿出现了周期性的停电。我的公寓里只有电力取暖,而停电有时持续数小时———绵长,寒冷的数小时,黑暗的公寓里,不舒服的感觉在滋长,直到我的呼吸在烛光中泛出白汽。我发现,在这种时间里,我不会考虑涪陵的新堤坝建不建得起来,或者新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或者白鹤梁是否被有效保护。我想到的只有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它将所有事情简化。
而在中国,许多人也作如是想。这跟美国的情形不同,在那儿,每个市民平均拥有三千瓦的电力供应———足够让所有人同时打开一个烤箱和一只吹风机。在中国,每人平均150瓦,只够每人拧开一两只轻型灯泡。而对于六千万中国人来说,一只灯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供电。
这类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国家治水已有许多个世纪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都不曾有过如此长久成功的历史,将河流为人所用。四川省中部的发展,最初就得于都江堰的建造,一个设计非凡的灌溉系统,两千三百年前建造的,而直至今日依然完美运转着,将成都盆地变为全国最富饶的稻谷产区之一。即便长江也曾被驯服过,虽然规模相较小得多;葛洲坝在1981年完工,在如今这个工程的下游。
但另一种历史是河南的那种,当1975年时,暴雨导致了62座现代的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一座接着一座,有两万三千人死亡。虽然那次灾难的规模很独特,但糟糕的工程技术却不算那么异常: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有3200座大坝溃决过。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大坝的失败率为3。7%,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0。6%。
到了最后,我就像涪陵的大多数人那样———我消极地观看着大坝的准备工作,而我也尝试不要下太多的判断,批评。毕竟,我只是个外人。但我想,在大坝修筑之前来到这儿比之后来好,而且能看到白鹤梁,以及驯服前的长江,也很好。这里有人类的历史,有长江的历史,而当它们相互冲突,永远改变这个地方时,我不是特别想呆在这儿。
乌江
这钓鱼的老人并不指望真能钓到些什么。“现在钓鱼不是时候,”他说。“冬天太冷了;鱼儿不太动。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退休了——我就是来玩儿的。”他笑笑,望向乌江绿绿的水。老人在空中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在他身边,他的钓竿也直直坐着,靠着一块石头。好几个小时,老人和他的鱼竿就这么坐着,在一个类似今天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们就和岩石一般沉默,一动不动,直到这个固定的景致——岩石,钓竿,老人——看似和那冷冽碧绿的乌江水隔了一个世界之遥。
和乌江的水流相比,什么都显得缓慢了。在乌江的出口,即便那伟大的长江好像也停住了,它那泥泞的水流懒懒的,和那快速移动的支流形成对照。这两条江的水是迥异的,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条线,笔直,鲜明,好似地图上的分界线:长江是棕色的,乌江绿色,它们的相遇,好似两块釉彩玻璃被齐整地压在了一起,在白山坪陡峭的山顶下。
乌江乃是大山里的河。它从贵州起源,那儿山岭荒野,人迹罕见,而乌江向着东北,流入四川。在它的沿途,只有几座城市,无一大过涪陵,是以其流水可以保持碧绿清澈,直到它遇到了长江。乌江对于大型江船来说不够宽——许多地段,在枯水季节,只有十来米宽——而且也没什么理由吸引那些大船逆流而上的。即便在这儿,河东区的岸边,涪陵的城市中心就在河对面了,你望向上游,所见的是荒野陡峭的山岭,在远方。它们在河流上方的狭窄空间里挤作一团,那凹凸不平的蓝色形状,告诉你那乌江的上游是何等偏远荒凉。
所有的江河都有独特的个性,不变的特性,不在乎其长度,宽度,水流的速度。而涪陵这儿的两条江差别迥异,它们的对话只限于乌江河口的那色带。长江是人性化了——它被开辟成了航道,它被刺激,被导流灌溉,被建上了大坝;浮标标示在它的浅水区,而各种大小的船只在其被污染的浪头上涌动。它奔向上海。而乌江——清澈,翠绿,很少船只——从山中而来。一条江是关乎起源的,另一条,则关乎目的地:这就定义了它们的个性区别。长江,以其大小,其壮观,看似去向什么重要的地方,而乌江,以其狭窄的急流,看似从某个荒野神秘的地方而来;它那遥远模糊的山岭,暗示了其秘密将被一直保留。你可以在这里钓上一天,而乌江也不会给予你什么。
鲤鱼是一种慢水里的鱼,而它们是老人所期望的,这里还有其他八个渔人。他们分散在一条伸入河水的岩石上,他们的鱼线伸入一块较宁静的水域,这里,水位略微鼓起,而急流撞上岩石,溅起水花。“这里的鲤鱼可有一到八斤重,”老人说。“在城里,一斤要七八块钱,但我们不去卖,我们自己吃了。我也能抓到黑色的鲤鱼,但那是在更快的流域。这河里也有乌鱼——那是乌江里最好的鱼,但在河岸上可抓不到。那要卖二三十块一斤的!在夏天还有草鱼,但在夏天,鱼好钓,人太多了。”
渔人六十五岁了,他从一家重庆工厂退休已超过十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一件又脏又破的外套,因年龄背有些弯了。他们形成了对比,这一对形象——看上去脆弱的老人,和他那崭新闪亮的铝制鱼竿,有八英尺长。“这花了一百五十块,”他骄傲宣称。他抽着烟,和岸上所有其他男人一样,他身上隐约有些酒气。他谈到了另一种鱼,大概是河里最好的鱼,从没有人抓到过。他说了名字,但是他只说方言,而那词——有点像是鳝鱼——很难明白,他也不会写。无论如何,最棒的鱼经常是无名的。“那鱼非常罕见,非常好吃,”他说,“但我们的政府保护它。它要卖到100块一斤!如果你抓到了,没人看见,你可以走掉。如果有别人在场,你得把它扔回去。”他说话的态度严肃,好像是从一条法律中直接引述。他清清喉咙,一口吐在岩石上,然后继续顺着空空的鱼线,望向河中。
乌
乌的字形,有点类似一只鸟——顶上小小一点,一个四方的头,和一个弯弯的鸟嘴,一条直线代笔翅膀。和许多中国文字一样,它的形状反映了部分的含义:“乌鸦”。它的意思还有,黑,暗,可能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颜色,当暴雨云凝聚在河谷上方时,河水膨胀,成为愤怒的蓝黑色。
但在涪陵没人能肯定乌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颜色变化极快,而长江是恒久的棕色。在夏天,当雨水频繁,雪水融化了,鼓涨的乌江会流出平缓的棕色,它流入泥泞的长江时,难以相互区分。当枯水季节在秋季末开始了,江水由棕转灰,再到蓝绿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带,急流中刮出点白色浪花。
现在枯水季节过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几个星期,乌江一直流动着蓝绿的水。现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阳中泛光。越过那些老年的渔人,一排砂岩石堆积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对学生从一块石头跳去另一块,直至他们站到奔流中的一个石岛上。这是个美丽的景点,离江水那么近,脸上能感受到水流带起的冷风,江流从贵州一路往北带来的清凉。学生们在岩石上坐下,看着风景,听着江水。有一阵,在乌江的心脏处,除了流水顺畅的声音外,万籁俱寂。
学生的北边,一艘船停泊在岸边,靠近通往河东区的马路,五个男人在夕阳下,甲板上闲聊。他们的船有八十英尺长,甲板上一半空间为装有氧化铁的桶所占据。明天会有更多的货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结束了,男人们抽着香烟休息,看着日落。
不久,他们将前往江苏省的江阴市,长江下游一千英里处。他们将漂过三峡的崖壁,经过中国中部的低地与湖泊,然后,前往中国的远东。行程耗时七天。
“通常我们不会走那么远,”船主说。“通常我们去到湖南——我们把这些货物带到下游,再把矿长石带回到陶瓷厂。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时间。那里是毛主席的家乡,你知道么?我们通常会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个小时。没有,我没去过那儿。但湖南不错——比这里好。那儿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是。那里比较平一些——不像这里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国见过的大多数地方都比这里发达。”
这男人四十三岁,如果不和他说话,难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脏脏的灰色西装,脚套一双网球鞋,蹲在甲板上,抽着奇声香烟。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种,对涪陵老百姓来说的标准级别,四块一包。他的手很脏,肩膀宽阔强壮。他是个亲自动手的老板;他监督上货卸货,而他和其他八个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显,他跟其他男人很亲近,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说他们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不大情愿承认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种暗暗的敬意,当陌生人凑近来,大多数话是老板说的。
“有两个工人可以驾船,”他说。“我不行,但你得要有两个人——一个开船,一个休息。开船比开车难多了,你要知道。学会开车,只要两三个月时间,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准备考试。一个执照要花一万块。要花那么多钱,那么多的麻烦,因为一旦出了错,那是很危险的。
三峡不是很危险,如果你了解长江的话。当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来来去去那么多次了。这么多次航程后,它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