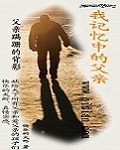消失中的江城-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一年的收入。他们还获得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奇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
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这些历史在脑中,我还是觉得人们对大坝漠不关心的态度值得关注。现在的人们较之从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个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国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提供教训,避免它们盲目的重现。然而,看起来,大坝与低地移民的命运不在普通市民的关心之内。一次孔老师和我上课间聊到大坝,我问他将来的变化是否让他忧虑。
“不,”他说,而且我看得出他觉得这问题好奇怪。
“那么,有什么人会担忧吗?”
他想了一会。“如果你是个移民,”他说,“那可能你会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注:我暂且不用个人主义一词)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
(关于这点,前些天HANS在卖奥运门票时也体验到。吃饭时,他很是抱怨了一番混乱场面。当时我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常年处于物质匮乏中,是以有一种生怕被甩下的不安全感。现在读了何伟的话,大概可以作为另一个补充。而何伟也许可以把我的理解当作他的补充。)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河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同样的本能,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消极观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人们形成一个社区,服务于个体,其结果就是,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应该帮助。当然,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发展到后来,在涪陵,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就会一群人出现了,聚集起动量来,逐渐膨胀,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偶尔,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吵架会升级,被观众驱动着,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戏愈演愈烈。
我为涪陵的群众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聚集在我身边。如果我在街上碰见一次吵架或者类似事件,而周围又聚了帮人,我肯定会停下观察。但通常,我观看群众的脸,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们的表情中,很难看出别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热切的看: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
群众如此反应的地方,在中国绝不仅限于涪陵一处。无数的作家,中国以及外国的,都曾经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以强烈的情绪和挫折感描绘了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社会,在同胞需要帮助时,人们置之不顾。我在我自己学生的写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们编写关于罗宾逊来中国的故事中。许多故事的主题都是罗宾逊盗窃腐败官员,但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乃是罗宾逊以行动助人,而群众消极围观。一个学生写道:
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扒手掏别人的钱。与此同时,他发现了那女人周围的人们也看到了扒手的动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们装作没有看见……
有那么多学生的故事描写了相似的场面,叫我震惊。而他们总是继续写到罗宾逊挺身帮助被群众抛弃的人——一个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开场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乌合之众围观。对我的学生们来说,罗宾逊的行为就是英雄主义了,在群众无所作为时有所行动,而他们将其抬升为了理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很少出现。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