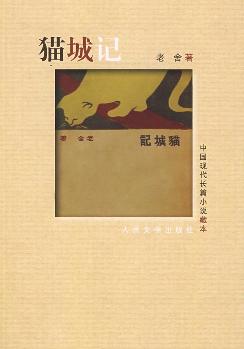神星城记-第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一样。旭垣对羽灵口中的故事抱着很浓厚的兴趣,不停地催问“后来呢”之类的话。而旭垣每一次这样问羽灵的时候,羽灵脸上就会涌溢着会心的笑容。
“后来呢?”旭垣问道,“公主找到他的心上人了么?”
“找到了——”羽灵的声音很小,“她找到了,她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就在——”
“哪里?”旭垣发现羽灵忽然沉默了。
“哪——”旭垣原本还想问,但是忽然间,羽灵倚在树干上的身子斜着倒了下来。羽灵的头轻轻地靠在了旭垣的肩上。
“喂,我说——”旭垣想把羽灵扶起坐好,他发现羽灵竟然是睡着了。但是就在他的手无意间触碰到羽灵脖颈的那一霎那,脑海中瞬时间像是有一道电流激过。
旭垣诧异地望着这张已然熟睡的脸——
我们见过么?
第四十五章 沉眠的梦
更新时间2009…11…20 16:35:54 字数:5243
三天后。
天高云淡。
深邃而悠远的蓝色,零星的几点白。旭垣仰望着怅阔的天幕,天空在他的视线中显示出一个优美的圆形弧度。他知道天与地相连的地方有一条分明的线,只不过现在这条线被周围的密林遮住了,难以看到。旭垣望着四周,最后把目光锁定在自己身旁的一颗巨大的榕树上。如果以一个人的年岁来形容这棵树的话,旭垣相信这棵树应该已经是树中的老者,但是老迈却不等于垂死。丰硕的枝叶,粗壮的树干,阳光从那厚重的枝叶之间传递着自己的光线。斑驳的影子落在地上,也投射在了那在树下沉睡着的人身上。
羽灵头枕在大榕树从土地中隆起的肥厚的根茎上。她黑色的头发一部分贴在脸上,一部分垂下与土地接触着。两道黑眉中间并没有完全舒展,看起来有一点哀愁的痕迹。双目微微闭着,眼角处还有一点浅浅的泪痕。沉睡中的羽灵嘴唇并没有完全地合上,一点点缝隙似乎在预示着她心中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她侧着身子,两条曲着的手臂一条压在另一条之上。被压着的那条手臂的手轻轻地攥着,而另一只手手指弯曲好像拉住了另一个人的手一样。她双膝微曲,彼此叠着,绿色的长裙铺在地上。旭垣从站着的角度俯视着沉睡的羽灵,觉得她的衣装将她打扮得就像一朵白色的花蕾。而且——
很奇怪的是,旭垣心里很清楚,羽灵比自己年长得多,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的睡容总是会让自己产生出一种想怜惜她的感觉。他记得就在羽灵刚刚睡下的时候,自己的脑海中一个怪异的念头一闪而过。他感觉自己对羽灵并不是那么陌生,虽说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对她的感觉,却又像很早很早以前便认识了一样。
他不知道羽灵为什么会突然间沉睡不醒,那时候他去问千仙婆婆,千仙婆婆说羽灵身上中了一种诅咒,她会沉睡就是这种诅咒产生作用的结果。
然后旭垣又问千仙婆婆,羽灵这样的沉睡会持续多久。千仙婆婆却说,想让她醒来,除非那个对她下了诅咒的人解除了诅咒。而至于那个下诅咒的人究竟何时才会解除那个诅咒,就是天意了。
旭垣回忆着千仙婆婆的话,忽然一阵风起,摇晃着榕树。旭垣看着枝叶在风中摆动,然后听见一个女子唤到他的名字,接着名字后面又添上了“师兄”二字。
旭垣转过身来,只见玫瑰站在那里。她火红的头发高高束起,绑着一条雪白色的丝带。白衣的衣领和袖口有一圈红色的滚边,一指来宽的红色腰带一侧系成了一只硕大的“蝴蝶”。旭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说:“我说过,你唤我名字便可以了,让你叫我师兄,你明明比我年长了很多。”
“可是,毕竟你拜千仙婆婆为师在先,”玫瑰的神情有些严肃,好像这是一件根本开不得玩笑的事情。旭垣看她对此事异常认真,自己倒是突然间产生了一种不敢“忤逆”她意思的想法。他晃了晃脑袋,觉得自己把这件事情想象得有些可怕。称呼罢了,其实自己也好,玫瑰也好,谁都没有必要那么执着的——
“我没有想到,你们会拜千仙婆婆为师,”旭垣说,玫瑰点了点头,说:“其实,在此之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玫瑰说自己会来到这里,原本只是随了越儿,是越儿要来这里找泪珍珠。但是没有料到,越儿找到泪珍珠之后便离开了此处。而她却和蔷薇风信子留了下来,居然成为了千仙婆婆的徒弟。虽然关于自己前世的事情,玫瑰都是从千仙婆婆那里听说的,自己对自己的前世没有任何记忆,但是这前后种种,总让她感觉到生命永远是处在一个转动的轮盘上,轮盘上的每一个格子都是一个出口。轮盘每一次的转动与停止,都意味着生命的下一次或迥异或相似的旅程。
“你找我,有事么?”旭垣问道,他相信玫瑰来到这里不是仅仅为了来唤他一声“师兄”的。
玫瑰点了点头,伸手指了指睡在树下的羽灵,说:“我想跟你说说她的事情。”
“羽灵么?”旭垣问,他很随意的就说出了这个名字。但是说完之后,他又再度产生了那种感觉,那种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仿佛曾经每时每刻都在念、每时每刻都在呼唤一样。
玫瑰说了声“是”,她想把羽灵与观叙之间的故事的后半段,也就是羽灵为了给观叙报仇而假装忘了过去的漫长的十五年里的事情讲给旭垣听。而在此之前,旭垣却并不知道,羽灵给他讲的正是羽灵自己与前世的他之间的故事。所以当玫瑰跟她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旭垣觉得异常的陌生。
他问观叙是谁。
玫瑰说自己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知道这个人是羽灵的恋人。
“他在什么地方,”旭垣问。他所想的是,羽灵此刻在这里因不明的诅咒沉睡着,她的恋人理应来到这里,照顾她,守护着她。
“他永远都不回来了,但是——”玫瑰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你也可以说,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旭垣有些听不明白,他听前一句时,觉得这个人好像是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正要为羽灵感到感伤时,玫瑰的后一句话,却又让他有些糊涂。
“她的恋人死于十五年前,”玫瑰说道,“她的恋人死了以后,她就不惜一切代价来到了敌人的住处,在那里一待就是十五年,为了就是给她的恋人报仇——”玫瑰说羽灵为了伪装,为了报仇,做了许许对多多原本没有失忆的人而言异常困难的事情。玫瑰说曾经有一次,在鬼城里,鬼城次主为了检验羽灵是否真的忘了归去,就命羽灵当着她的面活吞了两个精灵,而羽灵,不皱眉头地——
“我不明白,”旭垣脱口而出,话音刚落时,他忽然想起羽灵第一次见到他时,羽灵那悲戚的眼神,和她痛苦中闪映的笑容。记忆中羽灵那细腻的声音“你不记得我了”,渐渐的在他的脑海里变成了一串串连绵不断的回音。
旭垣诧异地回头,望向了沉睡的羽灵。他想,难道在此之前,我真的见过她么?难道那些熟悉的感觉,并不仅仅是感觉,我真的——
可是——
旭垣一只手按着额头,想从记忆的深处搜索着。但是在他的记忆中,父母、师父,所有熟知的人当中,真的没有羽灵的影子。他努力的回忆着,自己所有记忆的初始,回忆着记忆的开端,但是站在那里的却是自己的父母。
没有羽灵,难道自己在年幼,还没有办法记忆的时候曾经见过羽灵么?又或者,在他的生命之前见过——
想到这,他摇了摇头,他觉得那不可能。
他不相信人有前世来生。
但是过了一会儿,玫瑰告诉他说,羽灵这一生深爱着的恋人,羽灵十五年前死去的恋人,十五年来让羽灵为其报仇的恋人,此刻让羽灵心甘情愿去沉睡的恋人,就是他,旭垣。
一瞬间,真的只有短短的一瞬间,旭垣彻彻底底忘记了自己。
原来人世间,真正相连的恋人之间,爱情永远都不会消失掉。哪怕,我活着你却消失了,也没有关系。因为爱情会让我们重聚,只不过那时,我记得,你忘了。
羽灵的意识在一个不知名的空间里醒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己以前在夕极城皇宫里的那张大床上。她翻了个身子,却发现自己的枕边放了另外一个枕头。羽灵伸手摸了摸,发现那张枕头还温热着,而且枕头上还有几根掉下的短短的头发。
羽灵猛地坐起,但是坐起的同时发现自己身上衣衫不整。羽灵见状,立刻羞红了脸,慌忙将睡袍的一侧向另一边一拉,然后将腰带紧紧地系上了。
这是——
羽灵的脑海里一片混乱,她根本想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来帮助自己破解眼前这可以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形容的谜团。
“有人么?”羽灵喊了一声,她想看,自己这样喊一下,是否真的会有人来。如果真的有人来,那么自己就可以根据来着来判断一下眼前这个,让自己不知所云的环境了。
“你醒了么?”羽灵听到一点推门的声音,她猛地转过身去。视线中,只见观叙也穿着一件与自己身上一样的睡袍,朝床边走来。
羽灵吃惊地捂上了嘴巴,睁大的双目中,泪珠瞬间溢出,顺着她的手臂淌了下来。观叙好像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要询问,只见羽灵忽然擎起手臂,跪在床上紧紧地拥住了他。
如果可以,她想这样子,永远都不放手!
羽灵拥着观叙的手臂更加地紧了,嘴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观叙的名字。好像要将曾经逝去的岁月,曾经无法实现的团聚,那些被迫别离的岁月里所有的呼唤,完全倾诉。
“你怎么了,羽灵?”观叙也拥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发,“我们不过——”
“十五年,”羽灵哽咽着说了这三个字,没有前因的三个字。但是事实上,羽灵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里,而对观叙而言,其实他们只不过分别了很短很短,可能就是喝一杯水的时间而已。
观叙笑了笑,说:“羽灵,这可不太像你。以前你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连一句‘想我’都不怎么说,怎么今天——”
怎么才一会儿不见,就说像隔了十五年这么漫长?
观叙是这样理解羽灵“十五年”那三个字的,虽然对羽灵而言,他心中的伤痛的的确确是蔓延了十五年,但是似乎,观叙却不这样想。似乎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时空里,他们朝夕相对,从来就没有过分离。
“观叙,”羽灵搂着他的脖子,说,“对不起。”
“唔?”观叙想,羽灵越来越奇怪了。
“对不起,”羽灵声泪俱下,“我喜欢你,我明明一直都喜欢你,我明明就离不开你,却天天说着口是心非的,让你伤心的话语——”
“羽灵,”观叙松开她的怀抱,看到她一脸泪痕,紧张地问道,“你怎么了,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就——说这么多奇怪的话,你喜欢我,我一直都知道——”
羽灵没有说话,只是一双眼睛地望着他,呆呆地望着眼前的观叙。
“你,出什么事情了么?”观叙紧张的神色并没有消退,羽灵的目光没有从观叙的身上移走半分,过了很久,她因泪痕而有些干涸的脸上,浅浅地出现了一丝笑容。她说:“我好像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