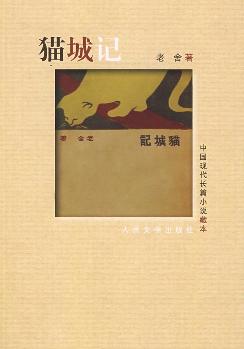神星城记-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记不清是多久,反正这种笑容真的是很久不见了。
观叙支起一只胳膊,看了一会儿羽灵的睡容,然后下床套上了衣服。
整理好衣服之后,他又站到了床边,他看到了羽灵拇指上的指环,很轻地把指环撸了下来,套在了自己的拇指上。
“羽灵,保重,”他低头吻了羽灵的额头,然后轻轻推开了房门,悄悄走了出去。
羽灵起床是一个时辰之后的事情。
但是醒来之后却不见观叙的踪影,她很难形容自己心情的复杂:观叙,真的是听了她的命令,走了,离开了这里吗?
掀开被子,床铺上连夺鲜红的蓓蕾静静绽放着。
自己已经把观叙最想要的东西给了他,而他——
羽灵但愿他会听自己的话。
但是事实证明,羽灵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她穿衣服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自己拇指上的指环不见了。她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把指环丢掉了,但是却四处都没有找到。她思索着若自己真的把指环弄丢了,往哪里寻找最有可能,可却百思没有结果。
正当她犹豫着,是否应该唤人来帮忙的时候,门“哗”的一声被推开,涟儿,确切点说,是转世前的涟儿跑了进来,看见羽灵神色泰然,不禁大叫道: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和观叙到底怎么了!”
羽灵被问得稀里糊涂,什么叫“她和观叙到底怎么了”,她刚想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又想起了昨夜的事情,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但是转世前的涟儿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仍径自大喊着:
“好端端的,你为什么要放弃城主之位?”话音刚落,十五年后的涟儿追着她前世的脚步到这里来了,当然,羽灵和前世的涟儿都是看不见她的。她看到屋子里只有羽灵一个人时,只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尚胡乱猜测时,羽灵伸出了自己那只原本带着指环的手,说道:“我的指环不见了。”
“你的城主之戒在观叙手里,他在大殿上告诉皇宫里的所有侍卫,说你已经退位,城主将由他接任,”前世的涟儿焦急地说着,“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城主之戒给了观叙啊?”
羽灵没有给自己回答的空闲,飞快地跑上了大殿。两个涟儿跟在她的身后,见此情景,一个比一个糊涂。
羽灵大喊着观叙的名字冲上了大殿,但是她没有想到观叙坐在大殿的深处,向左右侍卫半带着命令的语气说道:“现在我是夕极城的城主,那些已经过去的不作数的人或事,你们最好让他们立刻在我眼前消失,反正皇宫里的囚室都还空着,不妨都住到哪里去吧!”
观叙的弦外之音非常清楚,但是侍卫没有人敢动弹。虽然现在城主之戒套在了观叙的拇指上,但是谁也不敢忽视羽灵这样一个存在。所有的人都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城主之戒换了主人,而且这个人竟然是前城主的恋人(这在夕极城并不是什么秘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观叙,你这是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拿走羽灵的城主之戒,”前世的涟儿不解地问道,但是观叙的回答却是冷漠外加生硬:
“这是我夕极城的事情,与你这神物无关。”
偶然间的“神物”二字,让十五年后的涟儿一是想起了很多事情。她想起了在鸿江城波伦卡死后飘落到她手上的那张纸,想起了纸上的那如同诅咒般的语言——“只要有一天,你看到了传说中的神物,你将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斩杀”,再想起那段为了得到箫竹什么都不顾的、却总是被波伦卡百般看不顺眼的日子,细细想来,难道说,波伦卡总跟自己过不去,甚至死了以后还想要杀了她,真的是因为诅咒?又或者说,自己的前世会突然间变成一块紫色的大石头,倒在花丛里睡大觉,那块大石头其实便是一块神物,而转世成为现在的涟儿,所以现在的她,本质上也是神物?
“什么与我无关,”前世的涟儿响起了十五年后的她惯用的腔调,“我拿你和羽灵做朋友,你怎么这么没头没脑地说着糊话,再说了,你凭什么就要抢夺夕极城的城主之位,你又不是羽灵的什么人,根本不配做继承人!”
羽灵的脸在一瞬间红了。
“是么?”观叙翘起一条腿,手托着下巴,又晃了晃另一只手,故意显出了白绿相间的指环,嘲讽似地说道,“你觉得我该说你无知,还是可笑呢,如果我真的不是她的,”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用一只手随便指了下羽灵,“真的不是她的什么人,那这指环,我能把它套到我的拇指上吗?”
两个涟儿同时恍然大悟。
神星王国的城主继承之法,城主之戒是城主身份的象征,有城主之戒即被视为是一城之主。但是能戴上城主之戒的,只有城主之位的合法继承人:父母兄弟,妻子儿女。
换言之,羽灵和观叙已经结为夫妻了。
不然,城主之戒,观叙是没有办法戴上的。
可是,即便如此,令人不解的事情还是有很多。
观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径直走到了羽灵面前,用着只有两个人能够听到的声音,说道:“从今天起,你可以永远的休息了,我看过西极城皇宫的囚室,很好,很适合你。”
羽灵笑了一下,眼角挂着泪滴:
“你一点都不适合演戏。”
观叙心头一阵,唯恐羽灵在会说出什么意外的话语,用魔仙之力让她昏睡了。之后又命人把羽灵关进囚室,前世的涟儿——涟儿始终不知道自己前世叫什么名字——冲着观叙一番吵闹,却被观叙视为无理取闹。最麻烦的是,涟儿很紧张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样,偏偏这个时候,自己的眼皮又重重地垂了下来。就在自己快失去意识的时候,她模模糊糊听到观叙说“越兰石”什么的,但是她还没有完全听清,自己的意识就飘渺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涟儿,涟儿——”
“唔?”
自己分明很困倦,却非有人在这个时候推她,到底是谁这么不善解人意——
涟儿眯着眼睛,看见有个人影好像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她有气无力地抓了下那个影子,但是什么都没有抓到。
自己是在做梦吧。
那就接着睡好了。
涟儿又合上了眼皮,翻了个身,把脸转到了另一侧,说也奇怪,刚刚明明在皇宫大殿上的,怎么好好的就睡着了。她像自娱自乐似的躺着耸着肩膀,完全不顾周围的任何情况。欧利斯轻轻扯了下涟儿的耳朵,但涟儿仍不动声色,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迷迷糊糊地说着:
“谁也不告诉我,我到底叫什么,羽灵真是的,观叙也不好——”
无论对于欧利斯,还是对于梅妮,羽灵和观叙都是两个不陌生的名字,但是涟儿在这种情况下念出这两个人的名字,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奇怪了。欧利斯觉得自己再这样子干等着她起床,自己准会疯掉,便伸手用力把她拉了起来。
“醒了么,你是在做梦的吧?”欧利斯严肃地说着,事实上在涟儿方才睡着的那并不长的一段时间,欧利斯与梅妮听到了她长时间喋喋不休的令人费解的语言。
涟儿睁开眼睛,盯着欧利斯那张脸出乎意料地说了一句:
“你是谁啊?”
欧利斯没有思考,举起手就在她脑门上捶了一下。涟儿大声喊痛,欧利斯还是一脸严肃:
“醒了么,还在做梦?”
涟儿耷拉着脑袋,眼皮朝上地看了欧利斯一眼,神色异常疲倦: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丫头的脑袋准是出了故障,不然不会这么没头没脑地问这么个问题,虽说自己本质上是个大夫,但是不巧,脑筋坏掉了,他可是修理不好的。但是他也不想让眼前这个情形再稀里糊涂下去,抓起她那只紧紧握着毒镖的手——涟儿即使是在魂游异时空时,也没有把这只手松开——举到她自己眼前,结果涟儿一看到那支毒镖,飘忽的意识突然镇定下来,再一次将那毒镖夺了,不满意地说道:
“这是我的东西,你不可以拿走的。”
她的东西?欧利斯的脸僵硬得挤不出任何一种表情,这什么时候成了她的东西?如果自己没有记错的话,这支镖分明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怎么就成了她的东西?
“那不是你的东西,”欧利斯说着,但是涟儿不甘示弱,一下子从方才躺着的地上跳了起来,倔强道:“现在就是我的,我知道这上面有毒,而且是九子兰草毒,”说着,她又跑到梅妮面前,刚要开口,发现梅妮的双目有了些神色,不再那样无光,有点好奇,欲伸手证实一下自己那感觉有点荒唐的猜想,却见梅妮笑了笑,又说:
“我看得到你哦。”
涟儿吃了一惊,又回头看向了欧利斯,他猜准是欧利斯这个大夫趁着她不注意的时候治好了没你的眼睛,他果真不是什么好人,涟儿心里愤愤的,总觉得欧利斯趁自己“旅行”的时候做了什么别的事情。方才,自己“旅行”之前,梅妮还是一副拿他们当十世仇人的表情,现在,居然在笑——
涟儿轻轻走到欧利斯身边,贴着他的耳根小声问道:
“她怎么突然间就好了?”
欧利斯没有完全理解涟儿话的意思,就说:“那不是什么重伤,很容易治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涟儿的表情写满了自己的干着急和在她看来欧利斯的蠢,“我是说她怎么突然间,好像不把我们当成敌人了?”
“原本就不是什么敌人,”欧利斯很自然地说着,完全没有注意到涟儿恼火的样子,“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说着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说道,“你姐姐也认识她的,梅妮是精灵山峡的蜘蛛精,后来做了夕极城主的侍女。”
“是么?”涟儿狠命瞪了他一眼,然后又转向了梅妮,她想知道如果事情是这个样子,那梅妮一开始眼睛看不见的时候,又把他们当成谁了呢?
梅妮察觉到涟儿的疑问,就说:“我以为你们是十五年前那个坏女人派来的,是那个坏女人用你手上的镖,杀死观叙大人的。”
“她是谁?”涟儿问道,是谁杀死了观叙,也有可能杀害了师父?
“我听到了她的名字,她说她叫惠依兰,她从头发到脚上的靴子都是蓝色的,”梅妮说到这,又把目光转向了涟儿,她想起了涟儿方才的呓语,顿生几倍好奇,她问:
“你方才是做梦,做梦梦到了城主和观叙大人么?”
话虽如此,事实上在涟儿穿越时空之前,现在的涟儿根本没有见到过那两个人,她摇了摇头,但见梅妮的目光流露着更浓厚的好奇,她很神秘莫测地笑了一下,说:
“在此之前你见过我么?”
涟儿摇头。
“你今年多大?”梅妮又问。
“我十五年前出生的,”涟儿说,她很好奇梅妮为什么要问这些,梅妮说:“我方才能看到你时,便觉得有些意外,你长得很像城主的一个好朋友。”
“她叫什么名字?”涟儿结束时空旅行之前,隐隐听到“越兰石”三个字,但这三个字怎么听都不大像是一个人的名字。
“越兰石,”梅妮说道,“她是神星王国上古的神物,本体是一块拥有巨大能量的大石头,但是常常变成人的样子到处游玩,虽然她真实的年纪要比城主大得多,但是城主和观叙大人平时都叫她越儿,没办法,因为它变成的那个人的样子,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