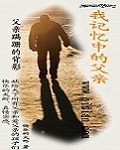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考虑一下,老太婆,是质量上乘的黑色丝绸。”
“穿着它为我的罪过。或者为我失去的农场哀伤!”
“十二码。”土地商毫不在乎她的反驳,继续说道,“一码一元,想一想,那将是去教堂的好衣服啊!”
“跟你一块儿见鬼去吧。我从不去教堂。”
“我早料到了,”土地商先生说,对我们挤挤眼睛,“好吧,亲爱的夫人,什么会使你满意呢?”
“给我二十块钱,我就干。”老太太回答道,还坐在她的摇椅里前后晃着。她的眼睛闪动着,她的手颤抖着,就好像她已经拿到了对她的心灵来说那么珍贵的钱。
“同意,”土地商说,“你什么时候进城?”
“星期二,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记着,我拿不到钱就决不签字。”
“别害怕,”土地商先生在我们退出房子的时候说。然后他转向我,以一种奇怪的微笑补充道:“这是一个魔鬼一样精明的女人,她都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律师。”
星期一到了,随之而来的是搬家的忙碌,而且又是个雨天;这是常见的情形,忙时天不睛。我毫不后悔地离开了老撒旦的家,很高兴,无论如何有了我自己的地方,不论它多么寒酸。我们的新住所尽管很小,可比我们原来的住所好得多。它建在一个缓坡上,一条窄窄的可爱的小溪从它的窗下静静地流过,小溪里有许多带斑点的鳟鱼。房子周围环绕着美丽的果树。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永不停息的小溪发出的丁冬声使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忧郁,它使我失去了许多个夜晚的安睡。我爱它,流水的声音、夜晚的寂静都在我心上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影响。流水永不停息的运动和永久的声响传递给我生命的意义——永恒的生命。看着流水闪闪流动,时而在阳光下,时而在树荫里,时而冲击着河中的石头,时而欢快地跳过它,我心中产生了十种神秘的敬畏,一种永远都无法完全摆脱的敬畏。
我精神的一部分似乎也流进了小溪,它深深的哭泣声和烦躁的叹息声在我看来是在为我永远离开了的土地悲伤。它对挡住了它去路的石头永不停止地猛烈撞击,与我自己在精神上同围困我的奇特命运做斗争相类似。白天,小溪叹息着向前流去,但是我忙于新的令人厌烦的各种事务,听不到它的声音。不过每当我长了翅膀的思绪飞回故乡时,小溪的声音便对着我的心低沉而悲伤地诉说。随着它的悲伤而又和谐的乐拍,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虽然空间很小,我还是在几个小时之内把我的新居收拾得比我先前那个舒适多了。这所房子所处的位置很美,它的环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大自然会,而且我希望,永远都会
“把神奇的力量注入我的心灵。”
只要我们对圣母有颗诚心,她也永远会对她受难的孩子们报以真诚。
那时候我对加拿大的爱是一种近乎于死囚对监牢的感情。死回想逃出牢房,惟一的希望只能是通过坟墓的门。
秋雨的季节已经来临。在很短的几天里,寒冷的秋雨便冲去树上华丽的紫红色,把一片阴冷凄凉的荒野呈现在瑟瑟发抖的观看者面前。但是尽管有雨有风,我的小屋却从未免受乔大伯的妻子儿一女们的烦扰。他们的房子和我们所住的小屋近在咫尺,就在同一块草地上,尽管我们的的确确已付过两倍的钱了,他们似乎还把小屋当成他们的。她们是些五岁至十四岁的健壮女孩,但是非常粗鲁,没有教养,和一伙子熊差不多。她们一点礼貌也没有就进入我家,那么小的人却要问上千个不相干的问题。而每当我客气地要求她们离开小屋时,她们会一字儿排在我门口的台阶上,黑眼睛从乱糟糟从没有梳过的头发后面盯着我,观察着我的活动。她们的来访令人烦恼,因为我不得不痛苦地限制我的思想,而沉思向来是我喜欢的习惯。他们的来访不是出于友爱,而仅仅出于一种无聊的好奇,夹杂着幸灾乐祸之心,为我学不好加拿大的持家之道而高兴。
一个星期以来,我独自一人,因为我的苏格兰女仆离开我去看她父亲了。有些婴儿的用品需要洗,在做了很好的准备之后,我决定用我并不娴熟的手洗它们。事实上,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项非得自己干的活。在几分钟的时伺里,我把手腕上的肉皮都搓抖了,可并没有把衣服洗干净。
同往常一样,门是开着的。即使是在冬天最冷的日子,为了让更多的光线照进来,把烟雾放出去,也一样开着,否则烟雾就像云雾一样包围我们。我是那么忙,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被一双冷漠严肃的深色眼睛盯着。那是乔太太,她带着轻蔑,笑着叫嚷;
“好啊,我很高兴看到你终于自己动手干了。我希望你得和我一样卖力地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应该整天静坐着,像一个贵妇人一样,而我却不能。你并不比我强啊!”
“你啊,”我说,对她的出现有些生气,“我坐着也好,工作也好,与你有何相干?我从不干涉你的事,如果你想整天躺在床上,我一点也不想麻烦自己去管你。”
“啊。我想你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同胞。你太骄傲、太自大了。我想你们英国人不像我们一样有血肉之躯,你们不和你们的帮手同桌吃饭。我想,我们认为他们比你们强。”
“当然,”我说,“他们比我们更适合于你。他们没受过教育,你也没有。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教育会使你对那些有长处的人稍示尊敬。但是,你称为帮手的人都很顺从,肯帮忙,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坏话。如果他们忘了他们的职责,我就会命令他们离开我家。”
“噢,我知道你会做什么,”这位无礼的夫人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是你的帮手,你会叫我离开你的房子。但是,我是一个出身自由的美国人,我不会听你的命令走开。别以为我来这里是出于对你的好意”。不十我恨你们所有的人。我很高兴看到你坐在洗衣桶边,我还希望你跪在地上擦地板。”
这番话只引来了我的一丝微笑,然而我的内心感到了伤害。我惊奇的是我从未做什么得罪这女人的事,她却如此怨恨我。
傍晚的时候,她打发了她的两个孩子来借“长熨斗”——她对意大利熨斗的称呼。我正哄我的孩子入睡,坐在火炉边的矮凳上。我指着架子上的熨斗叫那个女孩去拿。她拿了过来,却站在我旁边,毫不在意地握着熨斗,盯着刚刚在我腿上入睡的孩子。
刹那时,重重地熨斗从她松开的手上落了下来,砸到我的膝和脚上,看见离孩子的头那么近,我吓得喊出了声。
“我猜差点砸了孩子的头,”阿曼达小姐说,没有一点歉意,只有极大的冷漠。阿蒙少爷大笑起来:“如果砸着了,曼迪,我想我们就够受了。”我被他们的无礼所激怒,告诉他们离开我家。我泪眼汪汪,因为我敢肯定,即使他们伤了孩子,他们也不会有半点的懊悔。
第二天,当我们站在门口的时候,我丈夫被看到的情景逗乐了。乔大伯在房前的草地上追赶捣蛋的阿蒙。乔上气不接下气,像蒸汽机一样喘着粗气。他的脸因为兴奋和激动而变成了深红色。
“你这小无赖!”他叫道,差点因愤怒而窒息,“我要是抓住了你,会剥了你的皮。”
“你这老无赖,你要能抓到我,可以剥了我的皮。”那早熟的孩子一面跳上高高的栅栏顶,一面握紧拳头,以威胁的方式对他父亲说
“这孩子越变越坏了,”乔大伯说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们走来,汗珠从他的脸上往下淌,“该管管他了,否则,他会成为我的老爷的。”
“你早该开始了,”穆迪说,“看起来他倒像个可教的学生。”
“噢,至于说到这一点,骂人是有男子气的,”那父亲回答说,“我知道我也骂人,那么老公鸡会打鸣,小公鸡也会的。我在乎的不是他的骂人,而是他不按我说的做。”
“骂人是一种可伯的恶习,”我说,“从成人的口中说出已够邪恶的了,如果是孩子,那就更令人吃惊。如果说他从小对上帝不怀敬畏,那是很痛苦的。”
“呸,呸,那是假话。骂几句没什么害处,要是不骂人我就无法赶牛马。我敢说,在你们生气的时候,你们也会骂人的,只是你们太狡猾,不让我们听到罢了。”
我对这个假设禁不住好笑,但还是平静地回答说:“那些有这种恶习的人从不自找麻烦去隐藏它们。隐藏表明了一种羞耻感。当人们对他们的罪恶有了感觉,他们就走向改进之路了。”那个男人打着口哨走开了,而那个邪恶的孩子没有受惩罚就回了家。
下一刻那位老太太又进来了。“我猜你能给我一块绸子做头巾,”她说,“天气变得相当冷了。”
“肯定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冷,”我说着让她坐在了火炉旁的摇椅里。
“等一等,你一点也不了解加拿大的冬天。这仅是十一月份,在圣诞节过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冷。我和我丈夫离开合——众——国已三十七年。那年叫做寒冬年,我告诉你,女人,那雪落在地上有那么厚,封住了所有的道路。只要我们高兴,我们就可架着一辆雪橇从篱笆顶上滑过去。所以砍掉了树的土地便成了一片宽广的白色平原。那是个荒年,我们半饿着肚子,但是寒冷更糟糕,因为缺乏物资供应。我们走了漫长艰苦的历程,但是那时候我年轻,对困难和疲乏都很习惯。我丈夫一心效忠英国政府,他真傻。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我的心只相信事实。但是,他父亲是个英国人,他说:‘我要在父辈们的旗帜下生和死。’因此,他把我从舒适的火炉边拉出来到遥远的加拿大荒野上寻找一个家园。麻烦!我猜想你以为你有麻烦,但与我的麻烦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她停了下来,吸了一撮鼻烟,把盒子递给我,痛苦地叹了口气,用那块红色大方巾在她又高又窄、布满皱纹的眉尖擦来擦去,继续说道:“乔那时还是个婴孩,我怀里还抱着另一个无依无靠的生命——一个养女,我妹妹生她时死了。我就用奶我儿子的奶喂她。唉!我们驾牛车走了四百英里。这牛车带着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所有的家当。我们基本上是从森林中走过,我们走得很慢。懊,当我们到达那块潮湿的林子——现在罗彻斯特城矗立在那儿——的那个夜晚是多么寒冷啊!牛身上都是冰柱,它们呼出的是气雾。‘内森,’我对我丈夫说,‘你得停下来点堆火,我都快冻死了,恐怕孩子都冻僵了。’我们开始寻找一块能宿营的地方,突然我看到林子里有一点亮光。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简陋小屋,住着两个法国伐木工人。这两个人和蔼可亲,他们用雪搓着我们冻僵的四肢,并把他们的·晚饭和水牛皮分给我们共享。就在我们那天晚上宿营的那个地方,就在我们只听到风吹着树木的飒飒声、还有小溪流水声的那个地方,现在建成了那座大城市——罗彻斯特。两年前我去过那儿,去参加一个兄弟的葬礼。我觉得真像是一场梦。我们曾在简陋的小木屋的火炉边给我们的牲口喂草,那地方现在矗立着这个城市最大的旅馆。我丈夫离开了那么好的一块发展之地,却到这儿挨饿。”
我对老太太的叙述非常感兴趣,因为她的确拥有非凡的能力,而且,尽管粗鲁没有教养,但如果换了环境会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