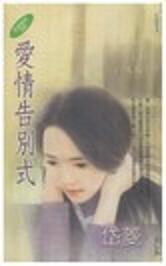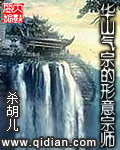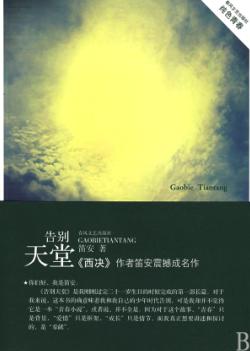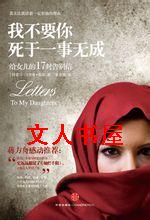告别虚伪的形式-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在边缘处叙事(3)
在此,韩东、鲁羊、刘剑波等作家的“诗人化”的经验构成了新生代小说“私人化”景观的一个层面,而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新生代女作家对女性“个人化”经验的言说则代表了“私人化”景观的另一个层面。而我们今天所讲的新生代小说的私人化问题其实主要是针对女性作家的文本而言的。陈染从《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等中短篇小说到长篇新作《私人生活》,都以一种近乎“呓语”式的内心独白体对女性的私人隐秘体验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表现。林白在她的《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等小说中对于女性同性恋、自恋、恋父等尖锐而“边缘性”女性经验的言说可谓率直而大胆,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则更是在一种“自传式”的氛围中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一个女人成长历程中个别的、个人的铭心刻骨的记忆,并由此把女性的奇特经验渲染到了极至。有人甚至认为她们就是依照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克苏的“身体写作”原则来写作的,“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继而将是率直的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这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① 我觉得,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对于隐秘的女性意识、女性欲望、女性躯体等的言说和体认既彻底地呈现了那些被遮蔽的女性经验,又在对于女性这个神秘领地的真正打开中实现了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敞开。实际上,无论是“欲望化经验”还是“私人化经验”,在新生代作家这里都只是寻找和发现生活与存在无限可能性的一种有效的艺术手段。对于“经验”的强调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内缩和封闭的姿态,但实质上却是以一种私人化的方式延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可以说,私人性和经验性正是“存在”的可能性得以凸现的前提,因为生活的可能性既包容了个体的可能性,又只有在个体的可能性身上才能体现出来。韩东是新生代作家中对于存在可能性的表现最专注和突出的一个。虽然韩东把他的小说称为“虚构小说”,但这种“虚构”却又是与“生活”和“经验”紧紧相连的,他表示:“我赞成小说家的写作有赖于他的生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生活的理解,甚至就是对于‘生活’这一词语的理解。由于对‘生活’的不同理解产生了对小说家的不同要求,他们的作品因此面貌也迥然有别。”同时,他又觉得虚构小说面对的是“生活的可能性”,他相信“以人为主体的生活,它的本质、它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并不在于其零星实现的有限部分,而在于它那多种的压抑或无限的可能性” ① 。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把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那种“被湮灭和潜在的可能性”挖掘和呈示出来。无论是表现知青和下放生活的《西天上》、《田园》、《下放地》等具有童年记忆色彩的小说对于历史反本质化的日常性、具体性和细节性的叙述,还是描写充满“自传”意味的校园和诗人生活的《反标》、《同窗共读》、《三人行》等小说在生活的现行逻辑秩序内开拓出“反逻辑”可能性的艺术尝试,抑或在表现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房间与风景》、《于八十岁自杀》、《吃点心,就白酒》等小说中对各种不同人物“关系”的透视与剥离,韩东在对他自我个人化经验的理性叙述和呈现中所完成的正是对于生活和文本可能性的双重建构。
其二,哲学化主题的生命性。我不同意所谓新生代作家对于“经验”的强调导致的只是平面化叙述和深度主题丧失的观点,相反,我觉得新生代作家正是在“经验”的帮助下才真正完成了对于八十年代新潮小说哲学化主题的重构与超越。新生代作家显然并不满足于对生活和现实表象的书写,相反,他们倒是时常在他们的文本中表现出了穿越生存表象而直抵生存本真的愿望,这也使得他们的小说对人类生存的关怀总是透发出一种浓重的哲学意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陈染、鲁羊等新生代作家的价值其实正体现在他们对于“存在”进行哲学思索的巨大深度上,离开了对其文本哲学化主题的确认,我们对他们的把握将是片面而不得要领的。不过,不同于八十年代新潮作家的地方在于,鲁羊、陈染等人的哲学性主题不是观念性而是体验性的。他们的小说总是充满一种真实的生存痛感,他们以个体生命经验的方式切入对于存在的哲学追问,根本上超越了前期新潮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派理念的观念性认同、趋附与模仿,从而赋予了其哲学主题以强烈的生命性和真实性。陈染是当今作家中对于个人化的风格追求最绝对的一个,她宣称:“我以为,在人性的层面上,恰恰是这种公共的人才是被抑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他才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性的。……我想,应该说,恰恰是最个人的才是最人类的。” ① 在她充满女性自我经验的小说中,对于人类生存之痛的抚摸与言说是尖锐而触目惊心的。她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她所体验和感受的全部生命之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努力做到的就是“让那些应该属于我的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血血肉肉真实起来,把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 ② 无论是《空的窗》、《时光与牢笼》、《无处告别》、《潜性逸事》等小说对于“孤独之痛”的表现,还是《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饥饿的口袋》等小说对于“家园之痛”的体认,抑或在新近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中对于女性成长史的回顾,陈染都赋予其对于“存在”的哲学思索以鲜明的生命性和体验性。某种意义上,现实世界中的陈染和小说世界中那些陈染的创造物是有着互文性、同构性和互为阐释的生命关系。这也是陈染的小说卓尔不群的个人风格的一个主要方面。而鲁羊的小说在新生代作家中则是技术实验色彩最浓的,同时他对于存在的把握和表现也是相当哲学化的,他认为“小说可能是写作者融入梦想和智力的某种精神综合体,是否要借助于外部形状和故事情节的描述,只不过是此刻的考虑” ③ 。他的小说通常由“现实文本”和“梦的文本”共同构成,作家以“冥想”的方式对存在和人生加以审视。他的小说主人公也都是终极意义上的冥想者,冥想是他们的基本的人生存在方式,他们不仅在冥想中泯灭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实现了对于世俗的弃绝与抛弃,而且还以对存在的恒常性的体认构筑了存在和小说本身。但对于鲁羊来说,他对于存在的思考是和他的人生经验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的《银色老虎》等技术化、哲学化色彩很浓厚的小说就我所知都融入了大量的真实生活经验。在鲁羊这里,甚至形式策略的选择体现的恰恰也是他自身经验的生动展开。即便是《 酌》、《九三年的后半夜》、《岩中花树》这样一些呈现形式极端化外观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作家本人的生命轨迹和情感印迹。这些小说中呈现出的作家本人对疼痛的经验的敏感以及对于自身精神痛苦的抚摸都与作为诗人的鲁羊的悲悯情怀互为因果。与鲁羊等新生代作家不同,朱文、何顿、邱华栋等人的小说似乎更具有感性化和表象化的外观。朱文的小说总是具有一种情绪化的抒情外壳,但即使在他的《我爱美元》这样直接书写欲望的小说里,我们也能够从文本“反讽”的叙述基调中感受和触摸作家思索人类生存困境的哲学之思。而张的《校园情结》等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意淫”心理经验虚拟化的表现,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何顿的《无所谓》等小说对于城市多余人、空心人、流浪者放荡漂泊的欲望化生存表象的白描,也都在具有强烈现实感和经验性的人生画面中触摸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的痛楚,让读者看到了深受挤压的现代人生命存在的盲目、无聊、焦虑、厌倦及其卑微的本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新生代小说文本中的“经验”性的强调更多的是为了凸现新生代作家写作方式的意义,我们不能把文本中的“经验”和作家本人的“经验”完全等同起来。更不能以文本中的“经验”来反证和指控作家本人的生活态度。这本是一个基本的文学常识,但遗憾的是,目前文学界对新生代小说的种种责难却正是由这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引起的。新生代小说确实对于纯粹私人化、边缘化的心理、生理经验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也确实对于种种欲望化的人生场景和人生画面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新生代小说的主人公也无疑都是些远离公众生活轨道放浪形骸的游荡者和漂泊者,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新生代作家本人就没有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关怀,也不足以指责新生代作家就是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欲望主义者和价值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我觉得新生代小说对于“经验”的书写,对于欲望化生存表象的书写并不是一种对现实的平面化的复制而是一种有深度的超越。新生代小说是以自我体认的方式完成了对于我们当下时代欲望化生存景象和欲望化精神心理氛围的生动观照,他们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我们时代里真实存在的人生景观。小说中“我”的率真、坦直的表白与表演并不是作家本人的“自传”,即使是“自传”,当其出现于小说中时它也已具有了虚构的意义。主人公、叙述者的游戏人生也好,欲望舞蹈也好,都不是作家精神的写真。实际上,虽然新生代小说家把我们时代精神沉沦、家园迷失的“废墟”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但作家们却是有着自己鲜明的精神立场和诗性立场的。“遥望废墟中的家园”可以说是新生代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叙事形象。而在世俗的生存之痛的体认中向往超世俗的诗性理想,可以说是新生代小说的共同主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评论界对新生代作家“缺乏精神高度”的批评恰恰是空洞、非分而不切实际的。什么是“精神高度”呢?以语言的方式或者以口号、宣言的方式直接在作品中呼唤价值、信仰、道德等“精神高度”实在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但那根本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它既不表明言说者就是这些“精神”的拥有者,也不能为作品在艺术上平添多少光彩,相反倒有可能因为“虚伪”而放弃了诚实。如果那样,新生代作家就不成其为新生代作家了,因为,“诚实”恰恰是新生代作家最可爱的品格。我们不能因为作家没有在文本中表现义愤填膺的呐喊、悲剧性的哭泣和正面的价值评判,就否定作家主体的精神性,也不能把文本表层的轻松、调侃、反讽、荒诞风格等同于作家心态的轻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