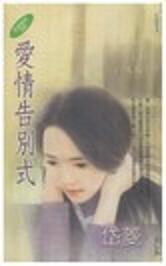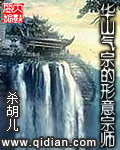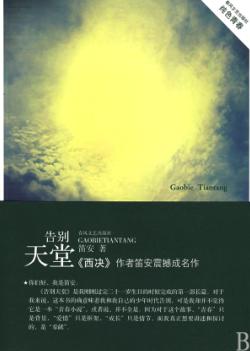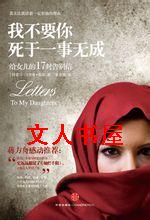告别虚伪的形式-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连副棺材都没有。”老许不仅对儿子杀死文医生没有一丝愧疚,反而偷了他的大烟膏,并连“我”也不放过,拉下大烟坡卖了。在老许这里,人类的贪婪、无耻和两面三刀的恶行得到了充分的放大。当文医生在时,他对“我”说:“夕阳可真是漂亮啊,它是我见过的最通人性的狗!”但文医生一死,他立即原形毕露,又踢又骂:“你个丑八怪,怎么走路跟扭秧歌似的,走两步要退一步?”与这种显在的恶行相比,人类的隐藏的罪恶则更为可怕,文医生的遭遇、许达宽几十年前的罪行、梅主人父亲的惨死可以说都是对于人类的所谓人道主义的绝妙讽刺。而欺骗、谎言和各种各样的“表演”则早已成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小说最后电影队的拍电影的情节无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象征了人类爱好“表演”的本性,陈兽医为在电影中出现一个镜头的不知羞耻,正是人类集体性面孔的一个素描。不幸,人类在演戏的时候,还不忘找一个垫背的“牺牲品”,“我”在拍电影过程中的死去,正是人类“谋杀”本能的一次辉煌表演。
《穿过云层的晴朗》就这样以一条通灵的“狗”烛照出了人世的黑暗与险恶,作家以狗的命运隐喻人的命运,以“狗道”反思“人道”,以“狗道主义”完成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虽然总体上这是一部充满温情和感伤的小说,然而在这种温暖和感伤背后,作家不动声色地对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却是深刻有力、振聋发聩的。
第六章狗道与人道(3)
三 “残酷美学”与文化诗情
《穿过云层的晴朗》是一部贯穿了伤感和绝望情绪的小说,叙事者阿黄表达了对自身命运和人类世界的双重绝望。一条条狗的悲剧与狗的几个主人的悲剧互为映照,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人生、现实与历史的残酷。但是小说又不正面去展示、渲染和放大狗与人的“伤口”,而是以抒情和感伤的叙述,把“残酷”改写为一种笼罩性的精神氛围和精神背景,占据小说表层的仍是日常化的世俗生活,甚至对“文革”这样的历史灾难的反思与批判在小说中也都被推到了幕后。这体现了迟子建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她追求的是对于“残酷”的日常化营构,是对于“残酷”的体验与反思,她要表达的是“残酷”背后的美感和诗意,是“残酷”的美学化和形而上化。对这种“残酷美学”迟子建自己有着清晰的感悟,她说:“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完全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当然,我并不是想抹杀历史的沉重和压抑,不想让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文革’在我笔下悄然隐去其残酷性。我只是想说,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 ’。” ① 可以说,正是“残酷美学”赋予了这部小说奇异的艺术品格,借助于作家对感伤的基调、文化的诗情、世俗的人生、神秘的氛围的互渗与融合,小说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力量与艺术力量。
小说的叙事魅力首先来自于叙事主体———阿黄九死一生的传奇性经历,以及它对这种经历抒情性的回忆、过滤与净化。它是一条多愁善感的狗,又是一条爱做梦、爱联想的敏感自尊的狗,同时还是一条有着浪漫情怀和通灵禀性的狗。它虽然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但在小说中它却早已看破红尘、洞穿世界和人事的本质了。正因为这样,它的叙述没有了浮躁、愤怒和偏执,而是呈现为一种难得的超然与宁静,它的忧伤、回忆和思念都是一种自我涅 与自我救赎。它最后的死已经不是苦难,而是成了一种精神超度的仪式。迟子建所信奉的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在这条狗身上可以说是绽放出了璀璨的艺术火花。
其次,小说的魅力还来自于作家在生活的日常性、世俗性与诗性和神性之间所建构的奇妙张力。小说有广阔的时间与空间跨度,涉及了众多的人物、场景与故事,虽然整体的世界图景是一种日常化和世俗化的景观,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在日常性的描写中灌注进文化诗情。小说有两个形象系列:以狗为代表的动物形象系列和以“我”的六个主人为代表的人的形象系列。在前一个系列中,狗、鹿、白马、野鸭都是充满灵性和神性的形象,而文医生给“我”取的名字“夕阳”更是诗性盎然;后一个系列中,乌玛尼、梅红、小花巾、文医生、大丫都是具有浪漫和诗性气质的人物,尽管“他们死的死散的散了”,但在黑暗的人世里,他们无疑代表了穿破“云层”的那一束“晴朗”光亮。与这两个系列相对应,小说中的“自然”则更是诗情和美感的化身。作为“俗事”的一种对照,“自然”是神奇而又美好的,丛林、飞雪、落叶、大河、湖泊、松林、星星、云彩,它们都有生命和灵性,与叙事主体阿黄有着源自灵魂深处的沟通与呼应,并作为一种独立的形象参与了小说主题的营构。即使在“人世”的社会层面的呈现上,作家也没有让世俗的灰尘完全遮去诗情的光辉。对放排、月亮节等民间文化风情的捕捉是作家挖掘日常生活背后诗情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在这些方面,小说对一幕幕东北民间风俗画的描绘确实很得萧红的神韵。最后,通灵而凄楚的语言也是小说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有很强的情感震撼力,这种震撼力既与小说叙事主体———阿黄以及它的主人们的悲惨命运有关,又更直接来自于它的诗意而敏感的抒情性语言。比如,小说叙述文医生惨死的那段文字,就至情至性有着催人泪下的力量,这里的语言可以说把凄楚的美感和毁灭的诗意表现到了极限。
我抬头望天上的云。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云彩,好几朵白云连成一片,一朵比一朵大,最大的那朵云像牛,居中的像羊,最小朵的像鹅。我感觉是牛带着羊,羊又领着鹅在回家。我想看看它们最终会在哪里消失,就知道它们天上的家在哪个位置了。正当我观察云彩时,突然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响“砰———”,我扭头一看,只见水缸举着枪,正对着湖心。而我的主人,他已经平躺在湖面上了!他游泳时从来不用这姿势,我猜水缸是把他当野鸭给打中了:我跳下湖,奔向我的主人!他虽然在漂动,但我知道那是水在推着他动,他的四肢不动了,胸前涌出一汪一汪的血水。他睁着眼睛,微微张着嘴,好像还想看看天上的白云,还想和谁说点什么似的。我知道他这是死了,我悲伤极了!没人看见我的泪水,它们全都落入湖水中了。我试图把他推上岸,但努力几次都不成功,我就想该回小木屋求助老许。水缸我是指望不了的,他开过枪后,一直呆呆地坐在湖畔,目光直直地望着湖水。在这里,情与景、人与物、动与静、描写与叙述全都被笼罩在悲情的语调里,汉语的表意与抒情功能、汉语的特殊的美感无疑被发挥到了极致,真是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句子都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样令人感动的语言境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已是很罕见了,但在《穿过云层的晴朗》这部长篇小说中却比比皆是,例如,小说写梅主人死的文字,写狍子、芹菜和十三岁被杀的文字,写白马累死的文字,等等,就都同样是既放射着艺术的光芒,又洋溢着浓得化不开诗情的美文。在我看来,《穿过云层的晴朗》的语言魅力和语言成就,既是迟子建卓尔不群的语言理想和语言追求的体现,同时也是她非凡的语言功底和语言能力的证明。更重要的是,对迟子建来说,这样的语言境界似乎也并不是刻意雕琢而成的,仿佛就是一种“日常生活”,她的语言总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这就是迟子建,只要她一开口,她的“口语”就已经是艺术化的了,就已经进入一种“境界”了。没办法,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天分吧。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3期)
第六章“符号”的悲剧(1)
———评艾伟的长篇新作《爱人同志》
尽管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与苏童、余华等八十年代成名的新潮作家的长篇小说无论在艺术含量、思想含量,还是受社会关注的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应该说,曾维浩的《弑父》、东西的《耳光响亮》、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李洱的《花腔》等长篇文本的面世还是以其新颖的艺术质地为新生代作家赢得了荣誉。在这方面,我觉得,艾伟的长篇新作《爱人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又是一部能够证明新生代作家艺术能力和艺术实力的作品。这部小说不仅显示了新生代作家艺术上的独特气质,而且在思想深度以及精神、情感的震撼力上也达到了令人信服的高度。小说既没有复杂的故事,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但是却以不长的篇幅、单纯的视角,完成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变迁和精神变迁的独特阐释,其对于人与世界、人与时代关系的独特解读,对于爱情、人性、英雄等时代性词汇的解构,都赋予小说一种罕见的力量和深度。
一 爱人+同志:爱情是怎么变质的?
在我看来,《爱人同志》的艺术力量首先就来自于小说独特的“爱情”描写以及对“爱情”崩溃、变质过程令人心悸的深刻揭示。题目“爱人同志”本身就体现了小说所表现的“爱情”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称谓,“爱人”体现为一种情感关系,“同志”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爱人”和“同志”的身份重叠,既可以证明“爱情”的高尚性、崇高性,又可以暗指这种“爱情”背后的政治、时代、社会或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时也隐喻了这种“爱情”的杂糅、混合质地与矛盾走向。应该说,女中专生张小影和残疾军人刘亚军的爱情最初是非常纯粹的。她想做的只是刘亚军的“爱人”而不是“同志”。甚至,这种爱情的发生还不乏一种古典“英雄美人”的意味和“一见钟情”的色彩,她“迷恋”他的声音和眼睛,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她觉得他很可怜很可怜,从那时起她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她觉得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件简单而普通不过的事情,也就是说她喜欢上了他。没有更多的理由。”而刘亚军对爱情的最初态度也是矛盾甚至拒绝的。他对张小影的辱骂和厮打,既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的心情反复无常,同时他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他的反复无常可以说正是他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同时也与他对张小影和这段爱情的“珍视”和“看重”有关,他既渴望被爱,又不愿张小影因他受苦受累。他的矛盾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们爱情的纯粹性。
但是,这种爱情的悲剧性又几乎是天生注定的。本质上,爱情是一种私人性、私秘性的行为,然而张小影、刘亚军却生不逢时。他们的爱情从诞生的那一刻就脱离私人性而成了一种公共性的行为。他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被公共空间取代。爱情也很快由他们个人的需要变成了时代的需要、官方的需要和公共的需要。正如接待张小影父亲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