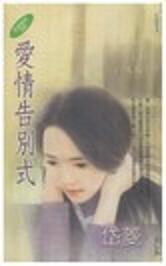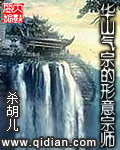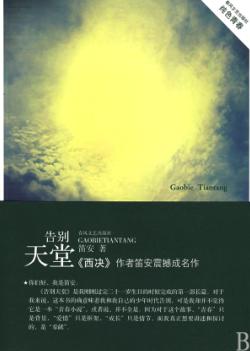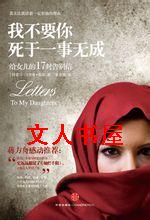告别虚伪的形式-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疤ǎ闪诵∷档闹魈濉U庖彩沟谩吨泄痪盼迤摺吩诙浴罢媸敌浴钡睦斫庥胗股铣搅苏窝Ш屠费б庖澹哂辛送耆娜搜б庖濉P∷等妨⒘肆教蹙裣咚鳎惶跸咚魇亲晕曳纯挂磐恼秸灰惶跏堑赖侣桌碛胝温桌淼恼秸U峭ü饬教跸咚鳎骷野涯闼牢一畹恼味氛肜吩帜阎没怀闪烁鋈俗晕伊榛甑牟芬约暗赖律窕坝胝翁傻慕狭俊P∷刀哉斡肜贩此嫉摹昂甏笮鹗隆北磺擅睢靶谩保诵陨笪视氲赖律笪试蛉〈闻杏肜放谐闪诵∷档摹案鋈诵鹗隆薄S肫渌担∷捣此嫉氖钦魏屠返谋纾蝗缢底骷曳此嫉氖恰叭恕钡谋纭⒅斗肿拥谋纾侵斗肿拥娜烁瘛⒆宰鸨慌で⒈湫魏椭鞫で⒅鞫湫蔚谋纭T谡飧鲆庖迳希∷档恼问泛屠返募壑狄丫耆梦挥诹硕杂谥斗肿有牧槭泛途袷返慕馄省T谧骷业睦砟钪校返脑帜岩埠茫蔚脑帜岩埠茫荡┝巳匀恢皇恰叭恕钡脑帜选!叭恕奔仁钦庵掷泛驼卧帜训某惺苷撸持殖潭壬弦餐钦庵终斡肜吩帜训牟斡胝哂胫葱姓摺T谛∷抵校颐强吹秸侵斗肿幼陨淼娜醯阋约叭诵缘牟兴鸺泳缌苏魏屠吩帜训目崃页潭取T贙大如果没有范宜春的卑鄙与奸诈,至少冯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卷入这场政治的灾难;在我乐岭如果没有张克楠这样阴险、无耻的知识分子败类,李戍孟、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悲剧也不会那么惨烈。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刚正不阿、铮铮铁骨,那么你就很难想象知识分子的灾难会如此迅速如此大面积地扩散与弥漫。而这也是这部小说在政治与历史反思中最为深刻和尖锐的地方,它真正击中了知识分子最为脆弱的部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和“政治”并不是这部小说反思的艺术目标,小说反思的惟一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所有的“历史”、“政治”的画面都毫无例外地经过了心灵的过滤,变成了“心灵的风景”。
第五章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2)
三 “人”的失败与“艺术”的胜利
某种意义上,小说对于人心、人性开掘的深度其实也就代表了小说的深度。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的人性力量、美学力量与思想力量的根源。也许与小说对“历史”、“政治”反思的人学视野有关,尤凤伟在这部小说中大展宏图,一气刻画了不下五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每个人物虽都着墨不多,而且作家使用的也是散点式随机性的笔墨,但每个人物却都个性鲜明具有艺术的自足性。对作家来说,这既是才华与能力的体现,同时也隐含着更深刻的艺术意图。人物的众多以及面目的各异,其实正是为了寓言那场历史灾难的普遍性,是为了突出在那个政治与历史语境中人本身的渺小与无奈。这样,每一个人物既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又超越自身而成了整体的“类”的一个部分,他们分散在小说的时空中,其实构成的正是一个总体的普遍性的象征,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喻。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一九五七》与其说是想建构一个历史与政治的寓言大厦,还不如说是为了建构一个特殊语境中的“人性博物馆”。而这也正是尤凤伟以“个人叙事”的方式达到“宏大叙事”效果的又一例证。虽然,在小说中作家尽力展示的是“人”在与“历史”和“政治”对峙中的失败,但在对人本身的艺术塑造上,小说又恰恰证明的是“人”的胜利。在现象和现实层面上,人是历史和政治的“牺牲”,是毫无疑问的失败者,但在艺术层面上,“人”又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是小说最后的赢家。这也是艺术的辩证法。可以说,《中国一九五七》正是在人性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统一中呈现其在“人学”领域的成就的。
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历史、政治的人性化以及人性的政治化与历史化这两条艺术原则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小说的如椽巨笔正是在这两条原则的引领下突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在作家笔下,人物的“精神战争”主要在三个相互纠缠相互联系的层面上展开:一是人物灵魂世界的自我搏斗;二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精神较量;三是人物与政治和历史环境的对峙。这三者构成了小说人物的现实生存境遇,也构成了作家所要发掘的人性辩证法的主要内涵。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自私与坦荡、软弱与坚强,既是泾渭分明的,又是相互交织彼此转化的,它们构成了小说所塑造的三种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基色。一种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李戍孟等为代表的坚守人格自尊与信仰原则的知识分子。冯俐以自己的道德伦理去对抗冰冷的政治伦理,不惜慷慨赴死;李宗伦为了“打狗的猎枪不能打人”的人格自尊,自绝尘寰;李戍孟为了自己“书写的权利”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龚和礼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之原则,宁可“食草”,吃得满嘴绿牙浑身浮肿死去,也不愿做“食蛇”的“野兽”。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一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自我生命的代价换回了知识分子“人格”的自尊。一种是以高干、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为代表的苛且偷身、不惜以迫害他人来保全自我的堕落知识分子形象。高干为了讨好管教,不但处处积极表现,还不断打小报告;张克楠为了巴结管教甚至不惜卑鄙地为管教捉笔“剽窃”泰戈尔的诗;而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人在我乐岭农场阉割残害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一幕,可以说既放大了他们人性中的丑恶,也隐喻了知识分子自我阉割的恐怖。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另一极,他们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良知却完全被阴暗丑恶的人性淹没,这使他们最终成了统治者的同谋与帮凶,成了对于同类的施虐者与施暴者。再一种就是主人公周文祥、吴启都、高云纯、苏英、张撰、解若愚、陈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周文祥曾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但落入政治的陷阱之后,他就沦入了既不能拯救别人,也不能拯救自我的悲剧境地。虽然他的人性、良知和人格并没有完全泯灭,但是强制性的自我阉割与自我扭曲已经使他一步步地变得妥协、软弱、明哲保身,失去了与现实抗争的能力。在第三部中他的最终成为“食蛇”一族,以及第四部中他和劳改犯们排队“告密”的场景都具有很强的寓言和象征意义。它象征化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心态和精神状态,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自我“死亡”的历程。在小说中,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是被作家置放于特殊的生存境遇中刻画的,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性问题其实已经被置换成了生存问题,生与死的选择、求生与本能的冲突使得小说中的人性哲学根本上超越了美丑善恶的层次而突进到了生命哲学与生存哲学的疆域。这方面,第三部中围绕“吃蛇”与“食草”而上演的一幕幕具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色彩的戏剧就是这种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这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又不完全是一种对峙和冲突关系,实际上他们还是互文性与互补性的,他们各自构成了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的一个侧面,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方的影子或心理潜意识。
与“人”的毁灭主题相呼应,“美”的破碎也是小说悲剧性美学力量的一个重要根源。小说的主体当然是反思和书写历史的灾难,但是在这种灾难的边缘我们仍然不时地能遭遇“美”的亮色与闪光。作家对美好事物、美丽人性的寻找与向往不是为了去营构一种虚幻的美之乌托邦,而是为了借这种美好事物的毁灭来反衬历史的灾难,来反思历史的黑暗。因为,美越是纯粹,越是趋于极致,她的毁灭带给人的刺痛才越是尖锐和持久。这大概同样也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尤凤伟是一个书写民间传奇的高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爱情”传奇无疑是最能体现尤凤伟风格的华章。周文祥和冯俐、吴启都和齐韵琴、张撰与王妃、竹川与她的乡村女子,这四对爱情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主旋律,每一对爱情都如泣如诉,每一对爱情也都不缺浪漫、忠贞与甜美。但是同样,每一对爱情也都有一个悲凉的结局。在爱情悲剧降临的那一刹那,绝望弥漫在小说的天空,它激起的是我们灵魂深处经久不息的忧伤。而天真、可爱、善良的小建国的死,以及善于在“地狱”中寻找美与艺术的画家张撰的命运,也无不折射和象征了小说所描写的那个“黑暗的年代”对于美、童真、艺术和人本身无可逃避的巨大毁灭力量。
第五章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3)
四 “回忆”叙述与文体意识
我一直把尤凤伟视为山东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他是一个对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结构有超常敏感的作家,也是一个在艺术上极富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作家。从“石门”系列到“抗战”系列再到这本《中国一九五七》,无论涉足什么题材,表达什么主题,尤凤伟始终都能保持那种艺术的纯粹性,始终都能让艺术的底色不因“写什么”的变化而褪色。而这绝非是一般的作家所能做到的。如果说,尤凤伟从前的小说因民间性的叙事和传奇性的故事而风格独标,多少有些沾了艺术表现领域陌生性的光的话,那么《中国一九五七》这部在一般作家手下难免会有主题先行、道德说教色彩的政治反思小说能完美地贯彻尤凤伟“真正的小说”的艺术理想,则确实让我们服膺了他卓越的艺术能力。我们当然现在还不能简单地给《中国一九五七》盖棺定论,给它以终极性的评价。但从个人的阅读感觉与艺术感觉出发,我敢说,它是我二年度读到的最为优秀的小说。说它优秀,不为别的,只为它的艺术,只为它的艺术纯粹性和艺术创造性。
其一,“回忆”的叙述学意义。《中国一九五七》是一部在叙述基调、叙述视角和叙述节奏、叙述语式上都非常和谐、非常统一的小说。庞大的题材、众多的人物、流动的地点……这一切对于小说的叙述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因为它往往会带来小说视点的混乱和结构的零散。而尤凤伟却有着把劣势变成优势、束缚变成自由的艺术魔力,叙述的难度反而为他的小说增添了摇曳的美感与魅力。尤凤伟在叙述上点石成金的武器,并不神秘,那就是先锋作家特别擅长使用的“回忆”。“回忆”作为主要叙述方式在这部小说中的成功运用确实显示了尤凤伟非凡的艺术匠心,也在技术层面上为小说的成功提供了保障。首先,“回忆”作为一种心理化的方式有助于赋予小说互不相干的时空、故事、人生以一个笼罩性的精神氛围,这实际上也就赋予了小说统一的精神秩序和统一的美学框架。说穿了,“回忆”的功能就是把万事万物皆收笼于心,它能真正超越具体时间、空间的束缚与限制,而给小说叙述以高度自由。其次,“回忆”既是一种主体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正是小说反思政治、历史主题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