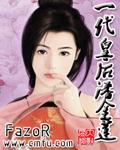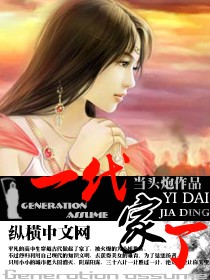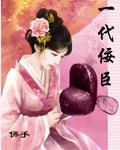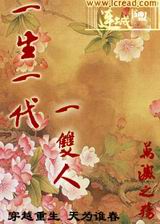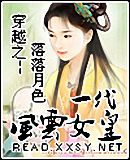一代伟人: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
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5、6、7、8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
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
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
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七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
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
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破核威慑(10)
在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原子能工业和其他国防尖端领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措施,使得这些领域在“文革”的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无论是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的四年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
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
这年3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4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人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人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
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啊?”
专家们肯定地回答:“可靠!”
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
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
4月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
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
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l、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4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
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
寻求团结(1)
寻求团结,再访苏联,对苏联新领导失望后永别莫斯科
1964年10月,曾经不可一世、刚刚过完70寿辰不久的苏联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这天正好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诸于众,它们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忙得不亦乐乎。为赶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伍修权是这样回忆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就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之前,我们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至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杨尚昆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赫鲁晓夫突然下台,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紧急而重大的难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处理中苏关系?
四个月前,在赫鲁晓夫70寿辰的时候,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曾联合致电祝贺。贺电说: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而这下,真的发生重大事变了,奇特的是,这事变的主角恰恰是赫鲁晓夫。
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此时聚焦中共中央领导层。周恩来以他那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敏感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
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
周恩来所说的这两种态度,决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关系上的两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这天,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毛泽东还交代外交部,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随后,这份有中共中央四位主要领导人署名的贺电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天夜里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贺电发出去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对这种考虑,周恩来向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庆日,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
寻求团结(2)
决定做出以后,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先试探苏联方面的态度。会后,立即由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一见面,周恩来主动而又感慨地说:“今天是10月28日,两个礼拜来的变化很多,……我们对变化不甚了了,所以想在两党两国之间进行一些接触。”
契尔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接触”。作为驻华大使,他对接触一事求之不得,接触总比对抗好。
周恩来诚恳地说:“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就在契尔沃年科惊喜之时,周恩来的话题更进一步:“如果这样对你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在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