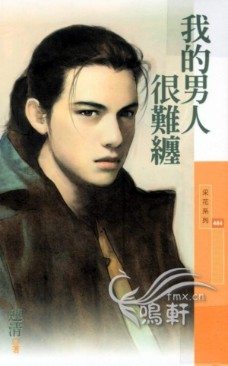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8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过。错划右派问题 ‘改正‘了,生活对我的蹂躏也并未终结。我好苦、好累哟!这一切,全因为他已离去,他 没能扶我一把,对这一切他全然不知道,他只是默默地走了,走了。
30年前,我离开他太匆忙,我未能找到他的坟茔,未能在他的坟茔前倾诉衷肠,倾倒苦水,他会怪罪我吗?也许,他曾等待倾听我的哭诉,等待倾听我凄凉的哭声里的情和爱,孤独寂寞的他又怎忍心起身呢?他对人世间还有着万千的留恋撕扯着他已不再跳动了的心。
正当英年的他被活活饿死。40年杳无音讯的大哥景衡,突然在1988年从海峡彼岸给老家来了信 。我写给大哥的第一封信只能是把景超的遇难告诉他。这对于大哥委实是太意外了,他说接 到信后‘如五雷击顶‘,‘不禁老泪直流,悲痛万分‘。然后,大哥回到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他见到尚健在的舅母时,大哭:‘我没有把景超照顾好。‘9月下旬,大哥、三弟 景凯、四弟景刚及景凯的女儿艳梅、女婿一行,来到了兰州我的家中。在吃第一餐团圆饭时 ,大哥举起酒杯站了起来,哽咽着想说几句话,从他的喉间却只挤出了几个字:‘今天,我同自己的家人团聚……‘说着,泪如雨下,无法再说下去了。这泪水,这未能尽言的祝酒辞 ,正是最郑重地表达了大哥对此次团聚的拳拳之心。他心中的抱憾尽在不言中。大家都哭了 。家宴上唯独少了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就离开人世的景超,使整个宴席变得冷落了。此时,我 的心在滴血,在哭喊。我多么想在家人们面前倾诉我多年来郁积的悲苦和委屈啊!但是,我 不能也不愿大哥在乍到兰州的第一天过分悲伤,因为他已经是古稀的老人了。我尽量控制着 眼泪,景刚向我递来了一张餐巾纸让我擦泪。擦吧,擦吧!在这充满了家人的亲情,充满 了喜庆气氛的团聚时刻,我不能让眼泪任意涌流。
多年来,我极少放纵自己感情的奔涌,因为我没有权利任意地悲伤,更没有权利在忧伤中消磨时日。20年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现实,只准许我接受命运的摆布,谁也没有给我权利,让 我任意悲伤!在失去景超的最初的日子里,除了同情我的难友们曾给予我许多至今还让我感 激在心、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帮助以外,那些曾和我共事多年、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志‘们 (那时我还没‘摘帽‘,没有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同志‘)有谁关心过我,安慰过我吗!那时 候,谁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景超。我心中最亲爱、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十 恶不赦‘的极右分子,有谁敢再提起他呢!仿佛他是极自然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无须再 说及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我是理所当然的。而我的身边尚依傍着两个不到10岁的孤儿, 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里?那些曾是我的‘同志‘的许多人,此时都冷漠地疏远、回避着我 ,对我和两个孤儿视若未见,权当路人。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 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特别是在作为党的喉舌及驯服工具的甘肃日 报社,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 多悲苦,许多凄凉。但是,景超留给我,要我做妻子的一人来承担的一切,我必须全部地担 当下来。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上,我所要做的只能是苦苦挣扎,踏着苦难,踩着忧伤,走我 自己的路。多年来,正是这苦苦的挣扎,重新铸造了我的性格,铁石心肠就是我,我变得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
大哥一行在兰州只住了3天,我们就开始了新疆之行。四弟景刚在石河子建设兵团的处境依然很糟。这次新疆之行的目的地,就是他在石河子的家。我们是抱着幻想,想借大哥的‘东风‘,争取让他恢复工作。几年前,他所在的单位143团精简了他,让因公负伤的四弟自谋 生活,这种做法显然没道理。
我们的新疆之行,达到了当今中国人旅行的一流水平。我们有四个软卧铺位,也就是说独占 软卧车厢的一个包间。不用说软卧车票是大哥掏钱买的,而且是凭大哥的台胞证才一次购 得了4张。大哥的服役够长的了,‘七七‘事变后,他就是军人,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杀过。但在解放战争初期,他被解放军俘虏过。这样,到退役时,他才只是个中校衔。但是, 他的‘养老俸‘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景凯作为离休干部享受县级待遇,我作为副教授也行将退休,我们都希望手头宽裕一点。这一年失控的物价,却十分令人不安。
当晚近午夜时,我们各自就寝。
第二天一早,列车奔驰在河西走廊上,行程已很远了,窗外已是另一派景色。漫漫戈壁伸展 到无边的天际,火车南侧的远处,一抹起伏的窄窄的山脉蜿蜒而去,始终又和列车的走向平 行,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祁连山了。橙红色的太阳跳出地平线不久,但一点也不耀眼,它色 彩鲜活,又大又圆。只有偶尔出现的排成了队的钻天杨尚未飘零的树叶闪着疏落的绿光。啊 ,我久违了的河西走廊!我梦魂里久已失落却又魅力无限的戈壁风光!你苍凉、辽阔的存在, 证明了我的过去,我过去的存在!你是历史的见证人。重逢重重地撞击着我感情的闸门,我 不平静的思绪被翻搅得如同滔滔巨浪中颠簸着的一叶扁舟。我知道,凝滞封闭了几十年的往 事,将会一幕幕重现,沉重的幕布要拉开了。
列车在继续前进中。
窗外闪过大片草原。一团团、一簇簇的野草行将枯萎。我曾工作过的甘南把草原叫海子,如 果这也是一片海,海面上出现的有红、黄相间的浪花,白白的羊只在浪花里悠闲地浮沉游弋 。突然,似幻又似真,我分明地看见景超身着整洁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白皙瘦弱的面庞执 拗地向着我。他热切地望着我们的车窗,急急地从羊群中迎面奔跑而来……他奔跑的速度赶 不上车轮前进的速度,随着列车的前进,不见了他奔跑的身影。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在草地里,羊群中,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向我,向着我们的车厢迎面跑来。
前面出现了白杨、沙枣树掩映着的村落,房顶一概是后高前低,如徐缓倾斜的小块坡地,一 块又一块,高高低低,大小不一。院墙都不高。墙外,一墩墩发黄了的芨芨草错落地出现在 路边,周遭夹着各种杂草。景超从那边后墙的拐角处出现,绕过芨芨草墩,又急急穿行在小 径中,奔跑而来……飞驶的列车又越过了他。
在列车的隆隆前进中,一片无垠的新绿伸向远方,是才出土的冬麦给大地涂抹了这鲜艳的颜 料。无垠绿色上镶嵌着条条阡陌,景超又从阡陌上向我奔跑而来。他一点也没老,他在用 年轻强壮的双腿用力奔跑。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列车超越,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出现,继续拼命 飞奔……啊,这无结果,却又永不休止的奔跑!
这情景勾走了我的魂魄。我痴痴地呆在了窗前。在火车的飞驶中,我一连几个钟头地望着窗 外……30多年来,梦里的他也从未这么清晰这么执拗地出现过。我觉得是他听到了我心灵的 呼唤,才这样出现在面前……他跟前跟后,苦苦地追赶火车,追赶妻子,不断出现在车窗外 面,是为了细细地瞅一瞅衰老了的命苦的妻子,也让我好好地瞅瞅他。也许,他知道在这列 火车上不仅坐着我,近半个世纪杳无音讯的大哥从海峡彼岸归来,使家人都聚在了一起,他 是想尝试着冲破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也来参加这次聚会,这来之不易的聚会。然而,他的一 切努力都毫无结果。无论怎样,他已是个悲惨的失败者。
我用力闭住了眼睛,让苦涩的眼泪流进心里,苦极了的心沉极了。我在默默中忍受着这不堪 承受的重负,听到了泪水在心中倾轧激荡的声音。
我们在景刚家住了10天。用大哥的钱请客,周旋,费唇舌,写报告,也被请,得到各种以后 一概未能实现的承诺。然后,在乌鲁木齐买了火车票东返。乌鲁木齐真是个具有民族特色的 美丽城市,商店里出售的维族小花帽十分漂亮。
火车东返时,我们一路未作停留,因为天已寒冷,乌鲁木齐已开始飘雪,大哥得赶紧回台湾 。
在行经高台明水站时,我不禁放声大哭了。
我哭得死去活来,全然不顾是在火车上。
30年来,我苦熬苦度,从来没有和家人见过面,没有和这么多亲人团聚过,更没有在家人面前开怀痛哭过,让我哭个够吧!我靠在门上哭,趴在铺上哭。大哥替我脱去了鞋,将我的双 腿挪到铺上。我依然大哭不已,在铺上翻滚着哭!我要把这辈子该流尽的泪水,畅快地流个 够!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痛哭声中,从记忆深处一幕幕走出……
景凯和景刚躺在上铺悄没声息。他们也在流泪吧,他们能说什么呢?
大哥声音颤抖,哽咽着说:‘弟妹,你这样哭,我以后还怎么回来……‘他大约认为这是阻 止我大哭的最恰当的理由。然而,不是大哥的归来,不是同家人团聚,几十年来,我何曾畅快地哭过?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 的丈夫死去而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 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 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
……
我又一次经过了高台,经过了明水,我从他长眠的地方擦身而过,但我未能哭倒在他的坟茔 前向他诉说一切,几十年的血和泪,凌辱与苦难,扭曲与抗争,这已是历史了,说也说不完 !我要把全家人团聚的事告诉他,把分别了40年的大哥从海峡彼岸返回故土同家人团聚的事 告诉他,你知道吗,大哥返回故土和家人团聚时,最最伤心的,就是少了一个你!
大哥回台湾后,我急切地寻找当年在安西劳动时的难友。到1990年春节时,终于与在十工农场同台演出的侍峒山见了面。30年的沧桑巨变,使我们的难友情更醇更深。当时,本书的前 几章已开始写了。侍峒山告诉了我许多难友的通讯地址。然后,就有了我和在高台县国营南华林场工作的曹宗华的通信。
曹宗华当年不到18岁就戴上了帽子。30年一弹指,他也50岁了,他在信中称我‘尊敬的和大姐‘,说,接到来信,‘我高兴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好‘,问我:这些年‘不知大姐你是 怎么熬过来的,详情以后请大姐慢慢再谈谈‘。我万万也没想到,他在这封信里竟告诉我: ‘ 前几年我被分配到明水河农场当小头儿,闲暇时带着家属孩子闲逛,看到这里的大片坟地。 我曾听说你老伴的遗骨抛在这里,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但我不知他的姓名,请你告诉我一声 ,我将尽力帮这个忙,将他的坟墓找到。‘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决定要做的事吗!我太感谢了,我感谢老天终于睁开了眼睛,让宗华来帮助我了却我多年未了的夙愿。这是宗华在19 90年7月6日写的信,我当即决定略做准备到八九月天气稍凉,就奔赴高台。但心中仍有疑惑 ,当年未能见到的坟墓,30年后还能找到吗?
8月下旬,景刚因事路过兰州,我说及去高台的打算,他决定和我一同前往。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