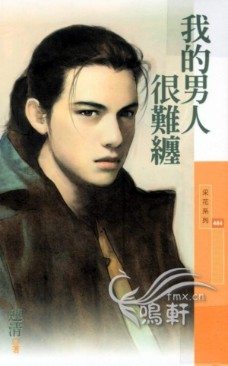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此刻,作 为阶级敌人,我们已无权过问此事。我们如去找县上,一说及身份,自己就有可能被轰出来 。为等农场来车,我们在旅店住了两三夜,从早到晚,一直听着工人时轻时重的痛苦呻吟声 ,这呻吟,一声声击打着我们的心扉,更使每个人都思绪烦乱,心情沉重。但大家都无言, 我们能说什么呢?后来,还是热情的杨骁自己花钱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几十里外的林场领导 ,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不过,直到我们离开,得肠梗阻的工人还住在旅店呻吟不止。这是我 们来安西县后感受最深刻最沉重的第一件事。
杜博智终于坐着农场来县城办事的拖车来接我们,约1小时后,我们到了十工农场,那天依 然风和日丽。人事干部蒲廷珍已将我们的基本情况向农场领导作了介绍。李文亭副场长和工会主 席邹士杰还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大意是说,这个农 场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最早的职工主要是复转军人,也陆续招收了许多农民,今春 从省上和河西各专县来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大约有二三百人,还继续在来,对这些 人 的到来,我们是欢迎的。考虑到这些“同志”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上主要看 态度,该照顾的还要照顾,在生活上和原有职工一样对待,不歧视,对你们也是这样。省上 早来的一批“同志”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李副场长和邹士杰说话态度和蔼,都是陕北腔。他们所说的,在以后我们相处的几年里都 是实现了的,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地劳动和 生活,这样的处境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
会上,把我们这些右派称之为“犯错误的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感到既惊讶又亲切 。近一年来,已无人称我们为“同志”,我们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副总编辑樊大畏挖苦 地称我们“右派先生”,我觉得特别不顺耳。苏联诗歌“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 去”常萦回在脑际,提醒着我追忆有着“同志”称呼时的美好时光,对成为人民之敌的 不幸伤心不已。在这里,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呢,还是出于 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但是都感到有些宽慰,这里的政治空气与兰州似乎 有些不同。
当时,领导上就宣布把我们5人分在3个大队,我和杨康分在了场部的三大队。
我们是吃过饭才到农场的。午饭时,我看到排队打饭的长队中,有一梳长辫的年轻姑娘, 长得十分漂亮,脸晒成了绛红色,显然才从地里劳动回来,也是右派。另一年龄稍长的女同 胞站得比较靠后,戴最新潮的琅架眼镜,穿深蓝色男式制服上衣,米色毛料长裤,绛红 色 的长脸略显得黑。长队中的男同胞也有几个戴眼镜的,大都是书生相,衣着破旧,烈日的曝 晒已使他们破旧的衣裤发白,他们的脸色一律是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绛红色和黑红色。他们 也好奇地看我们,并议论一番。看来,他们都是先我们而来的右派难友。
我和两位女同胞住在了一个宿舍,这是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中的一间,是个套间屋。里间屋 有1米多深,有个可住1人的小炕,外间屋由南向北延伸是个大炕,两间屋的通道约1米 宽,大炕前有1米多宽的空地。大炕靠墙的前面,有一个长平台,这是用1寸多粗的树枝支 撑,高于炕,平面搭上木条、细树枝,再抹上泥,表面抹得光光的,成为一个1尺多宽的长 平台,这便是我们的桌子。戈壁滩上木材奇缺,除了场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人宿舍都只有 这样的平台聊充桌子,放些日常用品,如碗筷、洗漱用具等。我们能享受到同工人一样的待 遇,应该说已是一种优待了。
我们3人同住外间屋的大炕,3人并排睡,小徐靠墙睡,我睡中间,年龄稍长的石天爱睡在 靠通道的那面。
小徐,名福莲,浙江金华人,只有20岁,是地质勘探队145队的队员,但她已做了妈妈,也 是夫妻俩都打成了右派。她3月从勘探队驻地永昌县来农场时,硬是给生下才七八个月的小 女孩断了奶,把小女孩狠心地交给婆婆,流泪不止,难割难舍地离开了温馨的家。她这是第 一次离家,年轻的她独个儿离开家来到农场,但全家人的苦难都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石天爱有个有名的父亲军阀、大汉奸石友三,母亲程竹溪原是唱京戏的艺人,是石友三 的三房姨太太,只生了石天爱1个。石友三被卫立煌处死后,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一直住 在天津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解放后,一个曾得到她母亲帮助的中医向她母亲传授了一种治 疗关节炎的竹管疗法,她母亲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医生。1956年,石天爱从天津志愿支援大西 北,来到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才1年就当了右派。作为女人,她手上常夹着纸烟吞云吐雾 ,手指都熏黄了,在劳动和生活上肯定比别人更难适应,而且她是单身,还没结婚,这就很 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她比我大1岁,虚岁28岁,后来,右派难友们常戏谑地说她:“年方 二八!”
她俩都已没有了工资,因为她俩受的处分是监督劳动,是仅次于劳动教养的处分,只是还保 留公职。她们从农场每月领取20元左右的生活费。报社给监督劳动处分的只有杜绍宇1人 ,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大约是想自谋出路吧。这里专县来的右派普遍都是监督劳动,这反 映出有的地方越是到基层执行政策越左,监督劳动可以省却本单位一笔工资支出,他们也觉 得省事。她俩其实都没什么事,小徐跟我一样,也是由丈夫的问题而累及,她丈夫梁富杰原 是她上地质学校时的老师,人年轻精干,业务过硬。此次地质队因工作需要没让小梁下来, 可以到农场劳动的只能是小徐了,小徐其实是替丈夫受过。石天爱 说她自己是“天生的右派”,并无右派言论就当上了右派。她一说我就能领会,兰州经过鸣 放大抓右派的时候,地县还没开始鸣放,到动员大家鸣放时,人人噤若寒蝉。但右派按各单 位人数的比例要抓够,抓不出足够的右派无法向上级交差,各单位便只能找一些家庭出身不 好的人开刀。论家庭出身,全张掖地区要找出比石天爱更突出的怕是没有了,石天爱只能是 首当其冲地当了右派。如今我们都已当定了右派,回顾各自当右派的经历,都已是痛定思痛了。在这儿能够自由地 交谈自己的痛苦经历,也是一种幸福。在原单位人家总认为我们认罪不够,立场转变得不彻 底,没完没了的认罪,痛骂自己,我们已被扭曲了的灵魂每天都要承受这不堪忍受的凌辱。 现在,那种令人活不下去的氛围已不存在,它无法左右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石天爱头枕在叠起来的被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8分钱一盒的廉价烟,谈笑自若地说起挨 斗的情形,倒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打着哈哈说:“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哪见过 斗争会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他们说什么,我都认了。他们说我反党,我就承认反党。不 就行了吗?”由惊恐不已,到被迫承认一切,而后又玩世不恭,这一心路历程是由血和泪滴 成的,我的右派难友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在他的一生里都只吞咽委屈和痛苦 ,他们的性格和心性使他无法对人生开玩笑,直到了却了悲苦的一生。
小徐絮絮地说起自己的事来,仍不免心绪低沉。她问我:“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 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 来的,你说说看!”我觉得她提这个问题有些好笑,便不经意地回答说:“你真没弄懂吗?右 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我们都是因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才到这儿来改造思想的 。”她的脸色竟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我丝毫也没有料到,我的 回答竟成为对她的沉重打击。她虽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单位上只开过一个小型斗争 会,对很多事还摸不着头脑。斗争她时,有个劳改过的工作人员为了立功赎罪表现自己,“ 揭发”说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她那时生过小女儿不 久,心都放在了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 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一个普通的还是女性的地质勘探队队员的她,对这些哪会注意 到呢?但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她,此时倒是受到国家大事的关注,用不着对证落实别人的 “揭发”,也没怎么批判,就给她定了性。几天后,她被迫来到农场劳动。她记得十分清楚 ,她是3月18日来到十工农场的,属于来农场劳动的第一批难友,而她确实还没弄懂右派是 干啥的。我的回答使她清醒了,从此,她才真正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常常一个人偷偷饮 泣。
她说的最多的,还是小女儿的事。她来农场参加劳动前,不得已给才刚七八个月的小女儿断 了奶。刚劳动时,奶水胀得乳房疼痛难忍,她常要跑到地边挤出奶水,可她的小女儿却没有 奶吃。50年代,女犯人在哺乳期间尚可缓刑或在监外执行,没有触犯刑律、具有公民权的女 右派却是别样对待。永昌是个小县城,无新鲜牛奶可买,奶粉、炼乳都难以买到。她一边挤 奶,一边哭,心里在呼唤,为什么小女儿也要跟着自己遭罪?为什么?饿着肚子不断哭叫的小 女儿的哭声,时时响起在她的耳际,撕扯着她做妈妈的心。她问我:“兰州能不能买到奶粉 ?”我说:“能买到。”她立即兴奋地想请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买几瓶寄给她的小女儿 ,说她来时带了些钱,买奶粉的钱还有。那时,蒲廷珍因无去县城的顺车,留在农场还没走 。蒲廷珍为人憨厚,可也不能为一素不相识的右派办事。此时,为了小女儿,她似乎忘记了 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她根本对右派分子作为阶级敌人的严重性没认识。但我不愿拂她的意 ,她做妈妈的心意,急不可待地要让小女儿吃饱肚子的热切感情,一副泪汪汪企求帮助的神 态,使我不忍心说出此事难以办到。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犹豫,后来竟自己找到蒲廷珍要求 代买奶粉,当然,未能如愿。
小徐和石天爱都是由县武装部派人押解到农场来的,坐大卡车一起来的还有当地的不少右派 ,送他们的县武装部的干部腰里都别着手枪。两三天后,我见到荷枪的解放军押送来农场劳 动的右派,两三个背着行李的难友在前面急急赶路,荷枪的解放军跟在后面监视。他们大概 只在场部办了一下手续,分到了别的大队,未能在场部停留,就急急走了。这些难友的处境 比我们可惨多了,我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所谓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也可以如此执行 。
我在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劳动,是到一个很大的羊圈里除粪,全部工作是把一个冬天积 攒的羊粪铲起来,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到羊圈外面,堆积起来做肥料。有五六个人一起干, 铲的铲,推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