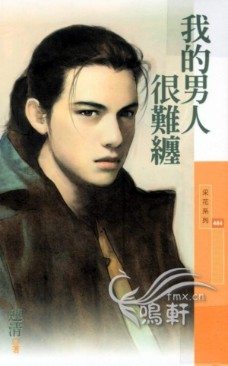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啊,我的亲人,你到底也没能等住,没能等住我们见面的这一天!你不是没有等,你能支撑 到那一天,等得不容易,等得苦。你苦苦支撑,苦苦等待,以全部的生命力等着我,用最后 微弱的一息等着我,可我没能及早赶到你身旁,你终于没有看到我,你等得好苦啊!这个可 恨的世界可以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你。你撒手而去,把没有涯际的 苦难留给了我,留给了你的‘小娇娇‘。你竟忍心离去……你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走了吗?3年 前我们临离开兰州前,你曾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的话激励自己:‘活着就是幸福。‘ 你万分眷恋曾给了我们无边磨难、太多痛苦的世界,是因为你对未来仍有着憧憬。可是,严 酷的饥饿不许你活,这个世界未能留住你,未能留住对你、对我们来说唯一可称之为幸福的 是你活着的生命。
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零零的小路上走来 ,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 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到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 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
啊,我的亲人,可怜的冤魂!你一腔热血透彻揭露的弊端,你痛心疾首不能释然的忧患,在 你受难时迅速扩展,无遮拦地汹涌起巨涛狂澜。不然,大饥馑何以能在全国蔓延扩展!我的 亲人,你又怎会遽尔离去,被逼进另一个世界?啊,不屈的英灵!你已默默离去,但是,我 知道,炼狱里的烈火喷发翻滚,也烧不尽你的冤屈和愤恨,烧不干你痛彻肝肠的血和泪!你 不会安息,你永难瞑目!
孤儿寡妇们的悲哭声,在队上一定响起过多次,干部们听得多了,也听烦了。他们无动于衷 ,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 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 们沉默了一阵之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 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此时, 队上干部同我这个右派分子之间,只有在景超及众多难友们的死因问题上的心照不宣而又 讳莫如深,才是一致的。当然,他们的讳莫如深,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一个个活泼年轻的 生命被逼死的全过程,他们全部清清楚楚,他们是参与者。良知,负罪感,不能说在他们所 有人的心灵深处就没有出现过。而残暴成性,作恶多端的人心底正涌出阵阵恐惧,毕竟,人 命关天。他们害怕遭到惩处。
队上不是我可以待下去,一直哭下去的地方。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找来了人,说了些什么,让来人带我去睡觉。我走出有灯光的办公室,在黑暗中走了一阵,被带进了一个挂着草帘的所在,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长形的地窝子。在昏暗的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灯光的摇曳下, 我看到睡觉的长长的土台子上不是炕,更不是床,应该说是略高于地面,用铁锨挖就, 只能叫做土台子的所在,堆放着许多被窝。领我进来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抱过两床被子 放在土台的尽里头,用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说:‘你就随便铺随便盖吧,如果不够就再拿一床 。‘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些被窝已没有了主人,它们的主人已悲惨地死去。在四工农场,我 的难友们睡的地铺上都铺着厚厚的麦草。这里的土台子上没有一根麦草,说明他们连农场自 产的麦草也没有带来,未能铺上。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里,他们肚中饥饿,又是在经受 着怎 样的酷寒啊!一个多月前,我在四工农场场部看见过一柄失落在路上尘埃里的塑料牙刷,当时判断一定是哪位难友的遗物,痛苦地想到我给景超也买过一柄同样的牙刷,不由得去推测 我的亲人是否仍在用它刷牙,还是……路上尘埃里的一柄塑料牙刷,曾撕扯着我滴血的心, 令我痛煞。如今,景超的塑料牙刷已不知失落在哪里,他生命的失落,也只是在我找上门来 ,才在花名册上翻来寻去……这里堆放着的一堆堆被窝,都各自有着多少生离死别、惨绝人 寰的故事啊!在这凄苦漫长的冬夜里,死难者们会向我尽情倾诉,诉说他们已无法沉默地咽 下的深深的怨恨,诉说那无情地吞噬了他们活泼泼的生命的残忍罪愆……
地窝子里又进来了个小伙子。他俩用拣来的几根木柴,在土台中段几块土坯支起的炉灶上 生了个小火,显然是准备做些吃食。他们神情自若,并没有因为我这个新寡的女人的出现而 有所表示,没有人说一个字的宽心或安慰的话。我就是我,他俩是他俩,同在一个地窝子里 ,竟像路人似的,才刚进来的小伙子也不和我打招呼。那些成堆的死难者的被窝,以及与之 相关的死难者们的事,在他们仿佛都无所谓,好像这一切与他们也都毫无关系,或干脆未曾 发生似的。我呆呆地坐在长土台的另一头,愣愣怔怔的,陷入了一种新的麻木和迷惘。我在 四工农场的‘医院‘曾目睹了死亡,听到过不少难友的死讯,从心灵到感情受到的巨大冲击 ,曾极大地改变了我自己。眼前,我是在这死人更多的地方,在堆放着许多死难者被窝的地 窝子 里在四工农场我还未曾见到过如此的景象。俩小伙子显然,他俩都是劳教的小右派 ,仍然很正常地做吃的,正常地安顿我睡觉,正常地说着他们自己的话,他俩同办公室那几 个 干部也没啥不同,这里的情景同那里何其相似乃尔,一切似乎都十分正常,这使我连眼泪都 流不出来了。原来,这个世道就是叫人们去饿死的,我的亲人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已饿死 了,一切的一切,依然还都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俩小右派的冷漠不在乎,更冰冷了我 悲伤的心。四工农场的囚犯待遇,精神磨难,潜意识里已凝固了的比别人低一等的贱民意识 ,使我对失去亲人的悲苦也觉得只能在心底悄悄消融……
我愣愣怔怔地呆坐着,一路上茫茫无际的雪原又不断浮现在眼前,心头飘起了一支熟悉的歌 :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路边。
车夫挣扎起,
转告同路人,
请你埋葬我,
不必记仇恨。
请把我的马,
交给我爸爸,
再向我妈妈,
安慰几句话。
转告我爱人,
不能再相见,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在农场几十次、上百次唱过的歌,谁料想述说的竟是我自己的故事。是的,他带走了一切 ,带走了我们俩的一切……‘来吃点吧,你大概没吃晚饭。‘俩小伙子用搪瓷饭盆做好了饭,竟邀我一起吃。我已大半 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办公室的干部根本没问及我是否吃过晚饭,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屑于为 我准备一顿晚饭。饭盆里冒着热气的是用米粉熬就的糊糊,一个小伙子的姑母从武汉寄来的 米粉。在这种时刻尚能从外地寄来米粉,这宝贵的外援看来几年不曾间断,他们年轻可爱的 生命因而才得以保住。在四工农场形成的吃饭已成为生命活动之第一需要的习惯性本能,使 我稍作犹豫,便从帆布提包里拿出一个粗劣的搪瓷短把调匙,同他们一起从饭盆里舀米粉糊 糊吃。当然,我吃得很有节制,并送给他们每人一个花卷,花卷是我用饭票打来装在帆布提 包里的。看样子他们已许久没吃过白面花卷了低劣的劳教待遇。整个河西走廊当时小麦 是高 产作物,我们在最饥饿的时候也只吃小麦,他们这里名为农场,特别是搬迁到高台以后,还 没有过收获。天哪,这儿不死人才不正常。他们连连说:‘花卷真好吃,好吃!‘年轻的脸 上透出吃了美食佳肴才会有的喜悦。这俩人长得都挺帅。交谈了几句,才知道他俩都是兰州大学的学生,他们都说不认识景超。领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定右派时才17岁,又一个王桂芳 !他俩的父母各在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任教,应该说,他俩都是教养好,非常优秀的小伙 子。他俩远在兰州的父母如果对这儿的情况有所知,一定都在感谢上苍,因为他们是这儿的 幸存者而感谢上苍。我忽然一下子明白了,他俩艰难地活了下来,对这里的什么也不说,显 得毫不在乎,习以为常。只是由于这里天天死人,死人属正常现象,说出死人的事实反倒不 正常。他们总归是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才被送到这里改造,他们一来到这里,一定和我的亲人 一样,立即就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知道了接纳他们的所在是人间地狱。但是 ,此时,他们对于地狱里为他们安排的一切只有承受了,说真话不是他们的事。这就是3年 的劳动教养要求于他们的。除了在饭食上有外援外,他们规规矩矩,抑制了人性中所有宝贵 的和应予发扬的东西,所以才有了如今的自己。为了生存,他们3年来怎样扭曲了自己, 怎 样紧张地绞尽脑汁应付一切,今天的我已无法用丰富的想象去加以描述,但,肯定地说,那 是男子汉们要以撕心裂肺般的痛楚才能说出来的复杂内容。我还想到,他们说不认识景超是 向我撒了谎。因为他们如若说认识景超,我一定要问及景超的种种情况,而那是不允许说出 的。他们无权说出,所以他们只能撒谎了。这里的干部一定早就向他们做过交代,不然,同 在一个队上怎么会不认识呢?可叹俩小伙子虽活了下来,失落了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地 狱就是只能把人变成非人,把活人变成鬼,而我们原先竟一点也没想到,一点也不知晓。我 的亲人的悲剧正是如此造成,许许多多的难友正是因此而离开了人世……我们当时竟还那么 执迷,错把地狱当成了通向人间正道的必经之途。我们的忠诚被无情地戏弄。我们作为阶级 敌人被残暴地打倒在地之后,自己竟还那么执迷,真是可悲之至!
吃完了饭,我坐在小伙子抱过来的被窝旁又发愣。那俩小伙子在地窝子的另一头收拾被窝准 备睡觉,已经和衣而卧了。可我怎么能和俩小伙子在同一个地窝子里过夜呢?尽管他们都很年轻。我愣怔着,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个领我进地窝子的小伙子看出了我的心事,他把脸转 向我,亲切地说:‘大嫂,你也累了,只管睡吧,我们不会碰你的。‘这一夜只能和俩小伙 子一起睡地窝子了。人死多了,真正的‘男女混杂‘,那些管教干部倒很同意。
我只好脱去大衣,和衣而卧,下面铺一床死难者的被窝,上面盖一床死难者的被窝,再搭 我的皮大衣。假如死难者还会说话,他们一定会强烈抗议,抗议对他们的遗物如此处置。不 ,不,他们不会说话了,生前他们被封住了嘴已有几年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们扭曲了 自己,他们一个个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从此说真话便有罪了。劳动教 养后,更是动辄批判斗争,捆绑吊打,进严管班折磨,说肚子饿会成为新的罪行,还无任何 行动的自由。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们便只能无言地活活饿死在这里了。
旅途的劳顿,雪原上的急急赶路,亲人的永别,地窝子里的情景一天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