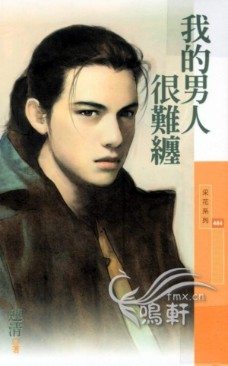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这 里差多了,他能够等到我去吗?我絮絮地说着,心情仍十分沉重。杜博智说些宽慰我的话, 敦促我快到景超那里去,尽到作妻子的责任。
去高台明水要坐火车,从四工农场去火车站,最方便的就是柳园车站,有四五十公里的路途 ,因汽车队的卡车常去柳园。
元旦过后,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到处一片白茫茫。
我焦灼万分地等待汽车队有车去红柳园,真是等得心都快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早晨,起床时 敲钢轨的‘当当‘声乍一响,我便会惊得吓一大跳,心狂跳不止,莫名地觉得新的一天不知 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或更大的不幸。悲伤,忧虑,焦急,迷惘。万般无奈中的等待,等待中 的惊恐不安,使我几近麻木的心理平衡急剧倾斜,精神濒于崩溃……
我切望赶快成行,奔赴高台,去救助我可怜孤单的,也许已是奄奄一息的亲人。此时此刻, 饥饿的他日思夜盼,唯一可指望来救他的,不就是做妻子的我吗?我已请准了假,我就要去 了,就要去了!我无法想象如今的他因为饥饿已被折磨成了什么模样,我更不敢设想他会是 ‘医院‘里那些形销骨立、瘦骨嶙峋的病号的样儿。但我认定,我只要出现在他面前,哪怕 他骨瘦如柴,昏厥在地,只要他一息尚存,还未跨出那最后的一步。我一定要把他救转过来 ,一定会把他救过来。他会躺在我的怀抱里微笑着睁开他无力睁开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 望着曾让他撕心裂肺般地苦苦思念着的妻子,望着他以为已经再也见不到了的最亲爱的人… …他会得救,我们都会得救。我们苦苦地等着这一天,已经直直等了3年,这一天眼看就要 出现。可我,可我还在忧心如焚地继续等待……但是,身边众多的死难者傍着那黑暗的大门 仿佛在低声告诉我:不容乐观,不容乐观,你亲人那儿是地狱!
我真不愿意他们絮叨。
准假以来,我每天都从打来的饭菜里挑出牛羊肉,放进一个装过奶粉的大玻璃瓶里,准备带到高台给我的亲人吃。我抵制了牛羊肉对我的诱惑,天天如此。只要饭菜中有肉,便顿顿如此。因为我知道,在如此严酷的大饥馑的日子里,外面一定很难买到肉,传说这里的一个难友用24块钱才设法买到一茶缸的羊肉,结果仍未能保住垂危的生命。我眼巴巴地、吞咽着口 水从自己的饭盆里省下肉要带给他,只是因为他比我更需要。况且,我只身去了高台,又哪 有钱,哪有办法去为他弄到肉呢?玻璃瓶里的牛羊肉已攒了多半瓶,这很可观,是唯一让我 感到欣慰的事。我的一片心,为救助我的亲人正在奉献的心,远在高台的他会感知吗?会的 ,他一定会。亲人的感应,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住呢?
焦灼的等待,分分秒秒都难熬的等待!
1961年元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总算有了外出的汽车,通知我时已临近开车,3个女伴匆匆忙 忙地送我上车。我先爬上了车顶,她们把我随身带的衣物里面裹着五六斤从食堂打来的 饼子打成了小行李卷,给我递到了车顶上,我还提了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些洗漱用具,还 有一两斤花卷。这些饼子、花卷,都是用当月发的粮票从食堂打来的,油嘴滑舌的‘职工‘ 炊事员再不给多打。石天爱在匆忙中说:‘我应该偷些面粉给你爱人带上。‘可惜早没想起 ,只成了遗憾。比起石天爱来,我参加工作早,当年曾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对于中国 共产党教导的一切奉若神明,在我们身陷绝境之后改变起来依然很难。从机磨坊设法搞点面 粉去救自己的亲人,这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啊,而我竟从未动过这样的念头!石天爱虽然想 得迟了一点,她毕竟具有此种救助难友的英豪气概,她认定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救人比什 么都要紧。小徐嘱咐我:‘来信啊!‘她内心里对我去高台是悲观的,只是没有说出来。王 桂芳暗自为她远在新疆的丈夫祝祷,为我送别的不祥的阴影,骚扰着她原本已经宁静了的心 。
农场离柳园车站四五十公里。我坐在车顶上,耳边一直响着呼啸而过的寒风,眼前闪过的是 茫无尽头的雪原。起伏的荒野、蜿蜒的远山,为雪花作弄,变成了迎面奔涌而来的白色的汪 洋波涛,又从汽车的两旁奔流而去。轰鸣前进的解放牌大卡车像是一叶颠簸着的小船。我为 汽车队工作了近一年,受到的仍是贱民的对待,空落落的车顶上就坐着我一人,司机的驾驶 室 里坐着的是食堂炊事员年轻活泼的妻子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司机也 巴结炊事员。好在我有皮大衣包裹,围着厚厚的围巾,心事重重地想自己的事儿,心潮胜似 眼前的白色浪涛,不知不觉间也就到了柳园车站,顺利地买到车票上了火车。
我的脸上没有刻‘右派‘二字这要感谢我们这个年代毕竟没有把古时候在罪犯头脸上刻 字作为标志的陋习保留下来。所以,尽管车厢里十分拥挤,旅客们仍用平等的态度接纳了我 。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还帮助我把行李卷举起放到行李架上,我有了一个和别的旅客们同样的座位。四工农场的干部们从来没有人这样帮过我。我很感谢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对全车厢的人突然感到都十分亲切,内心却又涌起无限的酸楚……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在旅途上十分熟悉的一切,此时却成为陌生的了。这列从乌鲁木齐开出的火车上,挤满了回老家过春节的内地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上海等各种口音的人都有,他们热烈地谈论 着同我丝毫无关只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带的各种吃食似乎十分丰富,有些人随便地剥食着煮熟的鸡蛋,吃了一个又一个。安西3年,我们几乎没吃过鸡蛋,鸡蛋是什么味儿都 要忘记了。唉,令人羡慕的吃饱肚子的新疆的来人啊!我呆呆地坐着,沉默无语,一直保持 冷漠的态度,使别人无法和我搭话。我,一个为救援自己的亲人从农场请假外出的女右派, 能和别人说什么呢?环境有了改变,我还得三缄其口,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悲伤地不 断想到,外面的世界和四工农场是多么不同,我们被人的世界所抛弃,是多么不幸啊!回想3 年前我们一行从兰州乘火车西去,在酒泉同景超分别后,杜博智还曾用他特具的陕西腔高声谈论,说3年后我们也许会乘同一趟车到兰州出席省上的劳动模范会议,兴高采烈。谁承想3年未到,我们在劳动上吃了大苦从未落后,却只落得像刑满释放人员一样的对待,甚且还不如,在严酷的大饥馑中庆幸自己总算死里逃生。和我们同一趟车到达农场的赵秉仁,上月已 饿死在四工农场,匆匆告别了人世……现在我在茫茫雪原上匆匆赶路,也正是为了去救助我 那生命危在旦夕的亲人。
明水到了,停车只1分钟。我匆忙背着行李卷从车上往下跳。这是个没有站台的小站,火 车离地面的距离不是我轻易能跳下来的,我只怕摔倒在地,好在壮着胆子跳了下来竟也站住 了。急忙走了几步,回头把前后左右都看了看,一片白茫茫中,下车的只有孤零零的我一人 。火车长吼一声,在隆隆声中又前进了。道班工人也只一人,已转身走进铁道旁唯一的一间 小屋里去了。
天已傍黑,寒风刺骨。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眼前只是望不到尽头的茫茫雪原, 白茫茫的一片。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我该怎样去找你啊?此刻,唯一可以询问的只有道班工人了。道班工人分明也看到了下车的我,当我探身进屋问路时,从我的衣着,背着行李卷的寒酸狼狈相,他至少也认为我是那些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家属。他走出小屋,很不情愿似的冷冷地用手指了指屋后,那是一条被许多脚印踩出的孤零零的向西北延伸出去的小路,说 顺着那条小路一直向前走去,就到了景超所在的大队。我问:‘还有多远?‘回答:‘八九 里路。‘我毫不犹豫,立即拔脚就走。
我踏着三四寸的厚雪奋力前行,除了脚下吱吱作响的声音伴我前进,茫茫雪原,万籁俱寂。 天 幕低垂,很快由灰变黑,天上连星星也没有。苍茫无际的雪原上,只有我孤独的黑影在孤零 零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踽踽而行,不断向前移动。像那茫茫雪原,思维几乎也成为一片空白, 只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反复出现在耳边:‘快走,快走,一定要赶到那儿,一定要见到我的亲 人!‘雪原模糊不清了,横亘在眼前的是黑黢黢的一片,只有踩在脚下的小路依然清晰可辨 ,间或发出白色的闪光。孤零零的小路引导着孤零零的我不断前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我不觉得背着的行李的沉重,手里提着的帆布包也觉不出它的分量。心里万分焦灼,只嫌脚 步从积雪里拔起来不够轻快,走得太慢太慢。才到十工农场时,我就听冯士伟说过狼群在戈 壁滩上追赶他和牛车的事,此时我也顾不得想及这些,不知道什么叫恐惧。我只求上苍保佑 ,让我快快赶到景超那里,他苦苦地等我,那痛苦难以为我所想象,他已难以承受,也许他 已等不及了呢……
走了许久许久,按照常情会慢下来的脚步,却一阵紧似一阵。
走着走着,路上出现了几棵大树,树下脚印零乱,原来黑暗中清晰可辨的小路一下子看不清 了,仿佛还有别的岔道,通往队上的小路究竟是哪一条?我急出了一身冷汗。在这黑夜的茫 茫雪原上,去问谁呢?踯躅良久,我只得弯下腰来,放下行李卷和手中的提包,焦 灼地对杂乱的脚印仔细地反复辨认,看了好一阵才总算看清,然后又毅然前行。
走啊,走啊,忽然,前方传来了脚步声,迎面出现了一个黑影。我毫不惧怕,惊喜地迎上前 去,向他打听。他吃惊在黑夜雪原的小路上竟会遇见一个女人,一个远道而来的女人,但也 不多话,只是指给我看,前面闪着昏黄的灯光的所在便是,说完转身就匆匆走了。他行色匆 忙,也是来看望亲人的吗?已经看望过亲人,见到亲人了吗?队上的干部没必要这么着忙地赶 黑路……我一下子就想到这许多,由不得地由己及彼地推测来人的行踪目的。不过,还真得 感谢他。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只顾低头匆匆赶路竟没注意看到那昏黄幽微的灯光。到了, 到了,灯光就在前面不远处。
我一脚踏进有灯光的队上时,煤油灯亮处,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都吃惊了。他们没有料到 一个单身女人冬夜会在这个时刻从车站走八九里路闯进队上。当然,他们不用问也就知道了我的来意。这些天来,跌跌撞撞地闯进队上来看亲人的一定不少,他们已应付自如。其中的一人听我说了景超的名字略有表示,另一人就拿起一个像是名册样的本子一页页地翻看, 也并不说话。我心中一喜,他们大概不清楚景超在哪个分队,住哪儿,想从花名册上查出来 。我坐在长凳上正想知道个究竟,听到的竟是晴空里的一声霹雳:
‘王景超死了,12月13日死的。‘
‘死了!‘这猛烈地轰击在心头的重击,立时使我觉得天昏地转。我嘴里喃喃着:‘他死了 ,他死了!‘半天竟哭不出来。
啊,我的亲人,你到底也没能等住,没能等住我们见面的这一天!你不是没有等,你能支撑 到那一天,等得不容易,等得苦。你苦苦支撑,苦苦等待,以全部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