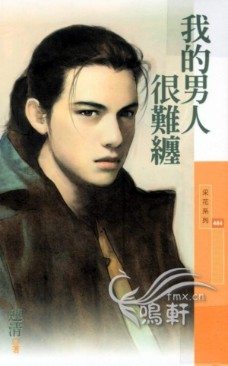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睡觉时,我就又饿了。我们几人说话都很少。我在忍饥挨饿中睡去。好像是为了补偿白天 清醒时挨饿的痛苦,梦中,我一直在吃着几年来从没碰过的好吃的东西……梦中的饕餮,将 我推入更为甜美的睡乡。我沉沉大睡直到天亮,醒转来十分费劲。
次日,我仍赶往‘医院‘。
我提着镰刀正要去割芦草,只见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从斜对面奔驰而来,车上拉着人。在 ‘医院‘前,车停了,跳下来的赶车人,正是那个瘸子‘职工‘。车一停下,他就吆喝着叫 车上的人下来,那几个形容枯槁的人肯定就是送来的病号了。他们动作迟缓,半天也下不了 车。只见瘸子生气地一把就拉下一个人来,那人猛不防被拉下车来,也许身体的什么部位被 弄痛了,他大叫一声,踉跄了一下,几乎要摔倒,又被骂骂咧咧的瘸子一把拉住。瘸子粗暴 地抓住这病号向‘医院‘门口走去,只见他身体左右晃荡,每抬一次脚步都挺艰难。瘸子把 他送到墙边,让他靠墙站住,又去吆喝别的人,那几个病号有的还在背行李,有的把行李放 在地上拖着慢慢挪动脚步,向前走去。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当车把式的瘸子对于 同自己一样服过刑如今饿成了这般模样的病号,竟如同对待猪狗一般。人类的同情心,在他 的身上已不存在。那么,是谁给了他摧残自己同类的权利?我不忍心看下去,更不愿和那瘸 子打招呼,就转身割芦草去了。
当我割来第一捆芦草,坐在靠大路一边的炕洞口,正准备烧炕时,一个人来到了我的身后, 问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一回头,看到他是欧阳夏,原省劳改局的干部。来四工农场 后,他曾在二站当小队长,我在二站劳动时才和他熟悉的。我简单地说了说来‘医院‘的情 况,也问及二站的难友们。他严肃地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不禁心 里一惊,又一沉,这种话可是说得的吗?继而又一想,我们如果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面 临的就是不能生存。我深深感谢他说的这句话。欧阳夏好像也正是为了说这句话才找的我。 凭感觉,凭本能,他觉得不能把这句话深藏在自己的心里。他是有事路过这里,看到我一个 人在这种时候还坐在‘医院‘的炕洞前,既感到有些奇怪,也是为我的生命担忧,为我的不 幸动了恻隐之心,所以走过来看看。毕竟,我不同于别人的,是个女性,还是个年轻的妈妈 。作为小队长,他并不能把同样的话讲给每个人听。他再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又默默地继续烧炕。‘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此时此地,这句话 真是太正确了!原来,我在思想上还没产生过生存不下去的精神准备。我只是想,情况即使 再恶劣,我也要活下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这迟到的意识需要行动,我却依 旧茫然,不知该怎么办。但总算有点开窍吧。我开始想到,难耐的饥饿一直继续下去,我的 身体也会被整垮,像‘医院‘里的病号一样倒下来。到那时,一切就真晚了。我无辜被整治 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于心不甘。我绝不能倒在这里,我还想重新获得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 的一切。我作为一个一心向党的人,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一切。党抛弃了我,世人抛 弃了我。但是,我还得为我所有的亲人活着,为我自己活着,我的一切不能就这样结束。我 一定要活下去,以我本来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我确信,总有一天,党的阳光会照 耀到我的身上。我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烧完最后一个炕洞,我正待起身走回病房,看见那3个年轻‘职工‘都走过来了。这里,正 是那间大病房的后面,平时没人来。他们来干什么呢?只见其中一个脸颊特红,小个子,说 河南话的‘职工‘,从棉衣里掏出一个小布袋,给那两人都倒了些炒好的麦子,那两人旁若 无人地立时大嚼起来。小个子河南‘职工‘招呼我说:‘你也吃些!‘往我的上衣口袋里也 放了几大把炒麦子,然后自己也吃起了炒麦子。这可是求之不得的佳肴,我也大嚼起来,只 觉得满口生香,每粒麦子都喷放出难以言喻的、令人迷醉不已的滋味。我几乎是在舍不得咽 下去的状态中匆匆吞咽了经过反复咀嚼的炒麦子,然后用舌尖搜括粘在牙齿、牙龈、上腭及 满口腔留下来的炒麦子的残渣,和着唾液再仔细咽下。
本来,这是不该问的。我在大嚼炒麦子的喜悦与兴奋中在这种时候能在无意间吃上炒麦 子真是幸运忍不住地问道:‘你们哪儿来的麦子?‘小个子河南‘职工‘回答说:‘我 们都 在场上干活!‘原来如此。他们不同于那些病号,活得健康自在,只是由于他们有着比别人 优越的生存条件。
这3个年轻‘职工‘,看样子都是略有文化的农民,不知他们犯了什么案子。3人中的另一 个是甘肃人,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在生产队劳动时不慎把队里的架子车掉下山崖,以破坏生 产的罪名判了3年刑。当时,我细细嚼咽着炒麦子,充分享受着这种从未体验过的人生之幸 福,脑际无端地又闪过了阿·托尔斯泰的话:‘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忽然间, 觉得对这段话又有些不甚了然了。但是,管它呢,我继续心安理得、仔细认真地品味炒麦子 无与伦比的美味,真觉得其乐无穷。那令人心醉神迷、回味无穷的咀嚼吞咽活动终于都结 束了,而胃肠的舒适感仍使我心情愉快。须知,这是11月以来我吃上的一次最香、最好的美 餐,小个子河南‘职工‘给我的几大把炒麦子,兴许能顶上我们全天的粮食定量呢。这粒粒 金贵,无比美味,能救人一命的炒麦子啊!
那个甘肃人和大个子河南‘职工‘吃完炒麦子,立即转身走了,几年的劳改犯生活,训练了 他们的警觉性,他们知道这儿不是多待的地方。
小个子河南‘职工‘还和我闲聊了一阵。他说,他常去一个家属家里,给送去麦子。这个 家属有个两三岁的小孩,男人是右派,去高台了,那个家属对他挺好。显然,饥饿的女人用 温情和肉体为她和孩子换来了粮食以维持娘儿俩可怜的生存。我平静地听他说着这些,无以 答对。他还说:‘那娘儿俩怪可怜的,我每次去,她都给我做吃的,她对我挺好,她确实好 !‘他找到了我这个可以倾吐私情的对象,大约十分兴奋,尽管拙口笨舌,仍不能自已地絮 絮地说着。他眼睛明亮,流露出憨厚、真诚的情态。大概,他并未想及他的行为是对他人的 侵犯。他俨然以那女人的保护神的架势向我诉说着这一切。我能谴责他吗?从内心里说,我 也不想怪罪他。欧阳夏的话还回响在耳边:‘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应该说,威胁 我们大家生存的那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小个子河南‘职工‘的谈兴一告终,我们就各自走了。我走进大病房,看见里间屋里的炕上 坐着机耕队的小张,他原是张掖航校的工作人员,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他 来四工农场不久,脸就瘦削下去了。我们原来常见面,他开的拖拉机领柴油都要经我的手。 论说,他工作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我们吃麸子馍、水煮干萝卜缨的时候,由于工作条件 的关系,他一直和干部工人吃一个灶,没受太大的罪。但他个头高,身体棒,饭量也大,在 十工农场放开肚子吃惯了,一到四工农场就受不了。他大概也是取消了工资的人,没 钱再买其他吃食。我和他第一次在场部相遇,他就叫苦不迭地说:‘这儿叫人吃不饱饭,真 受不了,受不了!‘由他的坦率,我又联想到,十工农场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他在习惯的 轨道上行进得久了,已忘了他自己的右派身份。情况变了,他的应变能力跟不上,不能低三 下四,说话又随便,这儿的干部工人能容得下他吗?机耕队丁队长也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坐 坐,我是以语言的谨慎,绝对的谦逊和礼貌,工作上的勤勤恳恳,来获得他和颜悦色的对待 ,小张除了工作上没话说以外,其他方面恐怕都差一筹。这样,人家对他这个‘阶级敌人‘ 起码也是疏远的,有了为难之处得不到原本可以争取到的帮助。他是我在‘医院‘里见到的 唯一的右派难友。
小张一见到我就高兴地问:‘咦,你怎么在这儿?‘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身体垮 了,他们就送我来这儿了。‘说话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还向我打听:‘这儿的条件怎么 样?‘我只好安慰他:‘还可以吧,你就在这儿养着吧!‘这样回答,我不禁有些黯然,也有 点为他担心。不过,看起来他的状况比同屋的‘职工‘病号要好一些。
在大病房里忙了一阵,我走出大病房,只见旁边小病房的门口斜放着一辆架子车,门大开着 ,两个‘职工‘男护士和干杂活的大个子河南‘职工‘,正从病房里往外抬人。两个护士中 ,一个是上海人,前两天曾和我攀谈过几句,对于3年的刑期满了以后仍然有家归不得,含 蓄 地流露过他无法诉说的苦衷;另一个就是曾给过我一瓶鱼肝油丸的武山人。上海人也很年轻 ,看见我,他紧皱眉头,连连摆手,示意我快到一边去,不要过来。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 们抬出来的是一具尸体,他怕吓着了我一个出现在‘医院‘里的唯一女性。但我不想躲 开,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已知农场天天死人。我想,我已承受了太 多的苦难,如今又面临着无法逆料、不允许诉诸语言的大灾大难,我能躲得开吗?看看死人 又怎样呢?苦难已使我无所畏惧,我不必躲避一个死人,要来的一切总归会来临。我忽然觉 得我、这些正在抬死人的‘职工‘,同死人之间并未拉下太大的距离。死亡,不也很平常吗 ?就在今天这个时刻之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有人要永远地离去,而眼下死神却已悄然 来临。一个‘职工‘的死去,没有人为他流泪,也没有任何送别的仪式……因为他的身边没 有一个亲人,他的留场割断了亲人们对他的记挂,对他的悲伤。现在,一切都已终结。不过 ,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再往前走了。这就样,一切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抬出来的尸体毫无 遮拦,几乎是被扔到了架子车上,只见他一头又黑又乱的头发,瘦棱棱的脸细成了长条,从 脸面直到脖子都是难看的蜡黄色,双颊不干不净,眼睛紧闭,一只蜡黄色的瘦手还搭在了架 子车栏杆上。大个子河南‘职工‘拉起架子车,两个护士在后面紧紧跟随,一起往外走,蜡 黄的瘦手跳动了一下,掉到了车里。他们很快地走出了小院,车上的人是安静地找到了自己 的归宿,还是含恨离开了人间?我相信,这些为他送行的人没有谁会跟这寂寞的灵魂进行交 流……他们干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尽管无奈。近来这种例行公事大约干得比较频繁,已使 他们自己麻木不仁。话说回来,我自己又怎样呢?我自己就不同于这些‘职工‘了吗?事实是 ,看着这一切,我也只是呆滞地站在那里,麻木不仁,沉默无语。我闭住了自己的嘴,让所 有的感叹、思绪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只能这样。那个上海人居然还想到我是个女人,试图 阻止我看见死人,他的这份人的感情,想一想,也还有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