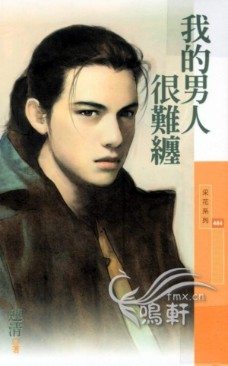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完成任务。1957年我到北 京参观农业展览馆,还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在我,一切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可是,反右斗争使我坠入黑暗的深渊,一下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又怎么能 想得通啊! 经过几个回合的批斗之后,我又一次想去死。我想用死来解脱自己,只有死才能解脱我已无 法承受的重负和痛苦,一个人活到了这等份儿上,为什么还要活着啊!我也觉得在这种时刻 去死太自私,我怎能把所有的苦难都留给他一个人呢?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了,自私就自私 吧,就让我做一个绝对自私的人。我在人世间既已无路可走,失掉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的 一切,我已无可留恋,就让我到死亡之谷去寻找快乐去吧,一旦跨进了死亡之谷,一切就都 解脱了,该有多好!
这是一个上午,我已被停止工作有些天了,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全办公室已没有 一个人理睬我,对我的要求是继续做检查交代罪行,我在沉默中却痛下了去死的决心。报社 附近的酒泉路有个小药店,我决定从小药店买些安眠药结束生命。我匆匆走出报社的大门, 走过中山林的公园时,托儿所的阿姨正带着孩子们在玩耍,3岁的小夏看到了我,大声喊: “妈妈,妈妈……”我头也不回,直奔药店而去。在这种时刻我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小药 店只有个年轻的店员,我问:“有没有安眠药?”他说:“只有一种,三溴片。”我从来没 有吃过安眠药,也不懂三溴片药性如何,问了问每次服用的剂量,就买了多于服用剂量十几 倍的药片。年轻店员大概是看到我神色有异,有点担心地含笑向我一再叮嘱:“这药可不能 多吃,不能多吃!”他不放心地把我送到门口,看着我离去。我回到家里吞服了全部的药片 ,而反应只是头脑昏沉了几天,我没有死。这次和死神握了一次手之后,我又想了很多很多 ……
每天,只有在家里相聚,我们才能悄悄地述说外面的世界不允许说的话,倾吐冤屈,互诉衷 肠。我们的斗室一时间又成了幸福的天堂。每天晚上,他都要伏在案头写人家逼他写的交代 材料,写啊,写啊,总也写不完!那时,他在报社动员鸣放的会上提了的“宝贵”意见,他 和别人私下随便说过的一两句话,他那受到热情赞誉的杂文,等等,统统被认为是喷溅着向 中国共产党进攻的毒液,字字句句无不被认为是毒草,他怎能交代完呢?
我难以理解,一夜之间,他忽然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那么,原来的他呢?那个才华横溢 、桀骜不驯,奋笔为党报写作了八九年的人,是报社从总编辑到每个普通工作人员都 熟识和承认的,即使真成了妖怪,从魔瓶里飞出的那股妖气,也得有个变化的过程。是谁有 那么大的能耐将他一下子变成了从魔瓶里飞出的妖气?况且,我们一直生活在报社的工作环 境里,住在报社的职工宿舍,众目睽睽之下的他,又是怎样变化的呢?
每天晚上,景超还用工整的笔迹写日记,写每天挨斗的情形,写他的委屈,他的痛苦,也写 出那可悲的世相。他的挚友王思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曾对他说,运动对 于被斗的人是考验,对于斗人的人也是个考验。在反右斗争中,他也有了自己真切的体会。 报社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是反右斗争的重点,人人自危。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惜 捏造罪名,把污水泼向已被众人踩在脚下的景超身上;有人善搞落井下石,得意愉快;有人 作批判发言时,神色慌张,说话结巴,大汗淋漓,倒像是受批判的是他自己……这些,他 都如实地记在日记里,他想郑重地把这一页历史永远地保存下来。
8月8日,甘肃省市新闻出版系统召开批判右派分子大会,就在报社礼堂举行。这是一次把新 闻出版系统的反右派斗争推向高潮的大会。大会未开始前,革命群众就要求各单位的大右派 “亮相”,让坐在前排的他们一个个站在方凳上,以便大家认识其嘴脸。景超是头一个站在 方凳上让大家争睹的对象。后来,又有人喊道:“叫黑社头子王景超的老婆和凤鸣 坐到前边来。”我本来坐在不引人注意的中间靠后的位置上,这时便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站起来走到前边。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省上的王秉祥。1951年庆阳土改时,王秉祥是庆阳地 委书记,景超作为报社挑选派去的记者,写了几篇好通讯,如《二十串麻钱》等,当年, 王秉祥对景超也是熟悉的。现在,景超作为甘肃日报社的头号大右派站在方凳上让会场所有 的人观瞻,此时的王秉祥对景超这样的大右派也许始料不及,但参加大会将他批倒批臭,似 是理所当然。我心里仍替景超难过,他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开完大会,回到家里,我仍有些忿忿不平,说:“他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站到凳子上?看一下 你们的嘴脸,就能把批判引向深入?”然而,景超竟还宽解地说:“群众运动嘛,这有啥?”
《甘肃日报》8月9日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此次会议。
两天后,省市新闻出版系统批判右派分子大会继续举行。《甘肃日报》仍在一版报道,消息 指出:“以王景超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在今天的会议上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在确凿的证 据面前,这个‘黑社’的头领王景超不得不承认这个集团的存在……但是,王景超却仍然 抗拒交代这个反党集团的具体活动。王景超这种无耻抵赖,顽固蛮横的态度,引起全体同志 的极大愤慨。”
此后,对“黑社”的追剿围攻,便又上了个新台阶。
景超在参加革命前,生活很苦。他生于1924年,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侵 略者的炮火,将他逼出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18岁的大哥景衡带着13岁的他为躲避战火 ,流落到四川等地。大哥后来参加了抗击日本鬼子的商震部队打日本鬼子去了,13岁的他生 活无着,经老乡介绍,在伤兵医院当了看护兵,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伤兵医院吃不饱饭, 小看护兵们为抢几口饭,常在饭篓子旁打架。后来,他从伤兵医院逃跑出来,在国民党为沦 陷区学生办的国立中学从初中到高中先后上了三四年学。学校说是管伙食,肚子仍吃不饱。 西安解放前两三年,经过刻苦学习,他考入西北大学。此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他认定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西安解放,他很快报名参加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随军西进。
敌军仓皇西逃,沿路烧杀淫掠。景超他们走过的地方,处处满目疮痍,十室九空,炉灶被 捣毁,炊具被砸烂。在一个镇口,一个老汉捂着刚被解放军包扎好的伤口,哭诉说:“马家 军(指马步芳的军队)把我全家杀光了,我活着有啥用?大军同志!请你们为我报仇哇!”这血 泪的控诉,在景超和工作团全体同志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烈焰般的阶级仇恨,队伍里响起了《 解放大西北》的嘹亮歌声。
在西进途中,景超热血沸腾,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行军驻扎到了张家川回民聚居地区, 领导上向大家讲了党的民族政策,告诉大家,回民喝水有讲究,我们喝河里的水,要到下 游去取水,不能饮用村子附近河里的水。此时,经过一天的行军,人人都累得动不了了,景 超拿起一个脸盆,独自跑到河水下游,舀起一脸盆(行军中无其他盛水的用具)水,端到屋内 ,供大家饮用。有一位同志不慎把手碰破,血流不止,围着几个人,都不知该咋办,景超看 到,不多说话,把一条干净手帕拿给他,让他包扎,自己又去赶前面的队伍去了。
西进的路上,领导上还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一次学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 话》,让大家讨论。景超对该文后面的一段话感触很深,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作出 如此英明的论断。这段话是:“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 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 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他谈锋很利地说了说自己的深刻体会,当时就有点语惊四座。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也成为他处 世做人的原则。
行军到兰州城外的东岗坡时,同行的徐列出了件危险事。当时,大队人马沿着盘山道顺利前 进,有些年轻人乘着一股猛劲,从陡峭的山崖上往上爬,速度很快,徐列也从山崖上往上爬 ,走了一段路,却怎么也动不了了。稍有不慎,就会掉下悬崖。此时,左近前后都没有人, 徐列正在紧张万分之时,已上了山崖的景超一回头看见了徐列,就慢慢退回,要拉徐列一把 。山路很陡,走上去后,很难再走下来。最后,是徐列把背着的一杆“三八”式长枪递上去 ,景超拉住长枪,用力一拽,才使徐列脱离险境。50年过去了,徐列还记着当年那危险的一 幕。
到“8·26”兰州解放,他随工作团进了兰州城。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他参与了《 甘肃日报》的创办工作。在编辑部,他才华出众,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新闻和通讯,受到从 总编辑到普通工作人员的瞩目。
曾几何时,他又成为“黑社”头子,成为对党抱有刻骨仇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受 到全报社以至省市新闻系统多日来的猛烈批斗,还要他站在方凳上让大家观瞻。天啊!这瞬 息变化的世道,让我怎么能接受呢,景超他自己又怎能接受呢? 过了几天,我下班后回到家里当时的上班就是准时到办公室挨斗或写检查交代罪行,看 见景超躺在床上,屋里一股浓烈的六六粉味。六六粉是数月前要来消灭臭虫的,此时,六六 粉纸包已从床下取出打开了,我哭叫道:“你是不是吃了六六粉?是不是吃了?”他脸色煞白 ,心情沉重,看到我着急哭叫的样子,悲怆地说:“我刚才想吃下它,还没有吃……”他 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说得很吃力。多日来毫不停顿的狠批猛斗,他活着的勇气也已消蚀殆尽 ,刚强的他终于也想去死,用死来了结一切……我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此时此刻,我 真害怕失去他。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吗?我们想要活下去真也太难太难! 他冰凉的眼泪流到了我的头发上,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也是生平在我面前唯一的一 次流泪。他告诉我,下午的斗争会上,要他交代“黑社”的黑纲领,“黑社”本来就是莫 须有的事,哪有什么黑纲领,他无法编造,交代不出来,就骂他“耍死狗”、“放屁”。他 沉重地喘着气说:“这日子可怎么熬下去!”在绝望中,我抽噎着哭成了一团。这天晚上, 我们没吃晚饭,连灯都没开。在绝望的哭泣中,我们觉得彼此都无法离开,也感受到了大难 之中相依为命的甜蜜,一种未曾经验过的甜蜜。
反右斗争将我们双双打倒在地,这真是我们来到人世间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难以承受 的苦难,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迹斑斑,而两个受难的灵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 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