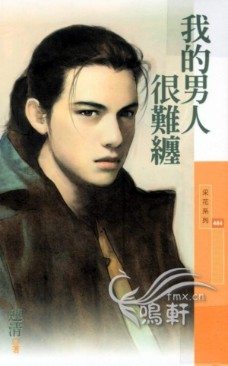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惨孑然一人。90年代初,我和徐福莲回 忆这一事件,徐福莲记忆犹新。她说:“我陪着陈尔云流了不少眼泪!”当时,她的小女儿 随婆婆已去了广东,她那曾是印尼华侨的婆婆是广东人,对故土有着特别的依恋,原先不远 万里来到甘肃追随唯一的也是她认为儿女中最有出息的儿子,是想在儿子儿媳身边过上安稳 的生活。反右斗争使儿子儿媳双双划为右派,老人无法再在永昌安住下去,只得回老家依傍 女儿们去了。所以小徐陪陈尔云流泪是哭他人的难肠,内心里暗自悲伤的真正是小女儿已去 万里之外的广东,自己前程未卜,对小女儿无论怎样牵肠挂肚也难以见上一面了。这种母女 被活活拆散不得见面的痛苦,比之已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同亲人永别了从而留给亲人的痛苦, 究竟哪一种更加令人痛断肝肠?
再说,陈尔云一家那时只知道戈壁深处人们生存的艰难,生活的严酷,却根本不晓得将人们 圈在这里的戈壁滩凶残暴烈的秉性。从古到今,它曾无情地吞噬了多少活泼泼的生命,已是 无以计数了。
这一惨剧给所有的上海移民的心头都罩上了撕不开抹不去的巨大阴影。这也是我来农场后遇 到的第一桩触目惊心的暴死事件。许多日子,我的心里老是翻来搅去的,难以恢复平静,孩 子们的惨死,让人无论怎么想也觉得太可怜,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9月,《甘肃日报》发了一条给全省首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新闻,字数不多,摘帽的人数也 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我中学的英语老师李端严,此时他在兰州大学任教。这条发在一版不 甚醒目的短新闻,在我的难友中,俨然如一声春雷滚动在每个人的心头。人人争相传阅这张 报纸,并当做最大的喜讯,互相转告。“摘帽”毕竟有希望了,回到人民的行列已指日可待 !
农场肯定已收到有关的文件,不久后就要求对下放人员一一进行鉴定。这自然是一次非同小 可的鉴定,它关乎到“摘帽”。鉴定在各组进行,然后集中到中队进行平衡及文字上的修 正定夺。
我对于首批“摘帽”未抱什么奢望。首先,我衡量了一下自己,从劳动上来说,男同胞们绝 大多数都比我强,我虽也尽了力,总的来比较只是一般过得去。其次,我当右派是受景超的 株连,作为夫妇右派,领导上按照当时的释义只会考虑其“反动”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因而 会把我们的问题连带在一起,继续株连,绝不会优先考虑把我一人先解脱。所以,我在思想 上比较冷静,没有太多的波动。再次,我也想到省上首批“摘帽”的人数极有限,农场步其 后尘,人数也不会多,所以轮不到自己头上。
有些人并没有如我这般冷静,特别是有的人自认为劳动上拔尖,又是原共产党员比我等 非党员要清白一等的人,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变得心慌意乱,坐卧不宁。一 组的王永就属这种情况。一个休息日,他特意到队部和我谈心大概和本组的难友坦诚地 说话有某种不便吧,他的困扰全摆在了脸上。过分的希冀使他兴奋不已,害怕希望落空又使 他忧心忡忡,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折磨得他十分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 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坠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想抢先抓到自己手里争先活命。我只得从大局 方面开导他,说这次“摘帽”的人数不会多,他年纪轻(比我小一两岁)劳动表现好,经常 受到队上的表扬,估计此次优先“摘帽”的可能是有的,但人数既然少,不摘的可能也存在 。农场“摘帽”的决定会在国庆节宣布,也没几天了,就安心等待吧!反正着急也没用 。像王永这样内心着急、坐卧不宁的人,肯定还有不少。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前程命运的 大事,是领导上要求的“跌倒了要再爬起来”的标志,只有“摘帽”才能从屈辱的“阶级敌 人”重新进入人民的行列,从而被称作“同志”,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真的,这是多么令人 欢欣鼓舞的事儿,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毕竟有了一线曙光,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
1959年的国庆节终于来临。这一天,我的难友们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在庆祝会的盛典上宣 布摘帽的决定。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宣布摘帽的在全大队只有两人,一中队的李永龙,二中 队的一人,名字已忘记。李永龙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劳动上比较踏实,但不属于拔尖 人物,所以他作为首批“摘帽”的人,很出人意外。当时,我的难友们都还抱着在较短的时 期内争取摘帽的想法,语言比较谨慎,故对此也不多做评论。在全中队四五十个右派分子里 只给一人“摘帽”,似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给大家兴奋的意绪泼了凉水。
场部所在的三大队,此次也只给两人摘了帽:一人是陈明,他从武威步校来农场不久,就来 到场部三大队当伙食管理员,无论是大跃进的食堂化时期,还是此前此后,他都工作得勤勤 恳恳,想了许多办法,把场部及三大队的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伙食大为改观,这是有目共睹 的。此食堂吃饭的人在千人以上,伙食办得好,还被评为全场的“红旗食堂”。陈明首批摘 了右派帽子,这是情理中的事。但陈明对此反应平淡。他对自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未服 气 过,从未承认自己反党。原共产党员的他,于5月下旬送到十工农场后不久,立即给原单位 领导写申诉书,提出充分肯定的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一个正直正派的共产党员,从未同党 有过二心。对农场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他尽心竭力一定干好干出突出成绩,是由于他认识到 这是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经受一场特殊的考验。他仍然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和热情,任 劳任怨地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对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淡然处之,嘴里不说什么,心 里清清楚楚,他相信逆境会进一步转好,自己听毛主席和党的话没错。他就是要以共产党员 坚定的步伐,把革命的路走到底。另一个是马思聪,他与大音乐家马思聪同名同姓,但却是 土得掉渣儿的陕北人,父亲是老革命。他到十工农场后就在汽车队开车,看样子是农场领导 因其父亲是老革命而对他的特殊照顾,或许农场领导就认识他父亲。开车,不像我们下地那 样苦重,手握方向盘驰骋在满世界,又是自由度多么大的工作呀!在三大队时,我和马思聪 只有过遇面,从未交谈过,只听说他原来是张掖地区某运输公司的干部。就是这个马思聪, 在领导上宣布摘掉其右派分子的帽子时,竟直言不讳地大发牢骚:“我本来就不是右派分子 ,摘的什么右派帽子!”别人求之不得的“摘帽”,在他竟嗤之以鼻。又有哪个右派分子从 内心里就承认自己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时,被首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 ,在数十万右派分子中属凤毛麟角,人人只有庆幸的份儿,谁敢把内心深处的秘密公开道出 !马思聪敢于说出内心的真话,也只是在他认为同样与他受冤屈的难友面前。他到农场以来 ,自由惯了,没有谁敲打过他,他觉得说出真话痛快,便痛快地说了出来。
当时,只有“摘帽”的指示,对“摘帽”后相应的对待,如工资等最实际最直接的关乎到本 人生活及家庭的问题应如何跟上,并无具体措施,所以,直到我于1960年1月离开十工农 场,摘掉右派帽子的李永龙还是李永龙,工资还是按30多元的生活费由我每月造表发给,数 额并无任何改变。其他一切也没什么变化,他仍留在一组和大家一起劳动。
收割后的农事活动,主要是用大车把麦捆子拉到场上摞好。这来农场后的又一个大丰收,使 或圆或长的大麦摞,一个接着一个,光是在一组东边的场上就有近20个。我曾同场上劳动的 人一起摞起一个个的麦摞,在摞麦摞的底层时,一手提一个麦捆按照既定的形状摆好就行, 摆到一定的高度时,有人站在麦摞上指挥,下面的人用长柄木杈把麦捆送到需要的地方,由 上面的人接住放好。此时,站在上面的人是有技术的“把式”,既要把麦摞摞稳防止歪斜坍 塌,还要把麦摞摞得进不去雨水,有了雨水要顺顺当当地流下来。这种工作有相当的灵活性 ,不像割麦时要赶趟子,所以我能够胜任愉快。以后,摊场、碾场、扬场的全过程,我都参 加了下来。以前,我下乡时听说扬场的技术性很强,还见到农民扬场是用特制的木锨来扬。 这里根本没有木锨,大家全都用铁锨扬场,我学大家的样也用铁锨扬场,未曾料想还得到陶 杰的一声赞誉:“我发现统计扬场的姿势好看得很!”陶杰从我劳动的身姿发现了“好看” ,还坦率地说了出来,使我十分高兴,毕竟我是正当青春年华的女性。我一面继续扬场,一 面心里想道:“原来,劳动着的自己还‘好看得很’,陶杰你怎么就发现了别人所没有看见 的,还要说出来!”我喜欢陶杰的坦率热诚。
后来,全队的人马又一起转悠在沙枣树林里,用了两三天的时间采摘成熟了的沙枣。采摘沙 枣是为了收集沙枣子,为明年种植沙枣做准备。这是县上安排的任务。干这种活,真如度假 一般,大家说说笑笑,逍遥自在。略带涩味的沙枣,嚼在嘴里有几分甘甜,这对于一向无零 食可吃的我们,也多少可以解解馋。收集回来的沙枣,队里用碾子碾过,取出子儿上缴,碾 碎的沙枣泥,交给伙房夹在面团的夹层里蒸馍,自有一种酸甜的特殊味道,十分可口。我生 平第一次吃上了这种用沙枣泥做的馍。
这个金秋的尾声,在我记忆里十分鲜活的,就是在采摘沙枣中手指间曾不断滚动着黄澄澄的 沙枣,嘴里不停地吃着黄熟了的个大滚圆的沙枣。有时遇到沙枣味儿特别甘甜的一枝,左近 的人还关心地互相让品尝比较,顷刻间便把缀有沙枣的枝条扯个精光。
就在本书完稿之前,我得知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有两个饥饿的难友在这一年里被残 酷整死的事。第一个难友名叫郭斟玉,1959年3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去酒泉城附近背头年 晒干的草筏子以改良土壤。当时,早晨5点半起床时天还没全亮,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 了许多稀米汤,不限量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喝了不顶用,后来就有人想 了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用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 了,小米和谷糠留在毛巾上。把滤过的小米取出,放在另外的地方,再端米汤倒在毛巾上, 再滤出小米。这样倒几次米汤之后,就能滤出没有水分的小米,吃进肚里还顶点用。这种 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就将倒了几次米汤的郭斟玉抓住了,从他放在地上的短大衣里搜 查出一堆滤出的小米。此时背草筏子的劳教分子尚未出发,当即将郭斟玉吊到了 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6小时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 了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第二件事发生在冬天。有个难友,因饥饿,从菜窖里偷了一个老番瓜、几个洋芋,晚上在屋 后偷着煮,被到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