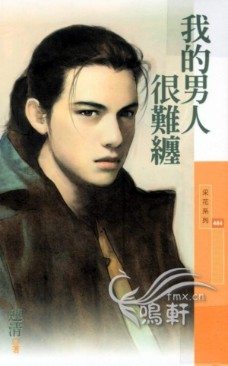经历我的1957年-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净。不仅我,我的几个女伴从地里扛回的铁锨都明光锃亮。
锄草比拿铁锨平整土地要轻多了,开始锄草时,因为手不顺,干一阵胳膊就疼得不得了。干 了几天以后,甩动锄头灵活自如,胳膊也就不怎么疼了。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又出现了。这 里农田周围的草丛里生长着一种蚊子,个头大,叮人很凶。我们锄地时,蚊子便成群结队 而来,肆无忌惮地袭击正在挥汗劳动的人,每一个人的头脸胳膊直到手和脚背,都是蚊子袭 击的目标,蚊子将它尖利的针形口器插进皮肤时有刺痛感,你旋即注目看刺痛处,蚊子的肚 里已灌 满了鲜血,变成了殷红色,如你迅速拍去一巴掌,手下便会出现一小团血迹,用你自己的鲜 血染红了的血迹,蚊子已丧生。而在大跃进的年代正大干苦干抢速度争时间的我们锄地是顶 要紧的,驱除蚊子不能影响锄地的进度,这就很受苦了。
我最怕蚊子叮咬。记得1955年在天水农村采访时,那里蚊子多,我的皮肤对蚊子特别敏感, 有一次蚊子在手腕上咬了一口,很快就肿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大疙瘩,竟大如手腕一般粗。有 个农村医生大约因为我是记者,还特意打了一针青霉素消炎。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是,在 天水田家庄采访时,夜里常有蝎子在房顶和墙上爬行,有时还会掉在床上,使我胆战心惊。 那时,我和一位毕业于农业学校的年轻姑娘同居一室,她来自江苏,每天奔忙于田间地头。 她 推广玉米异株授粉,我还和她一起干过,眉户剧《雌雄花》里推广的技术,那时我就很熟悉 了。这位姑娘工作上泼辣肯干,真想不到是位南国来的姑娘。我们同居一室,屋内支了两张 单人床。这间小屋就在农家院内。头天夜里,我们都已上床,熄了灯。我听到墙上有 不知什么虫子在爬行的声音,她听到后立即警觉地用手电筒照,啊呀,这一照我立刻看到 了一只大蝎子!她利索地用一把长把的扫地笤帚把蝎子扫在地下,用脚踩死。蝎子用有毒的 尾巴蜇人真是怕死人,这夜我心惊胆战,一直怕得睡不好。以后几天,也一直睡不好。有一 夜,从房顶上降落及从墙上捕捉到的蝎子多达5只,有一只就落到了我的床上。每次捕捉踩 死蝎子,都是那位姑娘干的,我显得很无能。
此一时彼一时。在三大队锄田时经受蚊子的袭击,凡是蚊子叮咬过的地方,都肿起了一个个 的大疙瘩,胳膊手腕上的大疙瘩都连成了一片,又痒又疼,非常难受。我再也想不到人世间 还会有这等苦楚,对蚊子的围攻竟莫可奈何。
有些男同胞们用纱布毛巾围在脖子和脸面上抵挡蚊子的叮咬,我把袖口紧紧扎住衣领翻起, 也算是一种抵挡,可这样的抵挡又顶多少用呢?每天收工后,身体的疲劳已容易恢复,被蚊 子叮咬后又痒又疼火辣辣的难受劲,令人心烦意乱。好在不久,我和小徐被调到畜牧组养鸡 兔,才躲过了被蚊子叮咬的苦楚,再未遭罪。
来四大队后,我未参加过锄草。四大队一中队以种麦子为主,凭靠人力锄草不顶啥用,多次 深翻过的麦田,除了骆驼刺,杂草很少。所以锄草在农事活动中无甚要紧。
在麦子齐刷刷地挺直了腰杆,大田里绿油油的麦浪不时泛起波涛之时,麦子已开始孕穗。为 了让麦穗灌饱浆子实粒大,一中队组织强壮劳力进行收割前的最后一次浇水。我对于自己没 干过的活有些好奇,在三组浇水时就讨了一份差事,给地里连续浇水不能回来吃饭的人送馍 去。浇水是苦活,日夜连续干,有时也很紧张。食堂里做了大大的白馍,按人数数个儿让我 送去,自然我也有一份。
我找到了王昭他们浇水的地头,只见潺潺流水正向低矮的地埂围成的一方方麦田里流去,流 满一方,便把地埂铲开一个小口,再向下一方浇灌。王昭告诉我,当流水徐缓地向麦田里流 去时,要到处巡视,看地里是否有流水急速旋转,直向地下流去的情形,如有,就说明地里 有窟窿,在流水旋转的地方急速用铁锨往下捣几下,把窟窿堵住。我下地时提着用炊事员的 围裙包着的十来个大馍,也扛了一把铁锨。按照王昭的吩咐,我便在地边巡视着,发现流水 旋转直下的地方,学王昭的样儿,立即用铁锨猛捣几下。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王昭一起巡视 ,边干活,边聊天。这活除出现意外的紧急情况,一般可以说是不紧不慢。此时,气候正宜 人,不冷不热,时而有微风徐来。设若我们的思维还如两年前那样,稚嫩,单纯,无忧无虑 ,一无挂牵,这该是一幅绝好的田园风情画。然而,我们久经压抑的心境终究难以豁然开朗 ;由于我们对不可知的未来还有所期冀,又使我们无法游戏人生。尽管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 闲聊,总也聊得不是那么开心。
我们面前一方方的麦田终于自近而远都灌足了水,大渠里的水要改道,这就要把流向这边地 里的水口子堵住。由大渠流向地里的水口子大,必须用铁锨铲起三四铁锨的厚土快速堵到水 口子上,方能堵住。这需要猛劲,王昭自然一个人就干了,不需我动手。
当火红的太阳将坠未坠之时,满天彩霞。绿油油的麦田里一片灿烂,灌水的田里泛起了金光 ,被麦子婆娑的叶秆明明暗暗遮蔽着的水面上,到处都是美丽无比流动着的图案。这画中, 也流动着我们珍贵的青春年华。
我乘兴而来,在这美丽的画儿里劳作沉吟,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黄昏,暮霭从天上轻轻撒落,先落到了麦田里,麦田变得暗淡了,绿油油的光泽在渐渐隐去 ,只有潺潺流水仍在不住地低语,如幽如怨如泣如诉。流水啊,农场的各种作物都靠你滋润 补养,延续生命;你是一首不朽的乐章,为什么在你悠悠的生命历程里也会出现令人叹息伤 悲的长调?古代的文人墨客常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而慷慨悲歌,在潺潺流水 的低语中,我感知的,似乎是一种更深沉、更悲壮的内容。我忽然悟到了些什么。
在暮霭的飘落中,我独自扛着铁锨,从田间小路转到了行驶大车的土路上疾步而行。极目远 望,天际还有一抹灰白色的亮光。
我想极力摆脱方才纷繁的思绪,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也不愿去想得很清楚的那些纷繁复杂 的思绪。人啊人,人为什么不能简单一些地去思维;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就不能由人 们自己把它想个透彻呢?
我还是尽量控制自己,不让乱如飞絮的思绪自由飘散,因为此时的我,深知在农场已拥有的 自由是何等的可贵,而这种自由也是绝对地有限度的。我要保护自己,最重要的还是思绪要 定格,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平静自己,心里却响起了一首歌: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云雾在荡漾,
微风轻轻吹来,
飘起一片麦浪。
我是每日每夜里,
永远不断地盼望,
盼望远方的友人,
带来珍贵信息。
理智可以使我把握自由飘散的思绪让它凝滞,情感却不是任自己随意驱使的奴婢,这不是, 它以一首歌儿的旋律回荡在心头,使我禁不住地也低声吟唱,悲凉哀惋的情调,由节节高亢 的尽情抒发,到最终坠落在低低的叹息声里。这叹息无穷无尽,没有了休止符。我沉浸在这 悲凉的氛围里,在暮色渐浓中,忽然觉得所有对亲人的思念,都化成了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的无尽暮霭飘落而下,使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真愿在这无尽的暮霭里失落自己……这世 界为什么硬是给了我一个生存空间?万般无奈,万般痛苦!啊,渺小的我,我将怎样苦苦地挣 扎下去哟!
刚才那首歌,是我初到农场不久时学会的。50年代的我,既做了年轻的母亲,又忙于工作, 连学歌的时间都很少。到农场后,最初听武威步校徐保安、靳清义他们唱这首歌,觉得也能 抒发些自己的离情别绪,跟着他们哼了几遍,也就学会了。他们在武威步校时,一个个青春 年少,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在年轻人里属于拔尖人物,各方面都很称心,正意气风发时节, 唱歌也很能抒发他们的军人情怀。十工农场接纳了他们以后,也许只有这首歌最能抒发他们 孤独寂寞的心情,他们拣起了它,反复吟唱,而心境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一场反右斗争的 风暴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友人,不会有哪个友人寄书信给他们。不过,他们远在数千里之外 的亲人,仍然情切切地日夜挂念着在农场受苦的他们。他们的亲人大都文化不高,不会用抒 情之笔详细地写出他们的思虑担忧的心迹,写出他们无以言表的相思之情。此时我已得知, 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是共产党员,党组织理所当然地要她和右派分子的丈夫在政治上划清界 限,而她自己心里明镜儿似的,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受了大委屈,仍然把丈夫当做依靠,当做 贴心人。在简短的书信往来中,她倾吐心曲,也只是表现在对丈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问丈 夫劳动能不能支持,需要什么不。她在信里讲的最大的“政治”,就是提起那个年代对丈夫 常用的一句套话:“安心劳动,争取早一日摘掉帽子。”靳清义的言论,主要是说党在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正如人的肌体上长了瘤子应动手术割掉,我们的党才能大踏步地继续前进。 到反右斗争中,他的这些言论被歪曲为政治工作犹如人身上的瘤子应予割除。靳清义本人就 是政治教员,原来的言论被歪曲得翻了个个儿,他有口难辩,就这样当上了右派。靳清义是 独子,他无法向家在农村的高堂老母从信上把这一切说清楚,就只得向母亲隐瞒了真情,母 亲压根儿没想到儿子会成为右派。那时下放农场劳动已为全国人民所知晓,老太太以为儿子 只是下放劳动,虽隐隐约约觉得内中有些蹊跷,心里想这或许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儿子不提 说,她也不能问,也不好往坏处想。对于20多岁就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她心里只有骄傲和 敬重,从来不向儿子提说什么,包括儿子的婚事。当了上尉军官的儿子的婚事还需她这个待 在农村的娘操心么?
这天晚上,我摆脱纷乱的思绪仍很快入睡了。半夜里被尿憋醒。厕所在队部后面,要走过三 组的宿舍,经过一个狭长的过道。我怕遇上男同胞,急急地把上衣长裤都穿整齐,才奔出房 门。可一走出房门,就见地上月光似水,深蓝的夜空飘着大片大片像棉絮似的白云,这白 云又似被一支大毛笔刷了几下,变得丝丝缕缕,由南到北飘散而去。我忽然觉得心里酸楚万 分,疼痛不已。我远方的亲人,你们可知道,此时此刻,孤独的我是在怎样的痛苦中思念着 你们。在深邃寥廓的夜空那一方,那个更寂寞更孤独的灵魂,一定也是在想着我的,男子汉 的他,此时此刻,心里一定也很苦很苦,比我更苦……命运之神,你为什么如此残酷地撕裂 我们流血的心?我不禁驻足而立,望着天上明亮的大半个月亮,心里发起狠来:月亮月亮, 你如没有了光华,天上地下都是一片黑暗,每个受难者心里都混沌一团,该有多好!人如果 倒退到猿,我们肯定就不会有如今的痛苦了。让我变做猿猴,变做戈壁滩上冰冷的石头!为 什么我竟是个有感情、有思维的人,我还是个女人!天哪,天哪!
这瞬间的痛苦和思绪,是一泡尿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