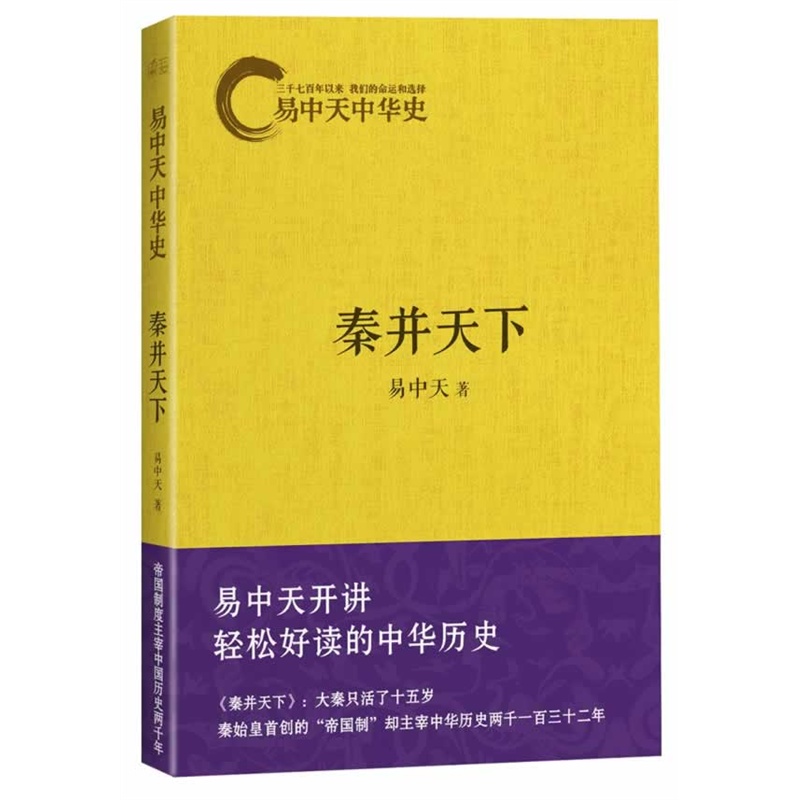ʦ��:�سǼ�����6601�ŷ���-��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1966������ұ�ת�Ƶ�̫����ֶ�ʮ���ţ��˴�����һ����Ժ�����������ֻ����һ�Σ����ǽ������������ң�������ʲôҪ����״����εȵȡ���
������ס�˲������꣬�ְ���ת�͵�ѧԺ��ͬ�������ǹ�����һλ�ɲ�ס�ҵĺ�Ժ��ǰ����ͨ��������ס�˲��������£���1966���°��꣬���ĸϯ��ȫ��֮�ʡ�������ʱ��ʲôҲ��֪�������㱻�ͽ����سǼ�����������˵���ǵ�ʱ�ι�����������л���εľ�������
���سǣ��ҵı����6601����1966���1�ŷ��ˣ�����ʱ���������Ѻ����ȷʵ���٣�����¥�������š������ҵ��Ƕ���¥��յ����ģ���Լ����ֻ���������ˡ�������Ĵ�����ض�һ�˶�ߣ�����Ǵ�Զ��������һ����С�����е�һ������
�Ҵӱ��������ؽ������Ժ��һ��ʱ���ڣ����˾����ϵĴݲк�ѹ�����⣬�����ϵı����൱�ߣ���ʳ�ܷḻ��
��
��������ҵ�ֻ��һ���ˣ����˿������Ϲ�����Ա���о��飬��������ÿ�춼Ҫ�����Σ�һ���Ҫ�ҳ�ȥɢ����һ���Ҫ��ȥ�������Ͷ�������������ʱ�����������ң��˺ܺ�����˵������Ҳ�������飬��ʱ��ͬ����̸���졣�������ϵ�һ��Ҫ�������������ҡ�����Ҫ��һ��Сľ����ֽ�š����顢��̨�Լ�������þߣ�����һһŪ���ˡ���һ�죬�������������������������Ѻ�ĵ�Ȼ��������ķ��ˣ��������������˹������������𣿡����ش�÷dz�������ǹ��ҵ���Ҫ������������������ο����˵���������ˣ��Ͱ��ĵش��Űɣ�ע�Ᵽ���Լ��Ľ�������ʲôҪ�����ң������������£��Ҷ�������Ϊ����
�����Ļ��Բ�����ȷʵ�ǵ�ο�塣��
���Ǻþ���������Լ1967��11�¼䣬���˲��ӣ�ʵ�о��ܣ�½½����������ԭ����ȫ��������Ա������1968�꣬��˵ԭ����Ƴ����Ա�Ѿ�ȫ�����ˡ�ѧϰ�ࡨ����
�سǼ�����Ȼ�����ա��ڲ���һЩ������������ǼȲ���̣ܽ�Ҳ���ᰲ�Ź�������ֻ����һ���£�������ĥ�ˡ������ˡ����ˡ����С����֮�ࡣ���Ƕ����е���Ѻ��Աֻ��˵һ�仰�������Ƿ���������
�����Ƿ������ӡ������Ƿ�����һ�䣬���������ʣ������Ƿ�������Ϊʲô���������������ȥ��û�ţ����ǰ�����ô�ġ������������Ƕ�ô���ĵߵ�����
�Ѿ���һ���û����ͬ�Ҿ����ˡ����Դ���Щ��������������Ϳ�ʼ�˴�Ե�ʡ�������ֹ��������ĥ�����Dz��ϵع������η����ţ���ʹ����Ϣ��ʱ�䣬ҲҪ���ѣ�ʹ��������������Ϣ����ʳҲֻ������ͷ���̲��ˡ���
�����ƺ��Ѽ������������������ֳ���һ�����ݺ�*����һ���ˣ��д����µģ�Ҳ�д����µģ���������Ͽ����������裬���Ǿ��ˡ�
Ȼ������ȴȴ����˵�������������ģ������ٵĻ����٣�����С�������ǰ������һ���ܻ�������˵���˼���ʹ����ˣ�ֻ�ܲ��ϵ��ظ��Ǽ��仰���Բ��������㡣ʱ���������������ꤻ�����ȥ����
�����ڴ��ʲ���˾����쳹����ʱ������ʶ����Ƭ���䵽�ҵ����ϡ��������Լ���ȡ�������������˽�����������йص��£��Լ���ͬ��������������ϸϸ���������д�ˡ�ƪ�����Ľ������ϡ�����ȥ֮��ȴʯ��������Ӧ�����˴�Լ�������£�����һ���ˣ�ָ���ҡ�
�����������ס��������ؾ��ᡨ����û�н��������ϡ��ȵȡ�������������������⡢����Ҫ���������ش�ֻ��һζ�ؾ�������ѹ���������ˣ�����������ȡ�������������ģ���Ȼ������ĥ�㣬�������������������µ�һ���ֿ�ʼ�ˡ���
�������ǵ�Ҫ���Ұ���д���ġ�������������д��һ�飬��Ȼ���ǡ������˾������������˹ء���
ÿ����ͬ��̸���ģ�ȫ���Ǿ��ˣ�����½���ա�������ڣ������ָ����ֶ��С�������������������⣬ʵ����Ҳ����κξ������⣬��ֻ��һ�����ء�äĿ�ش߱ơ���ѹ��á����ǵ�������е����㣬����Ҫ�ұ��죺����λ�ͬ�����淴��ë��ϯ�ġ�������Ū�������ǵ���ͼʱ���ҷ��ʵ�����ǰ�������ǻ��˺ܳ�ʱ�䡢˵�һ���߸ڷ��������棬��������˵�һ�ͬ�����淴��ë��ϯ�����ʣ��ҵ����Ƿ��������棬���ǻ�ͬ�������أ�����λ���Ž���������У�����پ���ֱ��׳�ػش�˵�����Ⲣ����ܣ�����ʹ����Ц�Էǣ�����ͬ����˵���һ�������𣿡�
�̶���������ͬ˹���ֵġ������ϵ�����ҷ��ʵ�������˹����Ҫ��������������������'���ش�˵������Ȼ����˹�����Լ�������������������������ġ�����˵����������Dz��˽���������ôҲ���Ը��������й��Ĺ����쵼����ί�Ĺ�ϵ������������һ�룬˹������Ϊ�������䡢���ҵ�����쵼��������ȥ��������������������ǵ�������Ա�Լ������κ��ˣ�˭�Ҵ���˹���ֵĿ��ˣ���������ãȻ�ˡ���
���ǣ���Щ�������ˣ���Ϊ���˵Ĺ��ߣ���������ƴ���ء������ܵ����ɡ�����սû��ͣ��ֻ����Ҳ���������⣬һ����ѹ���ơ��ߡ��������������������졣���˵ڶ������죨1968�꣩��������ҹͻ�����ַ����ƣ�һ�̲�����Ϣ����
�ұ�����һ��С������Ŵ����գ��������ȣ��¶ȸߴ�40�����ϡ����Ǵ���ȣ�ֻ���������Լ�������������ǽ�ǣ�����ǽվ�������������������˶�ʮ���죬�ҵ��������ź��ף�ѪҺ�³��ٻ���Ѫ���������������������ѿ�Ѫ�ڣ�Ȼ��ŧ�������ǰ�ĺ����Բ����ڶ����Ȳ�����Ϣ��Ҷ���þ�ҽ����ʱ�дӡ�ѧ��ࡨ�������Ķ�����Ա�����ҵ��������أ�������ҽ���������ģ���λҽ������������ɹá���
����վ��������Զ�ĵط����������ң������Dz��Ǻ���÷�������ⲡ���Ķ���Ⱦ���ģ��ⲡ�跨�Σ�����Ҫ����������ͱ��������Լ�����������Ҳ������ת�����ˡ���������
Ұ��������������ȴ�����������Ȩ������������ȴ���������ϵ�Ȩ��������Ȩ������������������ʵ����˷��˵�Ұ���о���������Ͷ��·��������ҵ�ȷ��������ɱ����ͷ��
������Դ���³�����
��������������֮�ʣ���Ҫ�ع��Լ���һ�������������Ⱥ��ߣ���ҪѰ���ⲽ��ص�ԨԴ����
���������Ļ��������У��Ѿ����������Լ����µĻ�������������Ϊ�ҶԿ����˽��̫���ˣ������ڽ����ӡ�����֮�⣬����һЩ��˿�������Ҷ�����������
1950����1952��䣬�����Ϻ��Ĺ�����Ա��������һЩ�л�����Ҫ�Ƕ���������������Щ�����˵1949�꿪�����ʱ����������Ī˹�Ƹϻر�����Ϊ���Dzμ��찲�ŵ���䣬��ë��ϯ����������������찲�ų�¥��Ȼ��������ȴ������������ȥ�ˡ�1950��ë��ϯ��Ī˹�ƻص�����ʱ�����ֲ��ý��ൽ��վȥ���������ڴ�֮ǰ���������Ī˹�ƻؾ�ʱ��������ȴ���廪��վӭ���������档��������һЩ�������Ž�����Է�������������쵼�����š�������治ס����ʵ���̲�ס����ֱ����ë��ϯ��ӳ�ˡ�ë��ϯ�����Ժ�ˣ�Ұ��Լ������ĵĻ����������桢�ܶ�������µ�ͬ־�����ʹ�Ҵ��Ϊ���ˡ�������Ϊ��֪����Щ���Է����Դ�ڽ��࣬���е����������Ծ�֪����ë��ϯ�Ļ��ֲ���Υ������ע����������죡�������ѣ���Ӳ��ͷƤ�������淴ӳ��Щ����������ע������ˡ���
1950���1952��䣬������������ȥ������һ�����Ź�����ͬ��һ������������ͬ��������Ϊ��ϯ���ˣ�������������Ĵ�������һ��С¥���������粿���ɸɲ���ͬ����Ͼ�����ӡ�ר�ŵ�ҽ����Ա�͵�����С��ȵȡ���
������������һ��֮���ֲ������ˡ���Ҫ�Dz���������������ϯ���˵����ݳ�������ǰ����û��ʲô��ְͷ�Σ��е��Լ������ݲ�����ʡ������Ի͡���Ϊ�������еĻ���Dz����ܾ�֪�����ҵ����ſ�֪��һ������
1952����ĵ�һ�����磬ë��ϯ�Ļ�Ҫ�����绰���ң�˵������λ�������Ҫ�����̵���ϯ����ȥ���ҵ�Ȼ���ҵ���������һ�߽������ţ��е������쳣������һ��������ë�ͽ��࣬��һ����������������һλ���롣��λ��������ʶ�����������ģ����イ�ý�����������̸����Ũ����������ʶ���ҵ������Ƕ���ģ���ë��ϯ��������Ŀ�ⶢ���ҡ��ҷdz����Ρ������Ҹ�����뿪ʱ������ȴ��ë��������һ��������ȥ�ˡ�����ʮ����ӣ�����ת������̬�Ⱦ�Ȼ��䡡
��ת����ë��ϯֻ���������ң�����ֻҪ���������룬������������λ������졣����ʹ��ʮ�־��ȣ����һ��DZ�ʾ����λ��������κ;��أ����ǹ�ͬ�����ŷ��롣�Һ�Ϊ��λ����ͬ־ҲΪ���Լ��ѹ����º����˽����Ҫ����֪ͨ��ȥ��ֻ���չ�ȥ�ij����ġ�����֪�������ѷ����˱仯����
��1953����ĵ�һ�����ξֻ����ϣ�ë��Ȼ���ʣ������Ķ����������Ǵ������������ң��ְ��������ҵ����ԣ�����������������������ر�ʱ���������ξ־��������ġ�����������Ǵ������鼯��칫�ĵ�λ������������Ϊ��ϯ������ϯ�Ǵ������硢�������Ⱥ�����ŵ����ˣ����������ң��ѹ������ĸ���ͷ���������˵����һ���ʱ����ϯ��˵��������Ϊʲô��֪���أ������˵�������������ˡ�����ϯ��˵������ֻҪһ������С������ˣ���Ҫ�Ǹ����������ҡ������ǵ��������������������飬���������⣬����ԭ���ǰ��ˣ�ֻ���鳤�ɽ��������Ρ��������������Ҵ�������һ����֮������һ�䣻���㿴�����˼ң���Ҷ�֪����ֻ����˵��֪��������ʵ���ܲ�ȡ���ַ�ʽ�����뿪���������λ��ȴ��Ϊ�Լ����ҵġ���ע�����˵�Ȼ������˿ɿ�����
��
���ţ�ë��ר����������������鳤���鳤���ˡ���������������˹�ְ�����������ε�λ����Ȼ����Ҳ����ˡ�����ֻ�ǹҸ���������������ʲôʵ�ʹ������������������������������һ��ʱ�䣬��������ϯ������µ�Ҫ����ë��ϯ���й�Ϸ�硢��Ӱ���赸����������ϣ�Ҫ���������ģ�������Ҫ��ֵ����ջ�����ָ�����ˡ���
���ĸ��ʼʱ���������������й������ž������չ��ʵ�ְ����������Щ��ë��ϯ��Ǩ���������Ժ�ķ�չ�������������ӵ��ˡ���
����ֻ˵�����йص��¡�1954���������ͬһλͬ־��̸����˵����Ҫ��ʦ��ժ������塢�������Ϊʲôȴû��˵��������Զ��ҳ�����ˣ���ˣ�ݵ��Ӱ�ʱ������������Ǵ��칫������֮ʱ������ʱ��û��������Ҫ����ְλ��Ҫ���ֲ��ϸ�������һ���û����Ŀ����Ŀ��Ϊ�����������ġ���һ���棬Ҳ�Ǹ���Ҫ�����棬������Ϊ��ͬ�������һ������������Ҫ��һ��ʶ��®ɽ��Ŀ����ͨͳ�������صġ�����ɱ��������ǵ�ʱ�õ�ë��ϯ�����κ�ʹ�á���
1954��1955��֮����һ�����µ�ë��ϯ�İ칫��������º�����Ȼ����˵�������Ժ��ٵ���������ʱ����Ҫ���Ⱦ�����Ҫ���飬��Ҫ��绰֪ͨ���ǣ�ֱ���������ˣ����Ѿ��������ڱ���Ҫ�����㡣�����ģ���������ô���£��Ҳ